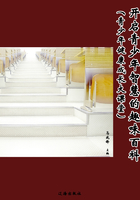凤梧早与他玩得心契,夜间听他谈些天南地北的荤素事尤觉新鲜,有心多留他几日,就说,外头有馆子,我把些钱给你。佑安说,鹤鸣兄弟跟我说,多吃些山珍海味最是补人。凤梧想了想说,那也不难,我可以捕捉,只是到哪里去弄熟呢?
佑安立即答,那又何难,拿到小馆子里去加工就是。第二日,凤梧就偷偷跑到后山,几个小时后就回来了,从一只小柴草篓里掏出几只肥硕的斑鸡来。
佑安讶道,难道你赤手能擒住飞物!
凤梧从长襟里掏出一把茶木弹弓来说,我迫得很近才打,不然吃不住劲。这个喜不喜欢吃?
佑安如同嗅到了烤斑鳩的香味,连声说好吃。凤梧叮嘱,拿出去加工的时候,切切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佑安点头,那是当然。连着几日,凤梧上山都有收获回来。夜间,佑安在屋里啃着煎烤的野味,问凤梧吃不吃。凤梧说,捕杀了它们就是罪孽了,哪敢再吃。佑安说,捕杀了它与吃了它,巳经没有区别,吃与不吃都是罪孽,既然如此,何必不吃。
凤梧不答他,避开那股香味跑出去。
这日清晨,凤梧如厕去了,佑安故意在一个小和尚扫地的时候,做出不期然让他发现秘密的样子。有些紧张地道,给你吃一点,你莫跟别人说是凤梧打的。
小和尚攥紧扫把,惊恐地摇头。
佑安轻视道,胆小鬼,凤梧都敢吃,你却不敢,他在云门寺的年头总比你长吧!
小和尚拖着扫把转身走了。佑安不知小和尚是否会去告发,等待着。
一日无事。
晚饭后,凤梧与佑安在外头散了步回来,早有人立在门口对凤梧说,海慧法师叫他速去。
风梧不知何事情,匆匆来到师父的禅房前,骤然心惊:门前一只纸盒,纸盒里盛着斑鸩等野物,正是从西厢房里搬来的。心中大苦,佑安你如何不收拾严密!
这是不是你的作为?烛光下,师父一张脸蜡黄,峻严可怕。凤梧心中害怕,不敢认又不敢不认,口将言而嗫嚅。是你做的还是你那个朋友做的还是你那个朋友叫你做的?师父拄杖的手不住地抖。
凤梧带着哭腔道,徒弟罪孽深重,师父救我。孽障啊!师父叫了一声,正欲举杖,身子却摇晃起来,扑通跌落。
凤梧上前抱住他,见师父双目紧闭,不由大恸动,师父啊!片刻,师父缓过劲来,倚在床上。凤梧后悔不已,反复请求师父宽恕。
良久,海慧才开言说,我其实早看出你俗心不死,向佛意薄,身在山门,念在尘中,但怜你性敏机智,在寺院里总是胜人一筹……小事姑息,以为慧根不浅者,总能自我悟识,何须大责,不期你终于滑落到这一步……也怪我平日教诲不严,愧对佛祖啊!话语未断而双泪长流。凤梧扑通跪下,悲恸万分道,师父啊!你,返俗去吧,我不留你,也留不住你。见师父如此感伤,凤梧心痛泣血,方知自己的思想作为太简单、太鲁莽,愧对师父栽培。事已至此,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纵然是勉强留在寺中也无甚意义了。
他问师父,可还有话需要叮嘱。
师父默了片刻说,守慈悲心,行利它事。你还年轻,最好学一门手艺,切莫浪荡邪命就是。说罢,师父转身抢珠念佛。凤梧含泪慢慢退出。
这时,天已经黑尽了,偏殿里的几缕烛光,飘曳而出,涂抹在那口卧立的铜钟上。
凤梧被师父叫去的时候,佑安尾在后头,站在门外窥听。那一幕在他看来真如演戏一般,却也有几分感动,更多的是计谋得逞的快乐,在他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位朋友兼棋友蛰居山门。
次日,佑安领着凤梧进城去。一路上凤梧默默无言,一副心事未脱的神情,佑安叽里呱啦,说个没完,有意给他开心。路上见一个小孩在牧马,佑安叫道,小孩,给你几毛钱,送我们一段路。
凤梧正犹豫间,佑安双手一合,便把他抱送上去,随即自己一纵,坐在他后面。因小孩牵着马缰在下面,骑不快。佑安对小孩道,你跑怎么样,多给你几毛钱。风梧这才说,那不行。
佑安说,到底是当过和尚的!又哈哈笑道,我正是要你开金口呢!他哪能跑过马!
到了万氏医寓,佑安跳下马道,鹤鸣,你看我把谁给领出来了。
进到屋里,喝茶抽烟,佑安得意地把整个圈套兜了底。凤梧羞恼了说,你这人也太鬼了!
佑安把茶杯一放,似有不悦道,你要是不乐意出来,现在再回去还来得及。
鹤鸣忙说,早晚是要到这一步的,既然出来了,就思量出来以后的事情。
凤梧锁了眉道,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块,又没本事,如何在这城里立足?
佑安说,你能用弹弓打斑鸩,那就是本事。要不然,跟我当兵打仗去,我保证你学打枪一定又快又好。
鹤鸣知道要他这样一个山寺之中出来的人去扛枪打仗,不太现实,说,你先安心在我这歇下来。佑安紧接道,朋友兄弟在,自然不会饿着你。
鹤鸣沉吟道,你种地只怕不在行,我们可以凑些钱出来给你张罗个小店铺。
凤梧道,你们也不宽裕的。鹤鸣说,总比你赤手空拳强些。
佑安当即掏出十几二十块大洋来,说,过些日我伤好了回天津,还可以寄些钱来。
阴历六月十五,是鹤鸣那未过门媳妇的老爹五十寿辰,鹤鸣备了一盒精致寿礼前去恭贺,佑安正想看看这位弟媳,便以朋友的身份一同前往。
这户人家姓江,鹤鸣那媳妇叫江秀英,她行六,上头有五个身体壮实的兄弟,这日都携妻将子来拜寿,一家人好不热闹。
江秀英也同兄弟们一样粗壮,也能大碗吃酒。她对鹤鸣及佑安的到来并不热情,把寿礼随意掼在一旁。席间,她叱叱咤咤,大大咧咧,丝毫不顾及鹤鸣和佑安的存在,对自家父母她却夹菜筛酒,很周到的。
佑安默言不语,鹤鸣见朋友神情不悦,吃罢饭略坐坐,就领着佑安告辞出来。
路上,佑安发话道,这个媳妇要不得,很没趣的。鹤鸣说,据说还能干。
能干有什么用,只怕过了门,倒是她指挥你的时候多。鹤鸣叹了一口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不是很满意,他家儿子多,多气力,所以就很骄人。
退了,退了。佑安说,退了她。
母亲虽然也不十分满意,却认定她骨盆宽,会生儿,又觉得她还算有点家底的。鹤鸣说。
退了退了,佑安说,我回家去给你找个会生儿的,而且一定比她温柔漂亮。
鹤鸣说,只怕母亲那里通不过呢,我是个不愿惹是生非的人。你先别跟她说,事情了结以后再告诉她。佑安说,有我在这里撑腰,没有什么事可怕的。
鹤鸣早就对这桩婚事心灰意懒没兴味,于是依言而行。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鹤鸣备了一份厚礼带足了钱到江家去。佑安一身短打,暗中在腰里藏了枪,跟在身后。
进得屋来,鹤鸣将礼物和礼金当即推开,江家人不明究竟,一时讶然。那江秀英呆在里屋,这时却俨然害羞没有出来。江父坐在椅子上,拉长了声问,这是怎么回事?鹤鸣把早想好的话说了,江老伯,承蒙厚爱,使晚生与秀英有秦晋之约……
江父原本是个不识几个字的粗人,打断道,文绉绉的我听不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鹤鸣于是直言相告,他先后请两个有学问的先生看了他与秀英的生辰八字,两个先生都说他俩的八字冲犯得十分厉害,趁着还没有结合,分手不迟;若是勉强结合,短不了三灾七祸。
江父听了这话,一时有些犯愣。江母精灵,问,这么说,你是想退婚?
鹤鸣有些尴尬,说,这也是为了双方的好。江母说,那两个算命先生在哪里,我倒想请他到这里来算一算。
佑安插言,算命先生云游四方,没有固定行业的,走了就走了,到哪里去找!
江母听出这个人口气不善,越发心里有数了,仍对着鹤鸣说,我家闺女行止端正,随随便便退婚,只怕是我同意了她同意了,她的几个兄弟也不会同意。
鹤鸣依然心平气和道,秀英的确是个好姑娘,只是命相不合易招灾啊。
佑安知道文不过去,迟早要同她家几个兄弟论个高下,于是说,把你家的几个男人都叫来通个气吧。
一顿饭工夫,五个儿子都回来了。听了母亲的叙述,大儿子轻蔑道,拿这么点东西来就想退婚啊,挑金搬银来差不多!
老三说,挑金搬银来不行,都晓得妹妹跟万家是订了亲的,退了婚,妹妹以后还怎么嫁人!
佑安说,你家妹子如果无缺无损,如何不好嫁人!老二火了,指着佑安的鼻尖骂道,你他妈的是他的什么人,你他妈的给我滚出去!
佑安慢慢站起来道,如果我不出去呢?老四老五出其不意挥过拳来,叫道,不出去就叫你尝这个。佑安身上挨了两拳,往后一跳道,你们先动了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谁敢再上来?说着牢牢一个站桩戳定。五兄弟同时冲了上来,屋里顿时打成一片。江父和江母都退到里屋去了,鹤鸣也情不自禁地退到里屋。一只手突然被攥紧了,回头一看,正是江秀英。她低声问,你为什么不要我?那样子一时令他有两分心软,但他知道自己心中从未对这个女人萌发过好感,更不用说喜欢,以后也不会萌发。订婚以来,他第一次与她说话,他说,好自为之吧。
外屋一阵乒乓乱响之后有了痛叫和呻吟,江母耳尖,听得出那是自家儿子的声音,推鹤鸣出去,说,让他停手,我们答应了。
鹤鸣知道佑安有一身格斗本领,不会吃亏,但也觉得不能太过分了,出来唤他停手。
佑安正提着老四的衣领,顺手一推,老四跌落到墙根。五个兄弟抱头抚身,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上前去。
佑安大声道,跟你们说,我是鹤鸣的好朋友,在部队上混事,什么恶战都打过,赤手空拳对付十来个人没问题的!说着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来,朝空中一抛,稳稳接住。江父扑通一声跪倒说,别开枪呀!鹤鸣赶忙过去把他搀扶起来,又令佑安把枪收起。佑安敛了枪道,我们原本也不想打起来,这不,礼品礼金都挺厚实,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说着,他过去在五兄弟肩膀上亲热地拍拍,倒反吓人家一跳。
鹤鸣对江家父母各鞠一躬说,晚生失礼了,请伯父伯母多多包涵,日后有晚生帮忙的地方,吩咐就是了。
给了个台阶,何不就势下去,尽管肚里窝火,江母仍挤出一分笑来说,你两人吃了饭再去吧。
改日来吃吧,鹤鸣说着,拉佑安出了门。出门以后便听江家兄弟有了骂声,佑安眉头一蹙,停脚欲回头。鹤鸣拽他二把说,走吧走吧,总得让人家也出出气。
佑安一阵朗笑,边走边说,好久没这样痛痛快快地打过架了。鹤鸣说,你天生是当兵的料。
为什么不说是当将军的料,佑安叹道,腿好了,是该干老本行去了。
你的部队都打光了,还上哪去干?
就凭这一腿枪伤、一身武艺、一张军官学校的文凭,上哪不能干哪!佑安颇为自信。
回到家里,鹤鸣跟母亲说把那头婚事退了,母亲一愣道,这么容易?母亲后来也觉得江家闺女对儿子说来未必很合适,只是有些惧怕江家兄弟的强蛮,所以认了。能如此便当地辞掉,心中顿有一喜,随即忧愁又袭上眉头,说,你年岁也不小了呀!
佑安一拍胸脯道,师娘放宽心,弟媳妇由我包了,保证给找个让你老人家舒心惬意的。
佑安回返天津前,要留把手枪给鹤鸣,以防江家兄弟报复。鹤鸣不收,说留了枪母亲害怕,也未必太平。佑安说,你跟他们讲,如果强蛮撒野,我下次来了就决不客气。
鹤鸣叫他放心,不会有事的。
走的那日,鹤鸣与凤梧把他送到江边,看着佑安上了小火轮,看着那只小火轮远成一丸黑影。
用鹤鸣和佑安凑的钱,凤梧在西街口购下了小小一另店面,经营棕绳、瓮坛、铁锅和明瓦之类的日用土杂。盈利虽不大,却也聊以糊口。
得空,两人时相走动。家中若是做了荤素丸子之类的好菜,鹤鸣总会叫少林送一碗过去。
这日,鹤鸣通过熟人,弄了两木桶廉价桐子油过来。凤梧很高兴,说是张记纸伞店每隔一日就来问桐油,价钱高些也愿要的。
鹤鸣告诉他,缺什么好销的货就及早跟他打个招呼,巡医在外,五行八作的人,总要认得多些。
凤梧沏了一壶茶递给鹤鸣,说,那个外号叫关公的警察称去五斤生漆,总说赊账,前日又扛了一口瓮坛去,看样子是要赖账的。鹤鸣说,我跟他的头儿熟,明日就去说,谅他是不敢赖的。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一边闲聊。
鹤鸣说,佑安去了一个多月,也没信来,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凤梧说,路上不太平,不会出事吧。鹤鸣说,他那个人粗中有细,又有一身好武功,出不了事的。凤梧点头附和,想了想说,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有武功,那也是可以挣饭吃的。
鹤鸣细心,听出他话语里有些感慨,遂问,店铺开了一个多月,你感觉怎样?
凤梧说,现在看来还算顺利,那也是托福你的多。天长日久,总觉得,还是自己学门手艺的好,当时出山门,海慧法师也是这样叮嘱我的。想想,是有些辜负他了。
默了一刻,鹤鸣说,想来也是的,趁着年纪还年轻,学门技艺倒不错。谈话间,两人把剃头、制伞、修锁、捏糖人、配首饰等行当都摸了一遍,要么是鹤鸣说,这行当小城太多;要么是凤梧摇头,那行当难做长久。
一时间,似乎没有哪条路行得通的。鹤鸣突然道,你跟我学医如何?凤梧一愣,那怎么行!怎么不行,你脑瓜子灵,能学的。不好的。
你是看我当年不肯学,才说不好的?
不是,凤梧红了脸说,这是你的祖传家业,你将来还要传诸子孙的,况且现在也有少林在学。
鹤鸣笑道,我的子孙那是以后的事,至于少林么,性情浮躁、少不更事,看来与学医是无缘的。即使他能学好,又有何妨,萍埠城若是容不下这多郎中,世界却是宽大得很哪。
对学医问药,凤梧原先并非没有萌生过这样的念头,但也只是闪念一瞬而已。同行犯忌,鹤鸣已经十分不易地捐钱给你置了店铺,你却有问鼎人家祖业的意思,岂不可耻。如今由鹤鸣主动挑起这么一说,不由得凤梧枰然心动,却仍有些跨躇。
鹤鸣说,店铺仍是开着无妨,合适的时候请个小伙计。你先读几本书,得空我领你到源心堂去识药,做个识药的中医总好些,再以后我就带你去诊脉看病。
第二日,鹤鸣便拿了几本医学启蒙书来,如崔嘉彦的《四言脉诀》,雷公的《药性赋》,汪切庵的《汤头歌诀》等,对凤梧说,这些书莫要嫌浅,熟读了以后大有用处,都是学医的基本功呢。
凤梧依言细读,从此把在云门寺颂经的好背功用到医药书上。十来天后便请鹤鸣在抱一摞书来,鹤鸣说,贪多嚼不烂,与其泛泛读十本,不如精细读一本。
凤梧说他都读得很细,记得很牢。鹤鸣便翻开《药性赋》,任挑出两味药,要他背说。凤梧一口气背完,只字不差。鹤鸣再挑两本,依然是指到哪背到哪。
鹤鸣讶叹,有这样好的记忆,学中医那是可以日有所进的。转过脸来对堂弟少林说,你要是学得凤梧的功夫的百分之一,又何至于这么多年了还背不下一本汤头歌!我记忆不好嘛。少林嘟哝。
是懒!鹤鸣呵责道。凤梧你可以雇个小伙计来,你集中精力学医。
少林说,何必雇,我来就是了。我把店子治好了,你就不会讲我懒了。
鹤鸣想了想,答应了他,叹了声,你呀,到底是不肯上进的。鹤鸣把凤梧领来,从枕边拿出两匣子的线装书来说,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伤寒》和《内经》,父亲在世时把这两本书看成是四子书,认为可以常读常新的。
鹤鸣摩挲着书面上父亲藏书的钤印,眼角骤然发潮。凤梧心生感动,说,我若不好好学,不仅愧对朋友,也愧对九泉之下的万老伯呀。
鹤鸣展颜一笑说,如果海慧法师知道你入了医道,也会替你高兴的。
凤梧说,等真正做了一点事情,再告诉他不迟。周佑安北去以后大半年音讯杳然,其间鹤鸣曾按他留下的地址寄去一信,也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