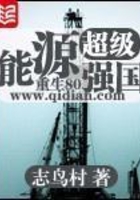板凳板凳歪歪,
楼上媳妇哭下来。
人问哭何事,
丈夫不成才。
又吸鸦片烟,
又好麻雀牌。
三天不籴米,
五天不买柴,
这日子叫谁过得来。
--民间歌谣
两个噩耗同时传到老爷岭,派去看望徐秀云的云杉回来,几位游击队领导听她汇报。
“秀云同志已牺牲……”云杉泣不成声道。
徐秀云牺牲,大家惊愕。
云杉骑马找到那个地方,徐疙瘩的窝棚已经烧毁,愣然中有人叫她道:“小姐,你找谁?”
一个山民站在她的面前。
“这家人呢?”
“走啦。”
“走啦,去了哪里?”
山民默默走到一堆树枝旁,说:“小姐你找的人,是她吧?”
云杉走近树枝,望着刚折下还带着绿叶的树枝。
“她在里边,不过你别害怕,她的头给人割走了。”山民说。
头给人割走,是徐秀云吗?云杉要知道答案,树枝一挪开,她惊骇,一具无头女尸,衣服也给撕破,双乳有奶汁溢出,干涸在胸脯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云杉问。
山民说夜里有了枪声,当夜见四五个男人和李转轴一家匆匆离开,留下这具尸体。
“这家的主人……”
“噢,徐疙瘩和他老婆逃走了。”山民朝树林子指指,说有个通到山那面的山洞,他们是顺洞逃走的。
“她是不是生个孩子?”
“男孩,准保徐疙瘩两口子抱走,他们没孩子。”山民说。
云杉还有一个疑问,李转轴怎同那几个男人走?他们是什人?山民说他们自称收购貂皮的老客,看样子是一伙日本人。
事情基本清楚,云杉求山民帮忙掩埋徐秀云。
林子中的一小块空地埋葬了徐秀云,山民找来一块圆石头摆在她的脖子处,权当头颅,憨厚的山民说:“人死后总得有具全尸啊。”
咣!徐德成一拳砸在案板上,说:“这仇一定要报!”
“现在不是谈报仇的问题,如何对蒋副队长讲秀云的事。”尹红说,他们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夜游神”行动小组最快也得在下午赶回营地,她望着徐德成。
“我来跟他说吧。”徐德成说。
“夜游神”行动小组下午带来第二个坏消息:蒋副队长牺牲。
鸦片加工厂全部炸毁,大家高兴不起来,徐德成失声痛哭,也顾不得游击队的纪律,一口一个二弟,呼唤他的草头子兄弟。
几个副队长转而劝他,悲伤的气氛笼罩营地两天。谁都知道他跟蒋副队长的感情,十几年里生死相随。
“尹代表,我们为蒋副队长举行葬礼。”徐德成说。
同志牺牲举行个简单的葬礼是必要的,她说:
“同意,秀云他们俩放在一起举行。”
“我安排人打井子(挖坟坑)。”徐德成说。
“蒋副队长的尸体不在,也不可能弄回来,打墓子做什么?”她疑惑道。
“他的马鞍还在……”徐德成要求过格了,他说,“隆重地葬,按绺子规矩。”
“这不合适,我们是游击队,不是胡子。”
“我不管,他是我的兄弟。”悲痛使徐德成不管不顾,谁也拦不住他,摔脸子(耍态度)道,“你可以不参加,你们都可以不参加,我私人葬他。”
“你……”
尹红还要批评他两句,徐德成一甩剂子(赌气离开)走开。几位副队长一旁看到这些,也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去劝劝他,讲清我们是游击队,不能搞这一套。”尹红说,“搞一个吊唁仪式,开个简朴的追悼会。”
徐德成抽了一夜烟,几个副队长轮番地劝,天亮时他才松口,说:“按尹代表的意见办吧。”
追悼会后,忽然不见了徐德成,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他能不能一个人跑下山为蒋副队长报仇?
“大家分头找。”尹红派出几路人马,满山寻找。
尹红也带两名女游击队员出来找人,她们在一处峭壁上发现了徐德成,尹红说:“别出声,让他做完。”
徐德成在做什么?懂土匪习俗的人一看就明白。他跪在一个石块垒起的坟墓前,点上香,声音悲怆道:
“江湖奔班,人老归天,草头子兄弟你走了,大哥来送你!”
隐蔽在树后面的人默不做声,望着那个江湖色彩浓厚的丧葬场面,下面徐德成的行为不可思议,他将手放在嘴上做出喇叭形,发出悲喑的琐呐声……
“他吹的什么调?”云杉问。
“《九龙调》。”尹红说。
两天后,小花上山来,讲了鸦片加工厂被炸后的情形。
“机器全部毁掉,消灭了全部护厂的皇协军,只跑了一个人。”小花扫了眼徐德成,“只徐梦人一个人跑掉。”
“蒋副队长的尸首?”尹红问。
小花心里像有什么事,第二次看徐德成,说:“被宪兵弄到队部去,正组织人辨认。”
“辨认的结果咋样?”
小花说目前尚不清楚,水野大尉还从山里拎回一个人头一起辨认,徐特派员让问一下,游击队最近有没有人牺牲。
“小花,徐秀云同志……”
“啊,难道是她。”尹红悲痛地说。
“还有一件事告诉你们。”小花第三次望徐德成,说,“打死蒋副队长的人是徐梦人。”
“徐梦人?”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徐德成。
徐德成的心猛然像给毒针扎了一下。
“徐梦人亲口对徐梦天说,他打死了蒋副队长。”小花说。
近日徐梦天忙一桩酱菜园老板被杀的刑事案子,几日未到康生院来,他主管康生院并非是院长,平常也不怎么来,将弟弟徐梦地交给他们戒烟。医生、护士管得了警务科长的弟弟?
忽略或是未认真管束,徐梦地戒烟没效果,武装看守下竟然逃走了,康生院长急忙向徐梦天报告,他正忙案子无暇顾及烟鬼逃跑,打算忙完案子再管他。
徐梦地逃出康生院,谁都能想到他最先去哪里,他走路相当吃力,好在天没风,花半天时间吭哧瘪肚晃荡到牤牛哨屯翟扁头家,背脸房寂静无声,他习惯望眼房墙,没挂盖帘儿,窗户帘却撂着。
“她忙着呢!”徐梦地酸起来,这种事以前他不怎么酸,为了抽口烟,舍孩子套狼他认可,今天发酸是他被关康生院数十天,戒烟要一百天,他除了受烟瘾折磨外,还想女人,只想一个女人--老崽子,他曾说你是一锅烟。她说你天天“刮海底”。
屋内的事情进行得很长,他心烦意乱地等待,想的也是屋子里的事。老崽子做这种事有人说他吃二模,便有一根氄刺儿扎在心上,虽然细小甚至看不见,还是针扎火燎地痛,唉!总归为抽一口(烟)啊!
门响,走出一个男人,他冷冷的目光望着徐梦地问:“你在这儿干啥?找谁呀?”
“找她!”徐梦地指下窗户道。
男人肉鼻子(扁鼻)一抽,忽地上前薅住衣服领子拎起徐梦地,他挣扎双脚悬空蹬踹,一只提溜跑掉下来。
黄毛子女人走出屋子。当地人称头发黄的女人黄毛子,刁泼女人也称黄毛子,有一种大蜻蜓叫黄毛子。
“老……”徐梦地将“崽子”两字憋在嗓子眼,面前的女人陌生,他说,“我找老崽子。”
黄毛子脸色很新鲜,说:“房子早卖给我们啦。”
“她人呢?”徐梦地打听道。
“上山啦。”黄毛子说。
上山的含意马上被徐梦地理解,她死啦?
“瘾死的。”男人说,扔东西一样把徐梦地撇到地上,摔个腚蹾儿(蹾屁股)。
徐梦地揉着摔痛的胯骨轴,打愣一会儿,穿上掉在地上那只鞋,眼泪巴叉地走了,一只夏末的蜻蜓跟他飞出屯子。
“我以为他是找你的。”男人小心眼道。
“就他气儿都喘不匀,还能干那个,嗔是。”黄毛子女人诙谐道,“你手捂脚摁地把着,谁沾得了边呀。”
徐梦地显然听不到这对男女打情骂俏的风流嗑儿,他和老崽子动嘴少,都是实质内容。老崽子死啦,他对女人再没什么想头,陈蝈蝈教授过他经验,对女人要逗、要糗、要敢动手……如今他什么都不感兴趣了,趁大烟瘾没犯找到大烟,犯瘾时没指项(望)不成。
“该割浆了。”徐梦地想到自家的大烟地,灰蓝色的植物使人兴奋,守着几百垧大烟放量抽……去大烟地。
徐家大烟地今年警察看着,替换了宪兵。实际情况是抽不出宪兵看护大烟地,三江两千垧大烟割浆时林田数马命警察局负责护卫。宪兵队为种烟户规定上交烟土数量,谁敢不按数交。
徐梦地接近大烟地的边儿,趴在壕沟里窥视比爹亲的植物,戒烟时管家说你再抽就把你爹气死,他说,没爹行,没大烟我活不成,人都活不成,要爹干啥?
警察挎枪沿大烟地边走,偷大烟几乎不可能,何况大烟还没熟,割浆还没开始,当他看见爹的身影在大烟地里出现,徐梦地放八跑开,回到亮子里。
城里是大烟鬼的天堂,哪个角落都可能藏着烟土烟膏。如今亮子里烟馆有几家,都是官办的,最大的是四凤的白罂粟烟馆,次之的是大竹的云仙楼,还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烟馆是朝鲜人仝相奎开的同乐园,其他还有三五家土烟馆。
徐梦地不敢去四凤的烟馆,怕家人发现他,发现就要送回康生院,吃高粱米、窝窝头、咸菜疙瘩、白菜汤不说,不让碰烟,烟瘾发作也不给抽一口。烟鬼们碰面当然谈烟,一个烟鬼自擂当年的风光,很有钱时到云仙楼去过瘾,大竹在关里开过烟馆,带过来名贵的烟具。烟鬼说鸦片烟中四大件头:胶州灯,寿州斗,张判扦子,象牙枪。
徐梦地去云仙楼可不是冲着烟具去的,他去捡洋捞儿--烟灰。
这天,大竹陪林田数马在烟馆大厅里说话,有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人给看门的拦在门外:
“去去,滚一边去!”
“爷叫我进去吧……”
“一角钱都没有你进去干吗去?麻溜走!”看门的轰赶道。
“行行好,让我进去。”
看门的土皮鞋发言,瘦得皮包骨的人悻悻离开。
林田数马见看门的轰赶一个没钱买大烟的大烟鬼,他看清了那个大烟鬼的面目,惊讶中吐出一句当地土话:
“羊上树!”
“羊上树?”大竹不知何意。
“叫住他,叫住那个人!”林田数马说。
大竹出去叫住人,此人正是徐梦地。
“徐二少爷。”林田数马用老熟人的口吻道,去年他在徐家大烟地见过徐梦地,说,“进来抽一口嘛。”
“我没钱,只想弄点烟灰,他们踢我。”徐梦地委屈道。
“弄烟灰做什么?”林田数马明知故问,他亲眼见到一个人吃大烟灰,买不起鸦片捡大烟灰吃,俗称吃灰的。
“吃。”徐梦地说。
“你是少爷,你爹该给你鸦片抽啊!”林田数马像是同情,宪兵队长有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连了解他的大竹都没看出来。
“我爹不给……”徐梦地到了山穷水尽,任何一根稻草有机会都会抓,他哀求道,“队长太君,你跟他们说说,让我捡一点烟灰。”
“烟灰地不捡,徐少爷要抽上等烟。”林田数马对大竹说,“安排他抽一口,要用最好的烟具。”
扑通徐梦地跪下,给宪兵队长磕头。
“你起来,去抽烟,抽完我有事情跟你说。”林田数马说。
“谢队长太君,谢队长太君!”徐梦地千感万谢,宪兵队长要是中国人,他会说你就是爹,是我的亲爹!
“去吧,我等你。”林田数马说。
徐梦地乐颠地去抽烟。游向钩子的鱼没看到危险,诱饵太鲜活,无法抗拒诱惑。
草头子死后,徐德成的话陡然少了,没事就一个人躲在一旁抽烟,蛤蟆头很冲,他一天不停地抽。
“德成。”尹红第一次以嫂子的口吻和他讲话,“你二哥捎信给我,让我开导你,怕你想不开。”
徐德成苦笑,说:“没啥想不开的。”
“不对,你过去烟没这么贫,几天一捆烟。”尹红说,“有什么话说出来,憋在心里还不憋出病来。”
“真没什么事。”
“没什么整天心事重重的……”
徐德成想的那件事搁在谁身上,都是难抉择,他要除掉自己的儿子徐梦人。几个月里决心都没最后下,难在他对死去一个女人的许诺,一诺千斤啊!梦人现在是凶手,他还效忠日本人,留下是祸害。
“黑心皮子!”徐德成用土匪黑话骂了一句,黑心皮子是狼。
他推想的情形几乎与当时情形一模一样,蒋副队长将梦人逼到一个死角,他举枪瞄准的一刹那,见到是梦人首先想到的是不伤害他,所以抬高枪口放了空枪,本以为梦人会逃走,可是梦人却打他一枪,离得太近命中要害。
“你放不放梦人一马?”尹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