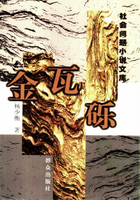两个身份特殊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做出的事情很少被后人真实地看到,但是她们无怨无悔地做了,应得到敬重。她们为“夜游神”行动小组顺利进入城中创造了条件,对付两个守城门警察和对付五名警察结果不同,没放一枪解决了两名警察,“夜游神”行动小组迅速到达鸦片加工厂,同皇协军的战斗时间很短。
“炸厂房,炸机器!”蒋副队长命令道。
那一夜徐梦人在工地上,睡在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枪声响起,他第一个反应抓起电话报告宪兵队,电话线被割断,他带上手枪爬出屋子,躲在一只巨大木箱子后面,最后给蒋副队长发现。
借着一丝灯光蒋副队长看清了他是谁,义气、善良使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抬高枪嘴放空枪,意思让他逃走。突然,对面射来子弹。徐梦人有了射杀的机会,毫不犹豫将蒋副队长击中。
爆炸声响起,“夜游神”行动小组急速撤离,没来得及带走蒋副队长的遗体。
闻到枪声赶来的宪兵队,见到是一片废墟,机器成为一堆乱铁。
“巴嘎!”林田数马扬起手,扇了徐梦人一个嘴巴。
“有什么话你说呀,时仿!”徐德富催道。
“这、这可怎么说呢!”管家谢时仿从来没在东家面前如此难开口,他的心更急,不知如何说好。
“梦地是不是人丢大了,让你张不开嘴(羞于开口)?”
“跟二少爷的那个女人,卖大炕!”谢时仿终于说出来。
卖大炕就是一巴掌,狠狠抽在徐德富的脸上,都说打人不打脸,忤逆儿子偏偏打他的脸。
“我劝二少爷回家,他死活不肯。”
“都那样了还劝他干啥,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徐德富疾首蹙额,“逆子,逆子啊!”
“老爷,二少爷走到这一步,有啥原因吧?”谢时仿说。
徐德富在想根源,梦地以前是个秧子(不务正业),大格还不过。自从让他去大烟地,跟打头的陈蝈蝈抽大烟,人就完了,钻女人被窝……钻也罢了,咋钻那样女人被窝。
“看样子女人挣钱,也是买烟土。”管家说。
“你说梦地现在又抽大烟?”
“捡起来了,那个女人也抽烟。”
“玩啦,完犊子(不肖)啦!”徐德富失望到底,心反倒平静了,问,“到底是谁家的闺女啊?”
“翟扁头他爹从窑子里领出的……”
“你瞅瞅这种女人他也要,彻底完蛋啦!”徐德富如负释重,“儿大不由爷,由他去吧,我也静了这股肠子。”
“老爷”,谢时仿劝说道,“二少爷怎么说还年轻,受人教唆抽了大烟,一时糊涂走了歪歪道。”
“抽大烟有人怂恿,钻不三不四女人的被窝也是受人怂恿?”徐德富说,“你别为他开脱了,抽大烟,和窑姐鬼混,多少钱财够造害(糟蹋),王八坑啊!我管他,尾后我可有王大娘唱。”
那是一条命啊!谢时仿没这么说,作为管家这样说也不合适,换了说法道:“大烟能抽就能戒,想办法戒掉。其实,办法也有啦。”
“什么办法?”徐德富口气缓和一些,问。
“大少爷他们警务科开办的康生院,有人近日投戒,不妨……”
徐德富听懂管家的意思,梦地到哪里强制戒毒说不定就戒了。说不管,总归是气头上的话,做父母的眼瞅着儿女掉井不救?梦天管康生院,能戒了两旁世人的烟瘾,自然能戒自己弟弟的烟瘾。
“我去找大少爷回来,商量商量此事。”谢时仿说。
“还是我去吧,顺便看看那个康生院。”徐德富说,眼瞅大烟开刀(割浆),大烟地离不开人,“你先去大烟地吧,过两天我也过去。”
谢时仿回大烟地,徐德富去警察局找到儿子。
“爹,爹怎么来啦?”
“有事,你有工夫吗?”徐德富问。
“有。”
“领我到你管的康生院去一趟,具体的事半道上我跟你说。”
爹要找他又要去康生院,徐梦天猜到几分了。出了警察局,徐德富问:
“梦天,大烟这玩意到底能不能戒?”
“能戒,咋不能戒。”
“那你说梦地咋就戒不了?最近又抽上啦。”
“两方面来看,他没戒彻底,再就是复吸,最难弹弄(对付)的也就复吸。”
“我使线麻绳捆他十多天,彻底指定彻底了,八成就是你说的复吸。”徐德富说明来意,“找你给梦地戒烟,你看中吧?”
“中,当然中。”
“实话说吧,我对康生院是张三(狼)哄孩子,信不大过呀。”徐德富讲了社会上的种种传言,“是这样吧?”
徐梦天未置可否,外地办的康生院大概是那个样子,三江县的康生院交给我徐梦天来办,就让它名副其实,戒掉大烟鬼的毒瘾。
“反正你弟弟也就这个熊样,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徐德富说。
“爹放心,梦地交给我,保准他戒烟成功。”
康生院规模并不大,装下百八十个人没问题,设施什么的比徐德富想象的要复杂一些,什么医生、护士、食谱的。走出康生院他问儿子:“咋没见绳子?”
“绳子?要绳子干吗?”
“绑人啊,犯烟瘾疯了似的,你不绑牢都不行。梦地我系了猪蹄扣(越活动越紧的绳扣)都没顶事,足足捆了十二道绳子,系了蛤蟆扣儿(绳结)。”
“爹,康生院戒烟采用科学方法,不用绳子绑,使用药物和心理治疗……”徐梦天说。
“中了,咋治能治了你弟弟的烟瘾才算尿性(能耐)。”戒烟与绳子没关系,徐德富没兴趣听,他说,“你派人把梦地抓来吧。”
“抓?”徐梦天惑然道。
“不抓他可来不了。”徐德富讲了徐梦地目前的状况,“梦天,你可别把那个女人也弄来,趁此断了他的念想。”
“我知道了,爹。”徐梦天说。
两名警察骑马来到牤牛哨屯,在翟扁头家背脸房前下了马。一个警察冲大白天撂着窗帘的屋子喊:
“家有人吗?”
屋内女人搭话道:“没挂盖帘!你没看见?”
“盖帘?少废话!”警察莫名其妙盖帘,横道。
“爷呀,你等一会儿嘛,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
“说啥鬼话,”警察嘟哝一句,失去耐心烦儿(耐心),亮出身份道,“我们是警察!徐梦地在家叫他出来!”
屋内没声音。
哐!哐!警察踢门道:“听见没?别找不自在(找罪受)!”
“找我?”徐梦地从院子里的柴禾垛里钻出来,头发、身上沾满草屑,“你们找我?”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查证身份,盘问。
“徐梦地。”
“你是徐梦地?”
“那还有假呀?是徐梦地二十多年了。”徐梦地贫嘴,他不惧警察,有仗义的嘛!他说,“找我什么事?”
“跟我们走一趟!”警察说。
“跟……我犯啥法跟你们走?”
“你抽大烟……”
“日本人还种大烟呢,你们咋不去逮他们?”徐梦地嘴不短道,也知深浅,当警察面没称日本人是二鼻子。
“那你去问日本人好了,我们只管你抽大烟,走吧!”警察说。
“你们知道我是谁?”徐梦地亮出哥哥,“徐梦天是我哥,你们敢抓我?”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正是执行你哥的命令,来抓你。”警察说,是徐梦天让他们这样说的,“你上马,驮你走。”
一阵风吹来,徐梦地轻飘纸壳一样趔趄,扶着一根木杆站稳,他用一下脑子,猜到哥为啥派警察抓自己,定准去戒烟,不能撇下老崽子,要戒一起戒,他说:
“屋子还有个大烟鬼。”
警察几乎没听他说什么,鹞鹰捉鸡似的将他拎上马背,鞭马出了院子。直到这时徐梦地才使出全部力气喊:
“老崽子,老崽子!”
一个女人出现在房前,远望他一眼,转身把手中的盖帘挂在房外墙壁上。
徐家人后来说日本宪兵队长的一撇子,把徐梦人的脑子打成臭鸡蛋,混汤子(蛋清蛋黄混杂)啦,他才出卖二叔徐德中。
鸦片加工厂被完全炸毁,死掉一队皇协军和丢失一挺机关枪,全部战果就是一具尸体,徐梦人说他打死了这个人,林田数马没表示出信不信,他命令宪兵将尸体弄到队部来,研究他的身份。
徐梦人从窗户可看见蒋副队长的尸体,他是谁?炸毁鸦片加工厂的人,自己击毙了他。在宪兵的组织下不断有人前来辨认,还没人认出来,辨认继续下去,林田数马扇了他一耳光子后没再找他,撂在一边是啥意思,他惴惴不安,哪怕再被叫去,再扇几个耳光子也比撇在这儿好受。他在乎宪兵队长怎么看自己,鸦片加工厂被炸毁,是否重建?自己还能当厂长吗?
“怎么做才能使队长高兴?”徐梦人绞尽脑汁想讨好林田数马的办法,辨认尸体,他要找到尸源以确定破坏者的身份。是啊,队长最想知道这件事,如果自己知道就好了。
颠覆军列和炸鸦片加工厂是不是同一伙人呢?徐梦人这么想决定了他的悲剧下场。军列上有鸦片,炸毁加工厂也与鸦片有关,鸦片,鸦片……他想到军列出事那天下午,在徐家药店看到骑马的陌生女子,她来后二叔出去一趟,他回来那个女子离开……他去了车站了吗?如果去了车站,这件事跟他有牵连。队长对此线索一定感兴趣。
“徐翻译,你哥来找你。”一个宪兵来叫他,“在门外等你。”
徐梦天在宪兵队部门外等着,徐梦人走出来。
“哥。”
“我来看看你,昨晚加工厂出事,还死了不少人,我不放心来看看。”徐梦天问,“没伤着吧?全家都惦记你。”
“没事儿,”徐梦人炫耀说,“我还打住一个呢?”
“打住……”徐梦天听懂了,梦人打死一个炸工厂的人,“他们是什么人?”
“林田数马队长正组织各行各业的人,前来辨认我打死的人,还没认出来。”徐梦人说。
一辆人力车停在宪兵队部门口,郝掌柜下车,远远地向徐梦天招招手,算是同他打个招呼,然后进院去。
“去辨认。”徐梦人说。
“梦人,看你挺好的,我回去啦。”徐梦天临走叮嘱一句,“抽空去告诉二姑一声,她惦挂你。”
“哎!哥慢走。”
徐梦人回到自己的卧室,不由自主地到窗前看那具尸体,郝掌柜向林田数马讲什么。
“队长,肯定是他,没冒儿(没错儿)!”郝掌柜肯定地说。
“嗯?”林田数马双眼放光,他说,“你跟我来!”
林田数马将他叫到队长办公室,说:“郝掌柜,你详细说说。”
“是,队长。”郝掌柜说,他是天狗绺子二当家的,叫草头子,角山荣队长改编他们成立特混骑兵队,他任副队长,“我们很熟识。”
“后来他去了哪里?”宪兵队长问。
“月亮泡子出事后,再没见到他。”
“你还知道他什么?”
郝掌柜想想说在往前,老头好绺子接受安国军改编,驻扎本镇他是副官,别的就不知道了。
“你的过来。”林田数马又领他到一个阴森森的屋子,他揭开一块布,桌子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问,“认得她?”
妈呀!郝掌柜脸吓变了色,他哆嗦上前,眼前云雾一样迷蒙,定了定神,才看出是女人的头,端详一会儿说:“是她!”
“她是谁?”
“赌徒徐大肚子的闺女,叫徐秀云。”郝掌柜说。
“说说她。”
郝掌柜讲她爹赌钱将她输给徐德龙,和他过一段日子,由于徐德龙赌习不改,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徐德龙是徐德富的?”
“四弟弟。”
“徐家兄弟几人?”宪兵队长问。
“哥四个,老大徐德富,老二徐德中,老三徐德成,老四徐德龙。”郝掌柜详细介绍道,“老大徐德富队长您熟悉,老二就是在徐家药店当坐堂医生的那个,老三死了多年,老四也死了几年。”
“徐梦人是谁的儿子?”宪兵队长抠得很细。
郝掌柜对徐梦人的来历说不上来,外人一般不清楚,当年徐德成把叫小闯子的男孩送回家,外人不知详情。
徐梦人一直站在窗户前,林田数马带郝掌柜领进办公室,他猜想种种,情形上看,郝掌柜认出那个人。
“对不对队长讲呢?”徐梦人拿不定主意,说了抓走二叔倒没什么,牵扯到家人怎么办?养母、大伯、大娘、四婶、四凤姐……他们受牵连咋办?可是,不用硬头货不中,林田数马因破获不了军列被颠覆案,屡遭上司训骂,只差没命他自切。
“徐翻译,队长叫你去。”宪兵来叫他。
走廊上徐梦人蹴蹴不安,队长叫自己去干什么,是吉是凶啊?他迟疑中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硬着头皮走进宪兵队长室。
“坐吧。”林田数马态度温和,说,“你击毙的人身份认出来了,他是天狗绺子的二柜,草头子。”
“胡子?队长,胡子炸我们工厂做什么?”
“问的好,胡子炸我们工厂做什么,胡子不抢东西胡子炸工厂,道理讲不通。”林田数马说。
徐梦人揣度宪兵队长在想什么,当然是鸦片加工厂,他试探着问:“加工厂怎么办?”
“工厂以后再说,你跟我去认一个人。”宪兵队长起身,他悄手蹑脚地跟上去。
见到徐秀云的人头,徐梦人一愣。
“你的认识?”
“认识。”徐梦人察觉宪兵队长的目光中隐藏什么可怕的东西,照本实发的好,他说,“徐秀云,我过去的一个四婶……”
林田数马满意他的回答,他说:“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人怕冲动,一冲动就不管天不管地了,徐梦人说:“有件更可疑的事向队长报告。”
林田数马盯着他的眼睛,示意叫他讲。
“军列被颠覆那天,我见到……”徐梦人冲动出使徐德中人头落地的事情,他确实出卖了自己的亲叔叔,他倒没忘说天真的话,“队长,假如我二叔有什么事,与我大伯他们没关系。”
“当然。”林田数马表示不会伤害徐家其他人,他许下空头愿:你忠诚皇军,也不亏待你。鸦片加工厂将来还要重建,你还是厂长。目前他给徐梦人安排事做,原来守卫白狼山的日军调到前线去了,三江的宪兵人数锐减到最低数量,眼看大烟就要割浆,今年几个省的鸦片运到仓库来……白狼山仓库目前只猪骨左右卫门他们十几个人,剩下的全是满军,“你去同猪骨左右卫门中尉,一起守卫仓库。”
“是!”徐梦人去执行宪兵队长的命令。
林田数马叫来水野大尉密谋。
“徐德中?”水野惊讶道。
“徐梦人亲眼所见。”林田数马说。
“现在抓他?”
“不,即使抓,也要密捕……”林田数马说,“你亲自盯住徐德中,密查他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