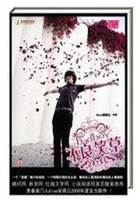新旧世纪的交替往往会造出某种历史性的奇观。历史在这个时刻往往也格外钟情于文学。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举步跨出了古典时代,新世纪赐予文学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新文学是那个世纪摇篮中的新生命。一百年过后,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的公正给我们以与我们的前辈均等的机会--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性。也许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文学的沉寂和热情的退潮不是一件坏事,它给原先为创新而疲于奔命的文学以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将有益于心理、情绪,以至创作思维和方式的调整。
告别80年代之后,觉醒的文学将拒绝非文学的行政性骚扰--尽管这种意图还无时不在--但拥有主体意识的文学会进一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拒绝那种意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名称来概括这阶段的文学。9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将摆脱充当某种附庸的地位。文学自身的规律将给文学的发展规定可能性,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由非文学的力量牵着走。我们始终希望,我们对文学阶段的划分和概括仅仅属于文学自身。
(原载《作家报》,1993年1月2日)
六、百年反思与文学期待
回望20世纪,在一片凄迷的暮色中,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带血的斜阳依稀映照着百年的呼号与呻吟。世纪的记忆原是血与泪的记忆。
苦难造就了丰富。要是没有这么多的追求与梦想,失败和屈辱,我们也许会为历史的贫乏而遗憾。但20世纪对中国来说的确是沉重的,这不仅由于苦难,也由于梦魇并没有在百年终了时隐退;人口的爆炸、资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如今仍是中国心灵的一团乱絮。
中国期待着一种认真的回望。也许今日的经济发展可以为失去自信心的中国提供刺激,但文化的偏离,它因无批判的“弘扬”所造成的旧习的卷土重来,已构成对现代进程的潜在威胁。回望也许无用而毕竟有益。至于可作为存在的思考的证实:我们曾经面对过历史的积重。
文学艺术向着商品的滑行现象令人吃惊。故作昂扬的应时之作与自甘沦落的插科打诨比比皆是,肤浅乃至卑俗的逗乐使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看上去都像是不入流的相声演员,整个的艺坛充斥着廉价的“绕口令”般的陋习,似乎人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耍嘴皮上了。
人们一面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五四”对于文化的过激行为的同时,一面却拱手恭迎当年被陈独秀、鲁迅等斥为“吃人”的那一套道德垃圾。有时,人们甚至因习惯成自然而说溜了嘴,连当年普通老百姓都为之不齿的“国粹”,也成了广告语汇般的口头禅。某种舆论倡导使“整理国故”一类的陈词滥调犹如时装表演那样到处走红。
文化的沦落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失去批判的锐气。现实的严酷遭遇使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中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伤害。于是,配合着商业文化的兴起,一些洁身自好的文化人选择了机智的避隐。他们一时忘却人间烟尘而躲进了“传统”这一安全可靠的隐蔽所。
然而,在艰难的时势中,我们的头顶垂挂着苍老的太阳。它时时提醒我们上面述及的那种百年中国的记忆。难道作为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却我们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层,忘却土层中的埋藏和郁积?
现实种种呼唤着“脱俗”的崇高的、有时却有点悲壮的投入。文学艺术诚然有其自身的律则,但它们对于切实人生的不可疏离却是始终的尊奉。人生和社会诸多的梦想或苦难,总是期待着文学艺术对它们有限的、甚至是无谓的承诺。
世间万象之中,文学也许是一种既聪明又“蠢笨”的事业。当仕途或经营造出了人生的繁华和喧腾,而文学却在寂寞的一角心甘情愿地品味着苦涩,有时甚至要承受惩罚和灾难。这营生始终与悲苦为伍,它的思考和不满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令人嫌恶的习性,而文学却毅然身负十字架流血于中途。
人们为追求欢愉尽可游戏而调笑,但他们不应以文学为工具。当生存成了严肃的甚至危险的话题,而恣意游戏文学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便难免尴尬。人间游戏场随处都有,习于此道者大可不必羁留这满布悲愁和苦难的殿堂。(原载《光明日报》,1995年3月28日)
七、开放的社会与开放的文学
尽管我们认定文学的创造总与个性化的思维以及个体性的运作有关,但文学也不能逃避社会精神和社会情绪的投射与反照的使命。文学作为个人的心音,它的亏盈和共鸣往往选择在更大的社会性空间中进行。与时代的脉动毫无关联的文学很难被确认真有价值。所谓文学的特性,是指文学与直接、抽象、概念化的说教无缘,文学总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体悟,传达出它的社会性的意愿、追求和憧憬。
有一种难以消除的误解认为,文学领域所发生一切都只与也仅仅只与个人有关。这从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看来是不确实的。最早的舞蹈因模仿狩猎对象以及表现狩猎的过程而兴起。最早的诗歌是情有所发而为浩叹以期影响群情的产物。到了近世,文学可以通过印刷得到发表,这却反过来证明了文学与社会不可脱离的性能。在形诸文字的与情感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严格地只与作者自身以及某个个人有关(如只为自己写的日记,以及只为特定的第二者看的情诗等)。就大部分的文学创作而言,自娱与感人两种品质总杂呈于创作及发表的过程中。也许创作的动机起于自娱,而发表的动机则归于感人。因此断然与社会隔绝的作品总是例外。
文学与社会的适应是双向的。从个人的动机看文学,作家希望社会不仅能够容纳并理解个人的特殊存在,而且能通过对作品的感知而接受作家对社会的召唤。从社会的意愿看文学,社会则希望作家通过他们的精神生产传达社会竭心的追求以及他希望取得的成果,从而展示社会的真实面貌。一个与世界沟通的开放的社会,当然希望通过作家的工作显示它可能到达的民主化程度、自由境界,以及它的开放性所带来的繁富。
因而,一个开放的社会理应要求一个开放的文学。社会总是渴望文学的张扬。这可以看做是社会的自私,也可以看做是社会的介意。当然,苛刻的社会为文学自由的付出可能极为悭吝。但文学的使命却不是等待施予。文学可做的事,只能是锲而不舍地坚持和争取。要求社会为文学作出慷慨的允诺和大跨度的让步毕竟近于奢侈,唯一的机会只在文学自身。
文学要解放人的心灵首先必须解放自身。开阔的视野、自在的心态、放松的情绪和从容的表达,将造就一个与开放的社会相适应的充满生机的文学形象。当然,仅此还不够,社会也必须在对文学的控制方面作出新的调整。首先,社会不能如同往常那样把文学看做是可以随意捏弄的面团,更不可把作家群体当做政敌。把文学家看做是随时都在酝酿和组织阴谋的那种心态是失常的。无可回旋的对于文学事业的僵硬态度以及无休止地向文学发动攻击的现象,只能发生在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而与一个健康社会无涉。
要是我们始终面对的是噤若寒蝉的作家和小心翼翼的文学,要是我们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随时都感到悬剑之危,他们所能创造的是什么?失去自由的作家创造的只能是失去自由的精神。那么,这一切的最直接的受损害者不会是别人,而只能是社会本身。一个声称酷爱正义和和平的民族,而它所拥有的却是随时都可能充当被告的“灵魂工程师”,这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原载《太原日报》,1993年2月1日)
八、无法拒绝的隐忧
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是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90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依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轰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明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久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在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忧时之作。19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掉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是他们要么漂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在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辞包装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但眼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到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目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某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得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笞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再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再到西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地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了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涵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面对不断制造出来的古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高精神的愤世嫉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原载《作家报》,1993年12月4日)
九、理想的召唤
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任,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出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应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在现实中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20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也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又何必苛求文学?况且,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开的精神劳作。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也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根本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本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乏,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大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就此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祈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原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