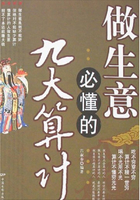中国新文学革命,最初瞩目于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效法。两大文学潮流迅速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所吸收,并融入了中国新文学的生命体而构成了新的传统。从郭沫若、徐志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生成和深入,而茅盾、巴金的作品,同样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除了展现实绩的力量,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启蒙的开拓力量。他对中国古文化了解最深刻,故批判最尖锐;由于深知此中积弊,故变革的意识最强烈,对于新潮的接引也最大胆。
中国新文学运动兴起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时间更为接近。许多现代主义大师当时正处于创造旺盛期,有的就是他们的同代人,但是由于中国文学当时的主要兴趣在于借用文学的力量以达到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因而或为人生而表现或为理想而疾呼,而对当时影响已烈的具有异质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不甚关注。对于现代主义的关注产生于新文学的创立立定脚跟之后。
全面开展的文学势态,使之有可能把视角转向新异艺术方式的寻求与借鉴上。这时对于艺术效用的关注超过了对于社会效用的关注。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象征派与中国现代派的实践方始起步。最早取法西方象征主义作诗的是留法的李金发。
他因写了与当时风尚迥异的作品而获得“诗怪”的称呼。从年至1927年,中国象征派诗歌实践,除李金发外,尚有由后期创造社转向象征主义倾向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以及姚蓬子、胡也频等。小说中的新感觉派因系间接自日本引进,故较诗的出现晚,但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1928年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起始。集合在这一刊物周围的撰稿人除刘呐鸥外,尚有戴望舒、徐霞村、施蛰存、杜衡,以及随后在《新文艺》上发表力作的穆时英等。这时的作品表现了以主观感觉印象和潜意识的着意刻画为特色的半殖民地都市的病态社会场景,体现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基本倾向。
世纪30年代初叶中国创立《现代》杂志,出现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诗人群,开始有力地推行现代派倾向的艺术实践。至此,中国诗歌始于李金发以至戴望舒,开始形成了一股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立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这一潮流的出现一直伴随着特殊而坎坷的命运。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民族的忧患、国计的艰危,社会现实不断提醒文学艺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觉悟。社会效用极高度的强调,驱使文学向着人生和社会的目标进一步逼进。审美的价值观成为非主要内容,文学的个人化和内心化则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现实的情势迫使文学作出抉择:即以停止诸多艺术渠道的开辟为代价的封闭式的抉择。此后在文学史中得到大量描述和肯定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即新的社会功利价值的概括,正是这一抉择的最简要的证明。从30年代后半期开始,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文学单一选择的结果,产生了一贯的批判命题:“为艺术而艺术”,其中对于现代派的宣判是与对于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宣判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叶的现代艺术思潮的兴起及消隐,是中国文学的“彗星现象”。中国几乎是自愿地放弃了与全世界艺术发展的同步性而自甘落伍(长时期以来,它视这种落伍为前进)。它把自己封固起来,闭目不看世界在若干年间脚步匆匆地向前走去。此后,虽有一些诗人,特别是40年代后期在大后方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中心开展的再度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活动,但毕竟是总体一致的格局中极少得到舆论支持的艺术支流而已--尽管其中一些文学现象在事隔若干年后的今日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中国由于自身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它采取摒绝有益于艺术自然生成与发展的决策,为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传播与发散,它宁取社会主义的单向选择而弃绝多向审美的寻求,这正是数十年来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样的情态之下,中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短暂的全方位展开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关闭了开放的形势。于是,便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大繁荣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长时间文学一体化之间造成了一个大裂谷。裂谷的两岸壁立千仞,它给予中国文学以封闭型的新特征。它终于成为中国呼唤艺术开放这一遥远的梦的潜在历史动因。
(二)觉醒:秩序的怀疑
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告别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由于自身的痛苦醒悟,再加上对于世界的了解,开始对已成定局的文学秩序产生怀疑。于是有了诸如上述那种魔盒的开启。中国文学进入年代后期的转向,对于已不新鲜的西方现代派思潮发生兴趣。这情景颇有点像学生补课。经过大动乱之后回归世界的中国,望着这世界的一切都有一种惊喜之感。这是一种需要,而不是某些偏见认为的那样是追求时髦的“时装表演”。
这种文学自身的内驱力,有点像20世纪英美诗中的意象派运动。它的跃起是对于当时统治英美诗坛后期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的反拨。当年极度繁荣的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20世纪已近尾声,它的因循刻板和华靡空洞加上陈旧的说教和抽象的抒情已使读者厌倦,这种厌倦创造了意象派兴起的契机。中国20世纪年代后期的形势与此有相似之处。50年代后期开始的“浪漫主义”诗风,历将近20年的时间沦落。它的最后装饰是千篇一律的华靡修饰。内容的脱离人间忧患和形式的僵硬单调,直接创造了艺术反抗的心理基础。
年爆发的“天安门运动”中群众广泛采用古典诗歌形式,说明了对于当时奉为圭臬的已有形式的摒弃,仓促间无以对应,只好采取了原已弃绝的形式。但随后开始的诗歌变革即朦胧诗运动,便广泛采用了接近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象诗,说明了对于业已异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及由此形成巨大约束力的艺术教条的反抗。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变革的动机,几乎都可以从艺术反抗主义这一原因得到解释。一种对于已有秩序的怀疑导致对于另一艺术世界的寻觅,于是出现了北岛、舒婷、顾城那一群令人惊骇的艺术反叛。读惯原先那种充满了矫情的甜得发腻的殿堂艺术的读者,如今猝然面对这样的句子和这样的表达方式:
地平线倾倒了
摇晃着,翻转过来
一只海鸥坠落而下
热血烫卷了硕大的蒲叶
那无所不在的夜色
遮掩了枪声
--这是禁地
这是自由的结局
沙地上插着一支羽毛的笔
带着微湿的气息
它属于颤抖的船弦和季节风
属于岸,属于雨的斜线
昨天或明天的太阳
如今却在这里
写下死亡所公证的秘密(北岛《岛》)
开始人们不免震惊,继而就能容忍并谅解。敏感的读者逐渐理解了这些新奇意象的组合“说”出了以往“说”不出的情绪和事实。心灵的重创、现实的复杂变形以及人们对这一切的纠缠不清的态度都在这里得到了传达的满足。
以诗歌的现代倾向付诸实践为发端,中国文学开始了超时空的向着“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大裂谷的对接。这种对接伴随着文化背景和文学观点差异而产生的大折磨,事实上修复了20世纪初叶开始的东西文化大交流的通道。中国为了挽救文学的人为衰颓,特别是解脱现实的大痛苦,重新向着西方现代文明燃起了引进火种的热情。这一切原都是古老的题目,但在噩梦醒来的人那里却获得了新鲜感。
把中国现时文学失去平静的经历解释成青年人的追求时髦,乃是一种不谙世事的焦躁心情的反映。一切都应从现实和历史的状态寻求根本的解释。这不是一般单纯照搬和模仿西方的现代派运动,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原因生成的艺术变革。这一运动当然受到了一种强大力量的驱使,那便是中国已经醒悟到自我禁锢,便是自我毁灭。中国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新的热情,与其说是由于对现代主义的兴趣,不如说是中国希望改变自己的世界弃儿的形象而重返世界的愿望的体现。在文化上和文学上,便是结束隔绝和要求沟通、吸取和融汇。
(三)荒园的“遥感”
中国的这一切自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因由。如同许多论着已阐释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现实的失望和精神危机更促进了现代主义的复苏和发展。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的失去皈依,普遍地呈现出社会的畸斜。暴力、吸毒以及笼罩天空的核阴云,使人们对现实失望。人对自身的存在感到荒唐,他们面对的是荒园。他们寻找精神的故乡但无所获。
在这基础之上诞生的艺术现象,再一次引起了中国的兴趣和同情。与“五四”那一次相比,这次对西方现代派的关注具有了更为强大的动因。“五四”是一种作为艺术全景介绍的不可缺少的必要,应当说,刚刚从封建桎梏挣脱出来的中国,完全缺少对于都市病的厌倦和反抗,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怀疑和仇视的条件。尽管当时中国由于年代的接近而“置身其中”,却缺少对此深切的感同身受的效果。而现在的中国,尽管时过境迁,却有着与这一文学思潮同向的理解的基础,这是一种“遥感”。
长达10年的社会动乱,加上比这还要长的年代里的社会禁锢,使中国噩梦醒后面对的是一片精神焦土,原先的罗曼蒂克的理想之光开始暗淡,急切间又不知路向何方伸展。以10年乃至20年为代价换来的失落感,人们开始寻找时间和希望。人口大膨胀造成的拥挤和摩擦,加之贪污和贿赂、陷阱和特权使人们在现实的积重面前感到了无能为力。社会的病态发展了人与人的吞噬和隔膜作为现代社会的孤独感亦随之而去。废墟的沉思和召唤、荒园的展延和凭吊、神圣的外壳剥落之后,人们发现了滑稽和荒诞。这些,都使中国与西方现代思潮产生了遥远的认同感。
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使中国与异时异地同时又是孕育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文学产生了“共振”。七八十年代之交产生的这一次中国向着西方的“盗火”行动,与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同,那次是全景展现与引进的文学自身的必然,而这次却是一次情感和理智的需要。
中国一方面感到旧有艺术方式的完全不能适应,另一方面感到这一曾经长时间发展但仍然新异的艺术方式对于表达特定阶段的社会、自然和人的谐调与适宜。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原先写着雍容典雅作品的那些已获得声誉作家的艺术变异。王蒙以《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深的湖》为起始,开始了新的艺术领域的开拓。他的杂乱无章、漫无头绪的叙述方式,使熟悉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情调,并对他的复出寄予厚望的读者大为吃惊。如下这样的一段文字是他们所热爱的小说家以前的作品中所未曾见到的:
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
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又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平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
陈杲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王蒙《夜的眼》)人们为这种不合章法的小说艺术而不安,不免异常深情地回想当年那个年轻的林震和同样年轻的赵惠文在飘满槐花清香的夜晚那抒情诗般的甜蜜的对话。那情景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正是《夜的眼》或《风筝飘带》中那种对于拥挤和焦灼的敏感,那种用不经心的调侃排解痛苦的睿智,从而显示了某种成熟的智慧。王蒙的创作倾向受到了广泛的关切,报刊开始讨论他的这种不合常规的艺术变异是否合理和是否值得。王蒙显然不在乎人们的七嘴八舌。作为一位成熟的作家,他已经觉察到以往艺术秩序中的弊端。他勇敢地迈出了一步。这一步是靠近了现代艺术的某些技巧,但显然不准备以放弃他的“少共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基石为代价。
另一位作家与她的处女作《红豆》都曾留给读者以雍容华贵的印象。在这个艺术新时期到来的时刻,她采取了比王蒙更为大胆的步骤,继获奖作品《弦上的梦》之后,宗璞写出了《我是谁》。不纯熟的,多少有点胆怯的借用变形的心理描写的方式,使她写出了一篇当时很引人注目的“怪小说”。在那里,人变成虫子:“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虽然它们并没有脸,她还是一眼便认出了熟人……它们大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却一本正经地爬着。”
驱使这些写出了优雅风格作品的作家,放弃甜蜜和美丽而趋向扭变和丑陋的,是一种比文学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现实生活的不宁和痛苦,使作家感到新的方式更贴切和更富表现力,这是一种“遥感”的力量。当然,这篇作品从卡夫卡类似的作品那里得到了启示,它在写实基础上的荒诞和变形,两种因素不和谐的相加造成了某种生硬和拼凑的感觉。
到了《泥沼中的头颅》,小说传达出来的无边沉闷和麻木、缠绕和黏糊、森森的冷气,竟让人想不到:
许多小虫顺着触角往上爬。“我们爬到你的头顶上,就也是思想家了。”它们仰着头大叫,小小的头很像甲虫,又像戴着面具。向上爬一段就变得更像人。有的爬得很快,变化的速度惊人。有的爬着爬着掉了下来,搅在泥浆里不见了。
头颅觉得自己正在腐烂。他必须从腐烂里挣扎出来。他大张了嘴,一面吐着涌进来的泥浆,一面大声喊叫:“我还要去找钥匙,好冲洗泥浆,你们不觉得不舒服么?”……头颅有些飘飘然,想要发表一通演说了。这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模糊的人形。这人形飘忽不定,忽而附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忽而凝聚为一个人,一个头颅从盘中跌出,一直向泥沼最深处落下去。
哈!四周涌来一阵笑声,这是看见人跌落时最时兴的伴奏。
可以看出这种非情节化的象征笔法,把十分沉痛的内容,托之以虚幻和荒诞,我们不难从爬行的小虫,爬得越高越像人,跌落的小虫在泥浆中消失,以及头颅跌落后笑的伴奏等看到倾轧、阴谋、陷阱以及冷漠无情。中国作家向着现代主义借取艺术经验的热情,受到痛苦的潜在要求的促使,他们感到唯此方能释放某种重压和积郁的深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