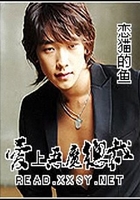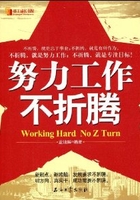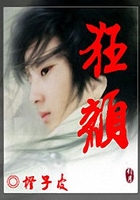文化的寻根因感到文化的匮缺而作出的补偿,其间当然表达了某种批判和扬弃的意愿。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如同郑义在《向往自由》中所描述的那种对于既定观念造成的既定秩序的厌恶和反抗。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反抗情绪支配之下,以逐步实现的热情终究在文学废墟之上重建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当然不是我们以往所习惯的那个样子。
(五)非禁欲的兴起
疏离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其范围相当广泛。它漫无际涯地冲击衡定的价值,终于以造成骚动而引起普遍的不安。全方位地反抗行动中不仅包含对大题材和大功利的疏远和否定,也包括了文学的情调和品格。自从文学受到一种观念的浸润和统驭,文学便迅速地附着于社会功利的母体。至此,文学不仅改变内容,而且也改变形式。多种风格急速地为一种统一的风格可取代,多种方法也受到规约。一种被派定为“最好的”方法驱逐了与之有异的方法。因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越来越严肃,也越有教育作用,慢慢地也就排斥了娱乐和审美的功效。
于是风格日趋僵硬。风格“硬”化的结果,造成了接受者的拒绝。于是文学复苏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对于“硬”化文学的反击。文学和艺术受到整个开放形势的鼓励,以及随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来的世界性现代文明的影响,在获得自由之后便是对于上述秩序的否定。这种否定的方式于是推进文学艺术的“软”化。
文艺软化现象其实即是刚雄之气的减弱和轻柔之风的增长。事情似乎可以追溯到一些大型歌舞节目的演出,那时引起轰动的是华彩的场面、鲜丽的服饰、迷乱耳目的音色。这一切似乎是对于刻板僵硬的着意反抗,但获得了成功。禁锢甚久的“严肃”化了的艺术禁欲主义,一下子找到了非禁欲意识的突破口。艺术原先的被忘却的目的和形态得到了新的承认。这时,宣传的唯一目的性便受到合理的怀疑,“非宣传”的意向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前台。艺术的开放不会不受到阻隔,但却难以抗拒。李谷一一曲《乡恋》从词、曲乃至演唱,都是一个无言的挑战。起而反对这一现象的,大都是素有名望的权威。《乡恋》以缠绵的柔情牵动人心,再加上新颖的发声,它让人感到亲切是自然的,因为与前不同。传统的评判使它一度受禁。然而艺术的“野性”却从此萌动。邓丽君的歌声以完全让人兴奋的内涵和形式蜚声艺坛,于是渐有危言,邓小姐也因而在过度风靡之下受到委屈。此后,轮到了程琳。她早露的才华受到年龄数倍于她的长者不适量的严责及至奚落。
但门户的大开受到既定国策的支持。中国国门并不单为经济交往而开放。文化风的流通本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但文化警觉的偏见极为深刻。从来的阶级批判与“纯化”的选择性机制,并不因开放政策的制定而受到任何挫折。于是,新的困惑和烦恼带来了连续性的震撼。间歇性的抑制往往借取政治的或准政治的方法进行。这种抑制无可置疑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不仅仅是艺术或文化的),但抑制的要求和行动却不曾断绝。因为是经济开放的补偿的需要,文学一如往昔,乃是平衡天平的重要砝码。它的价值是非文学的。
一位诗人的诗句谈到了阻隔东方和西方的有形的墙。但无形的墙似乎更为坚固和顽健。不论有形还是无形,作为墙并不能阻挡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也不能阻挡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文学的“硬质”(这种硬质的重要构因是文学艺术的高度政治化和宣传功效的强调。长期教条化的结果,是它的居高临下的训示习惯)在弱化。从金庸到琼瑶,文学的娱乐性因它的商品品格而受到社会无形的保护。通俗文学的兴起是“软”文学发达的重要的标志,通俗文学的大发展的态势引起的惊惶带有某种夸张的性质。原有文学的无挑战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它意味着一个单一的文化消费市场的消失。
最突出也最惊人的现象是军歌的软化。对于这一现象的叙述似乎应追溯到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当然,这主要是词曲的风格,而主要不是由于她的演唱风格):海风轻吹,海浪轻摇……过去威武雄壮的人民水兵在前进的动态的钢铁旋律,如今却化为了梦境的浅唱低吟。这当然不是一种个别的偶发现象,而是一种自然的反拨的流向。早在《闪闪的红星》中,李双江的演唱体现了男性不常有的柔婉,他的颤音的装饰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当日硬邦邦的乐音舞态中,这当然是迷人的。《再见吧,妈妈》的凄迷缠绵,创造了一个高峰现象。
还有《泉水叮咚响》,因寄传统的诗情于委婉而风靡全国。
现行军歌中历久不衰的两首:《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其动人心弦的魅力原是人情的温软所造成。人们容易发问:坚强雄壮的队列歌曲哪里去了?甚至进而质问:为什么这些歌曲全受到一路绿灯的优厚待遇?但是需要提醒这些质问者的是,一种文化逆反的潜心理并非一日所能形成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惩罚。它不意味着全部的合理性,但却有效地证明了不合理性。应该承认文学和艺术的生态平衡受到了长期的人为破坏。文学艺术沿着一条极端的路走得太远了,便造出这样一个畸形的发展。它自掘坟墓。无视文艺自有品性以及粗暴的强加,是导致这一悲剧结局的基因。
不能说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悲剧的因素并未泯除。例如迄今为止尚在津津有味地演唱、演奏或演出“打虎上山”之类的文艺怪胎所体现出来的怪癖好便是一例。不论正直或正义的舆论如何愤怒地呼吁禁止这种恶习,而演者兀自演出,动肝火者依然动肝火。1988年2月8日首都作家、艺术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迎春联欢,第一个节目中便有“打虎上山”。这种“拧着来”说明一种顽症。由此我们亦可理解那种更加顽强的对于秩序的反抗,它不是一种偶发现象,而是受到了中国文艺现实约定的愤激的实现热情的驱遣。既然它的产生不可阻扼,则它的存在亦不可抗拒。
(六)破坏与平衡的重建
文学的疏离化现象是中国文坛的特产,但受到了文艺一般规律的约定。一个社会的文艺若长期受到非艺术因素的干预,甚至由于褊狭意愿的驱使而提倡或扶植某一特定品类而抑制其他,文艺的生态就会被破坏。其结果是事与愿违,文艺因片面的社会提倡而彻底地背叛了社会,并脱离它的接受者。文艺于是成为一座孤岛。它只能依靠行政力量生存而无法自立。
结果是由文艺自身来纠正这一病态发展。它的第一步便是平衡的重建。这种重建首先要求弥补以往的缺陷。为此,就要打破以往的衡定秩序。批判的目光是一种必要,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反抗也是一种必要。这就产生了以上所述的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对于原有文学生态的脱节和疏远。为了矫正历史的偏离和误差,它往往采取偏激乃至反叛的姿态。这种反叛造成的积极结果,便是长期受到压抑和制裁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实践的恢复。
这种反抗的补充目标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抗争。要是没有整个社会发展态势的支持,它也不会奏效。中国文艺新时期以来十年发展中的纠偏与反纠偏、运动与反运动的矫正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秩序的反抗造成了某种补偿,但并不等于秩序的重建,它只是一种矫正和修复。
它自身不说明合理性,但它的行为却是合理的。以上述及的几个方面,我们均可确认其为成就,亦可确认其为不同程度的偏颇。从每一个实践看,疏离都是合理的,但疏离又造成了新的不合理。例如非政治化对于极端政治化是合理的,但若因此而无视国计民生,所有的文艺都去营造自身的象牙塔,便是一种新的失衡。寻根若是一种寻觅的求索,以求疗治民族之劣根性于万一,其积极用心可感天地。但若是由于文艺生计的艰危而唯求逃遁,则消极之心意显而易见。据此类推,所有的文学都板着面孔得了“硬化症”当然是病态;若为了反抗这种病态而一味地浓抹脂粉,满身珠宝而全面“雌化”,则委靡之音不足以兴国安邦,却也是一种灾难。
总而言之,秩序并不因反抗而建立。反抗是一个过程,建立也是一个过程。
七、从现代更新到多向寻求
(一)秩序的网仿佛是一个梦游者,中国文学在自己的深厚传统造成的梦的迷宫中冲撞。那迷宫布满了无边而坚韧的无形之网,以无所不在的笼罩与涵盖,束缚了这个渴望自由但又无法到达这个自由的梦游者。几乎每一投足都是一次冒险,几乎每一步都是超越规范的试探,都可能发生地震--除非你只按照前人和他人为你规定的方格行走。
传统是一种强大的存在。但传统又是一种脆弱的存在。它不期望对它进行任何的怀疑,它对任何的不驯都心怀警觉。这已成为全民族的心理积淀。每一个属于此民族的分子,都成了一个“白血球”,面对每一个“入侵者”,它都会为了维护这个母体而扑向前去。在中国,可以把传统的逆子先歪曲成传统的护卫者,最后再把他塑造成传统的偶像。此种现象已非仅见。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大泥潭的博大之处。它可以把投入的一切变成了同样的一团糨糊。一旦偶像的塑造完成,它便以保卫一切传统偶像的韧性来保卫这个新创的偶像。
鲁迅生前受到围攻和危害并不是他的灾难,鲁迅死后的被捧为偶像才是这位战士真正的悲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鲁迅与孔子一样成为了圣人,同样被供进了圣贤祠。以至于在每一个有关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位当今圣人都会受到邀请,讲一些支持邀请者的行为的“关键”的话。尽管这些邀请者所作所为可能是历史的逆动,例如所谓的“反克己复礼”、“批林批孔”,等等。对这位圣人从奉的香火自然是永恒的赞美诗,甚至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也不允许存在对他的批评乃至腹诽。
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却难以保持这个恒定。《青海湖》--这是一个并不出名也很少引起注意的刊物,于1985年第期发表了一篇从作者署名到内容都令人陌生的文章:《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仅仅因为是对鲁迅的生平作品谈了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因此便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事件”。据说此文引起了比文学界更为广泛的方面的关注,各报刊纷纷刊出名家对这个小人物进行的“讨论”。现在我们可以退一万步来看这一事件,即使该小人物所写的小文章全都是错的,且不论这一篇文章与成千上万的赞扬肯定的文章相比究竟会不会对鲁迅造成损害,单就究竟有没有谈论、乃至非议鲁迅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提出质问,便深觉此中的大谬。
几乎谁都无法挣脱这个网。这个文学秩序由久远的因素所促成,但一路流去,却添加了许许多多的沉积物。这个传统到了现在便成了混杂而难以辨清的统一体。它自相矛盾,又以不容讨论的面目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例如《在社会档案里》的受挫,据说是由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那么,作家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责任感才投入对于“社会档案”的探求吗?这真是一个中国式的永远弄不清的文学怪圈。这一类作品的“触雷”不足为奇,因为它对已成定式的颂歌模式不自觉反抗,必然引发更为强大的反抗力量。在这个网中,一切已经被确认的秩序,都必然带有真理的性质。既然如此,它就是不容怀疑的,不论这种秩序是由权威或是非权威规定。90年代,淹没已久的新月派重要人物徐志摩的诗集出版,并有人为此作出新的评价。紧接着便有人不以为然,其原因即:关于徐志摩的评价,前二三十年已有某要人作过结论云云。这种思维方式从来不被怀疑。以至于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美学家朱光潜,因为说了句“国外熟悉的中国作家只有老舍、从文”而遭到报复。人们不禁要据此发问:一位年愈八旬的文坛宿老,难道连这样自如地而又委婉地转述一个小小见解的权利都要受到干涉么?究竟是什么一种心理动机触发了如此不见容的褊狭?的确很难说这种文化性格是不是丑陋的。它造成了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的封闭。向后看的墨守前例和成规,被视为是正常的,而怀疑已有的结论却被视之为失常。
(二)传统文化心理面临挑战
幸好这种局面已面临危机。文学伴随着时代的觉醒已开始不安的冲撞。这形势犹如白桦那首着名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所宣告的:“觉醒的鹰”已不能忍受那约束它血肉之躯的“蛋壳”,它正在用嘴啄破那层薄壁,它的翅膀要挣扎,那有形、无形的网:
一点就破呀云海茫茫,太空蔚蓝,我们的翅膀原来可以得到那么强大的风,就在这透明的薄壁外边,再使点劲就冲破了!
我们就会有一个比现在无限大的空间。
这只不满“蛋壳”的鹰的觉醒,是由于外面世界迷人的阳光的吸引。它曾经习惯于黑暗,如今受到了光亮这个魔鬼的引诱。如同吃了禁果,人终于能够像人那样活着,但禁果也是那个恶魔引诱的。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觉醒,就是由于这种引诱。那时没有选择,也无所谓挑选。于是各色影响一起涌进,犹如八面来风充斥了这间黑暗的老屋。于是霉腐之气全被冲走,清新的风充满了整个空间。中国文学家们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市场上自由地挑选自己心爱的物件。于是冰心认识了泰戈尔,鲁迅认识了契诃夫,郭沫若认识了惠特曼。
那时,我们的视野向着世界开放,没有人来跟我们饶舌,说此人可以亲近,彼人可恶;说此书可以招财进宝,彼书则使人晦气倒霉;健康的还是有毒素的全由挑选者自行选择。那时并没有产生乱子,反倒繁荣了中国文坛。西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一切,由于不怀偏见的自由择取,反倒造就了一代中国作家的审美情操和艺术素养。我们吸收食物的肠胃也在这种“遍尝百草”的实践中锻炼得异常强旺。中国也并没有在这种兼收并蓄中变成“殖民地”。民族的品质也未曾沦亡,没有忘记了祖宗,更没有“亡党亡国”。
随后我们开始挑食,继而因为害怕不卫生,害怕病从口入而忌食,我们于是开始营养不良,继而开始贫血。因为我们“净化”食物的结果,造成了过多的营养补给的短缺。正如前面述及的由于交流的褊狭选择,造成了文学的贫困。这使中国文学这个贫血的婴儿,产生了严重的发育不良症。这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如今已成了重要的经验为今人所记取。
这次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域外的世界。我们的心态已经适应了当前世界总的发展格局,即第二次浪潮的标准化所产生的文学的单一选择已告结束。我们乐于接受如下的新概念:“艺术多种选择的缪斯。”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多种多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