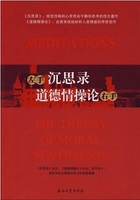一个民族的生命更新,在于它清醒地意识到对自身现状并有所不满,从此萌发自我否定的意愿。这种热情的火种来自20世纪初叶那次为凤凰涅盘而点燃的冲天烈焰。我们迎接的是一个为死亡中的新生而欢唱,为创造精神在烈火中再生而欢唱的时代。
我们显然为一个突然降临的巨大喜悦所震慑。我们为它给予的重新生活的权利而感激万端,如同随后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公社党委书记钱金贵,当人们告知他已官复原职时的反应是:“他捂着脸哭起来”,口齿不清地嗫嚅着,“到底证明我是好……好人,我感谢党!”(杨干华《惊蛰雷》)感谢之后他依然按照他以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和思维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当他如同当年进入大城市不能忍受香水和坐在一条长椅上的亲热的男女那样不能忍受开始跃动的新生活,他终于给自己做了一间小小的木屋,把自己装进了小小的幽闭的盒子。这一情节是极富象征意味的。
这篇小说把钱金贵的这种旧轨道运行归结为伪装革命者的引诱和破坏,即归结为唯一的政治的因素。其实这乃是中国国民性中劣质的顽固表现。在近些年中国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探讨中有人认为,中国人的人格属于归属型。这种形态指当需要的优势达到归属的目标后,由于社会结构的限制,便往往不再进取。
这是一种萎缩性的人格。历史上不少有志之士,一旦需要有了归属,便自行萎缩。这种人格的畸形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
“四五运动”开启了民族的灵智。社会一旦打开了窗口,外面清新的风装填了原先充满霉腐气息的房间,空气开始流通。于是这种归属感便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格中产生了变化,那种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自主的人权意识、竞争精神和效率观念为标志的自尊型人格开始生成。
显然,这种对于“四五运动”的潜在伟大意蕴的自觉,只是以后的事。在文学领域,一旦禁锢宣告解除,那种归属型的文化性格便重新显示出传统的力量。人们开始为恢复旧物而斗争。于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模式重新成为膜拜的对象,人们认之为文艺的黄金时代。于是文学的怀旧病开始传染和流行。
回想那时的文艺潮流,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情感流动。首先是为当时自天而降的胜利狂欢,欢庆新的十月,用的是腰鼓、秧歌乃至高跷的古老方式。接着便是悼念刚刚去世的领袖,每一次的演出和朗诵都伴随着欷歔和掌声。接着,是怀想那些去世更早的革命老人。一个一个地写,一直写到当时还没有恢复名誉的“沉黑的安源山”。人们在这些怀想之中初步获得了对于失去的记忆的情感满足。
接着,开始了更为“古老”的情感追求。千家万户从“洪湖水,浪打浪”开始唱,一直唱到久别的《兄妹开荒》。那种为争当劳模的人为的误会和调侃,那些已变得异常陌生的陕北高原的开荒场面引起了轰动性的兴趣。郭兰英成了最风行的歌星。她从《绣金匾》一直唱到“北风吹,雪花飘”。一方面是禁锢太久,饥渴也太久,人们翻箱倒柜把能够满足食欲的东西统统挖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这是更为潜在也更为强大的磁石般的“内驱力”,它把一切的欲念都吸引到那个最永恒的神秘的所在。
文艺的全面复苏,表现在对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文艺遗址的全面开掘。我们的欢乐旋风是一种旧梦的寻觅。我们开始手忙脚乱地清理遗产,并且发掘革命古董。油画《开国大典》,去掉一两个人像,修修补补,重新出版。我们唱《南泥湾》,唱《翻身道情》,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凡是记得起来、找得到的,我们都要搜集、寻找,而且按照原来的样子重建生活。
到1978年,我们沉浸在一片恢复旧物的激情之中。
凡是历史证明是好的,凡是伟大的人物说过的、规定的和肯定的,就应当让它重新出现。文艺曾经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恢复它曾经有的样子。我们当年的激情也是一种历史惰性的大发扬。
这一段文艺的怀旧思潮,把本应开始的文艺变革的心理准备加以消极的导向。人们的目光投向过去的文艺,人们重新向着那个曾经造成巨大窒息的文艺范式认同。
接着是无法回避的文学惯性滑行的阶段。人们开始把文学真实性的恢复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总目标联系起来。《假如我是真的》究竟还是真的,但真的也不行。因为联系上政治,即使是真的也要考虑“社会效果”。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论发明的估价,恐怕要留给后代人,社会效果即政治这样真实性的实现又在原先受阻的政治闸门前再次受阻。对《将军,不能这样做》最为有力的质疑便是:你究竟说的是谁?你说的动用多少外汇经得起纪检部门的检查吗?诗人毕竟是诗人,他一旦遇到了这样的胡搅蛮缠,最后的出路只能是:放弃辩论。当然,诗人也有愚钝之处,他也把诗看成了真实性的反映,他那时不会承认:诗人如同上帝,他可以创造天,创造地,创造男人和女人,创造世界。他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诗人只崇拜自己的良知和心灵;诗人不负责说明和解释。这是那一代、那一类诗人的悲哀。
五、人性--从废墟醒来的灵魂
(一)别无选择的选择
文学的社会功能对于中国作家几乎是一块富有魅力的磁石。不论你处于何种方位,这块永恒而神秘的磁石总会把你引向它的身边。处于时代大转折的通衢之口,文学本身有多种选择的可能,但是中国作家不假思索地把文学这艘久经风浪的船驶向了曾给文学带来诸多磨难的河道。
定向的思维告诉人们:你别无选择。因为固有的价值判断认为舍此文学便失去了它的庄严。这样,动乱结束以后的重建,可以说是一种不同时期的重复。不同的是,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充填和更新以往那种失真的乃至虚假的社会文学。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之舟曾在这条河道几遭没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给予文学参与社会的自由度是非常有限的。文学没有自由港,只有当你把文学置于肯定意识笼罩下,用于履行颂歌的职能时,社会方给文学以自由,反之则得不到自由。《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所触及的,不过是美好生活最初投出的一道阴影,而且是那样的轻浅。那无非是一个由几位口头挂着或不挂着“就那么回事”的干部组成的区委会,以及与之力量悬殊的两位年轻人的向着小小的(对比以后的现实确是“小小的”)官僚主义的冲撞。林震对“就那么回事”的回答,显示出青年的天真的锐气:“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真地去对待一切。正因为这样,所以“看见了不合理的事,就不要容忍,就要一次两次三次地斗争到底,一直到事情改变了为止。所以决不要灰心丧气……”
林震正是当年的作家王蒙。只因为这篇小说的作者没有温驯地向着生活发出甜蜜的礼赞,他受到了惩罚。还可以举出无数这样受到惩罚的例证,但并无多大意义。最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对着几道阴影的大惊小怪,从来也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随之而来的复仇女神却显得异常的无情。当年许多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干预,大抵都采取了委婉的方式,并不是如后来蜂拥而上的批判说的那样怀有“刻骨的仇恨”。有的作品甚至只是一种学术性论点的阐发,并没有触及生活的真实,但招来的报复却十分残忍。最富戏剧性的是王昌定的《创作需要才能》的遭遇,3000字付出了蒙受3000天苦难的代价。
但中国的作家对此的回答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白烨语),是梁南的《我不怨恨》:
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这种单恋式的苦苦的“爱情”,成为中国一代作家的最突出的品质。当然,这种品质也体现出受扭曲的性格特征。不论它是如何地受扭曲,它的执着却极其动人。现实主义简直是一位让人疯魔的爱神,被它愚弄,乃至被它坑陷,却又被受到不公正待遇者一往情深地迷恋。获得解放的中国作家依然致力于一种现实热情,那就是把远离大地而飘浮于太空的那个现实主义星球变为现实的存在。作家开始的社会文学的争取,其动力的神秘性即源于此。
从落实各项政策给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到及时再现改革面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参与和加入,为文学赢得了新的声誉。这一时期从小说《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到《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到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请举起森林般的手臂,制止!》,再到电视连续剧《新星》,这些作品都以及时而大胆地表现国计民生以及民众的呼声而激动了全社会,由此也鼓舞了作家的信心,并促成他们为此次事业坚持的决心。一批中年作家作为当时创作实力中坚都体现了这种坚持的韧性,以至于当这种创作的稳固地位和重要性受到忽视时,他们表示出来的愤懑并非不可理解。
当时盛行的切入社会的文学以涉及揭露伤痕的作品收效最显着。这类作品,散文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小说如卢新华的《伤痕》,诗如林希的《无名河》、李发模的《呼声》,戏剧如《WM》都是以求唤起人们的同声一哭。这类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只限于揭露和控诉。这些作品被称为问题小说,说明它们在触及社会存在的问题时有独到的价值。当然也有缺陷,即往往不能深掘下去,接触历史的根由。陈忠实的《信任》写旧日农村中的恩仇推延至下一代,由于其中一位过去挨整今日掌权的支部书记罗坤的不记私仇的大度,以及人情的感化,终于使两家言归于好,全村复归于团结。《妈妈的死》(高尔品,即辛颢年)就是这种社会功利目的的坚持的结果。“妈妈像绷紧的琴弦突然断了一样松开手,瘫痪了,两只眼睛睁大着,盯住墙上,眼珠发直,一动不动,白发披散在脸上。”在那个年代,由失手摔破石膏像,到再度念错人名陷入自责与他责交迫之中,最后因精神全面崩溃而死亡的悲剧,却是无数真实事件中的一件。《妈妈的死》把原是荒诞的作品写成了问题小说,正是当时一批问题小说共同存在的现象。
可以认为,由于文学观念的约束,作家失去了许多可以创作更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的机会。《妈妈的死》这篇小说的结尾所透出的“理性的阳光”,留给人的艺术局限的遗憾:“我原来只觉得妈妈的遭遇很悲惨,后来看了一些指斥‘现代迷信’的文章,这悲惨又添了一层意思,我们像白痴一样,受林彪、‘四人帮’愚弄!透过重重阴霾,一线理性的阳光,照射着我的灵魂。”
至此我们得知,仅仅从政治事件的角度,而没有更为深广的视野,许多“问题”是难以获得“理性”的认识的。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用另一种方式审视我们曾经经历和如今面临的一切,特别未曾认识到人应当面对自身,民族应当面对自身。
(二)颠倒历史的颠倒
“伤痕文学”沿着社会和政治的轨道滑行,竟然创造了奇迹。
由控诉暴虐野蛮进而抚摸自身的伤痕,乃是自然而然的导向,但它却不经意地点燃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之光:一颗温热的心在黑暗中跳动,无数卑微的小人物,开始胆怯地、小心翼翼地出现,并悄悄地进入了文学的很多领域。一颗又一颗受伤的灵魂,一个又一个饱经离乱的家庭,灯下烛前,痛定思痛,感慨欷歔。从鲜花到墓场,又从墓场到鲜花,历史在这个不久的时间内,演出了无数感天动地的“六月雪-窦娥冤”“凡人琐事”冲向了旧日只有头上显示光圈的英雄和神占领的文学圣殿。历史无疑地开始了一个大颠倒。这样,不是靠一种理论的驳难,例如对于“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和矫正,而是靠文学的事实,实行了堂堂皇皇的占领。这个占领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巨效--它由倾诉苦难而唤起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远远地指向了人、人的价值及人应有的尊严。
从这个视点来看《妈妈的死》,导致主人公的死亡的除了政治性的逼迫之外,人性的歪曲和泯灭,人在神的光焰之下自我价值的萎缩,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触及。诗歌禁锢最严,但又是反抗最早的艺术品种。它也有一个在社会-政治传统轨道进行惯性滑行的时期,也有各式各样的欢呼和控诉,正是这种欢呼与控诉,构筑起诗歌的凯旋门。
但刚一通过这个情绪激昂的凯旋门,艾青便发现了一条僵成了化石的鱼。《鱼化石》是诗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的凝聚,他把曾经是活泼泼的生命置放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异变之中--也许由于地震,也许是火山爆发,其实不止是一条鱼,而是把无数的鱼变成了化石。曾卓此时发表的《悬崖边的树》,这棵“保留了风的形象”的树,也是受一股“不知从哪里刮来的风”的摧残构成的树的化石。
要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流沙河的《草木篇》和《白杨》等篇章因有异于统一规范的意象而体现他的个性化创造,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则因全面地倾诉个人和家庭的苦难而开启了诗歌“归来”主题的闸门。灾难中的爱情的温暖,受监视的惨淡的婚礼,受屈辱的父母对于儿子的伤心和抚慰。从“九咏故园”到让人震动的《妻颂》,流沙河这个时期的创作重现了50年代的个性光辉。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创作的贡献,是把那一块块“化石”和“出土文物”具象化了。他融进了个人的亲属的悲欢之泪和痛苦之忆,依然是化石,却赋予它以丰满的情感血肉。流沙河最动人的一块“化石”是他的《哄小儿》:
爸爸变了棚中牛,
今日又变家中马。
笑跪床上四蹄爬,
乖乖儿快来骑马!
…………
莫要跑到门外去,
去到门外有人骂,
只怪爸爸连累你,
乖乖儿,快用鞭子打!
这是弱者的人格在受屈的环境中自尊的显示:宁肯给儿子当马骑,以受鞭打换取儿辈惨淡的快乐,也不愿在外受辱。人格终于在血泪的浸泡中觉醒。
所以,新时代人的觉醒的大潮是一个不期而至的快乐的实现。它由抚摸伤痕引发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验与审视。中国人普遍地发现自己活得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十分异常。这时,那暗屋破漏的一角传来了外面的丽日熏风,发现别人都活得不坏,于是悲凉之感顿生……舒婷在《青春诗会诗序》中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关于人自身、关于人与他人关系的呼吁:“人啊,理解我吧。”……她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表达我对‘人’的一种关切。”这位青年诗人视真诚为改善人际关系的至要,她对此显然怀有信心:“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
动乱年代,文化受到了血洗,文明受到了摧毁。但受害最深的还是人--人变成了非人、鬼、兽。中国文学界关于人的价值的再认识和对于人性的尊重的呼唤,比哲学界、思想界更为敏感。诗人不合常规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冬末滚过灰暗天边的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