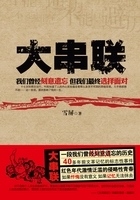陶羊子与任秋的婚礼在钟园举行。任秋希望热闹,任守一喜欢清静。结婚图喜庆,任守一听由任秋往热闹里办。除了任守一,陶羊子与任秋在南城都没有别的亲人。陶羊子请了女老板和胡桃来帮忙。
胡桃与任秋已经十分要好。他一口一个嫂子,满嘴甜密的话。任秋本来觉得胡桃不正经,不是个好人,但多接触了他,慢慢地喜欢上了他夸张滑稽的腔调,也喜欢听他的预言式的话,有事常吩咐他去做。
女老板租了一辆马车,用红布把车篷裹上。由胡桃驾车把任秋从小院里接出来,来到小巷。陶羊子在小巷后楼里取了衣物还有那副棋,再陪同新娘转回到小院去。到一处便爆竹鞭炮齐响。
穿着大红嫁衣的任秋与穿着长衫的陶羊子并肩走下车。胡桃在后面跟着。他凑个空在任秋耳边说:“我以后只叫你姐姐。因为我一直陪着你,算是你娘家一路人。羊子哥啊,只是入赘进来的姐夫。”
任秋咯咯地笑着,笑得很响。端坐在屋里的任守一默默地看着这情景,慢慢地眼皮垂下,念了一声佛。他也许不太合尘世的热闹情景了。
胡桃大言炎炎地讲着:“结婚讲究吉庆。今天就有吉庆兆头。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一片红光,红得灿烂,红得光辉。注定红透,红到头的。”
大家都笑。陶羊子注意到,任守一又朝这里望一眼,接着垂头合掌。
钟园的酒席摆了三桌。有女老板和任秋的邻居,胡桃和两个小兄弟,还有常在钟园出进的棋人。围棋研究会的棋士和一些有身份的棋友早已接到方天勤的请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了。
梅若云来了。她带来了秦时月送的一套西装,还有一条苏绣纱巾。她文静大方地走到陶羊子面前,说着庆贺的话。陶羊子默默地看着她。陶羊子给秦时月的请柬上写着的是秦时月及夫人。作为同学,他应该给她单发个请柬。现在她作为秦时月的夫人坦然而来,陶羊子不免有点愧意,自己对梅若云,也许一直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
胡桃却叫着:“秦二夫人来了。秦老爷呢?”
胡桃与任秋关系好了,他见到陶羊子与梅若云的神情,便有一点要为任秋讨公道的意味。
梅若云对陶羊子轻声说:“他会来。只是他早接到了方天勤的请柬。”
梅若云的口气分明在为丈夫作辩解。陶羊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任秋与邻居说着话,只是眼瞥过来看了一下。
进行拜堂仪式。司仪是胡桃执意担当的,他学了好久的贺辞,说得喜庆。最后说到送入洞房,但无洞房可送,只是请大家入席。
梅若云靠近任守一旁边,只是中间空了一个位置。
坐下来后,梅若云朝陶羊子说了一句:“那包礼物是秦时月送的,我没有再准备……我给婚礼送上一曲吧。”说着,打开了身后一直背着的布包,里面是一把琵琶。任守一眼光闪亮了一下,陶羊子知道岳父是很懂音乐的。
拨指一弹,琵琶声起,本来四下里闹哄哄的,立刻静了下来。这首贺婚琵琶曲弹得喜庆欢快,所有的人都被迷住了。不知为什么,陶羊子感觉那是她为他一个人弹的。陶羊子并不太懂音乐,却在欢庆的曲子里仿佛听到了一丝冷清,仿佛在诉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一直没有说话的任守一,对弹完琴的梅若云说了一句:“夫人真是神仙般人物,琴音之中自有慧根。”
梅若云听陶羊子讲过他的师父,很敬重地低了一点头,说了一声:“谢谢师父。”她用了师父的称呼,仿佛是求教于他,又仿佛跟着陶羊子称呼的。只是陶羊子现在已经改称爹爹了。
说秦时月会来,陶羊子还有点疑惑。但很快秦时月就来了,入席便拱手致歉。陶羊子很感激他,他毕竟还是来了。
秦时月本来想和梅若云直接来陶羊子这里。只是秦夫人看到方天勤的请柬,说要去参加。秦时月只有带着秦夫人去那里了。方天勤的婚礼开始,秦时月就把秦夫人留下,代他喝酒。他又赶到钟园这边来。他与方天勤只是在社交场合认识,与陶羊子关系要深得多了,况且这里还有梅若云在。
秦时月坐在了任守一的旁边。这是陶羊子安排的,他想让学贯中西的秦时月与岳父聊上一聊。
但是任守一又如以往低首半闭眼的状态。秦时月听陶羊子介绍,很热情地与他招呼,任守一也只是应着一声。
陶羊子想到任师父自妻子去世后一直单人生活,大概对有着二夫人的秦时月感觉不入眼吧。
秦时月在席上说:“我在那边参加了一场完全新式的婚礼,又来这里参加一场旧式的婚礼。”
旁边有人问:“你以为哪一种更有意思?”
秦时月笑答:“我看,各自所爱。如黑如白,也各有所得。”秦时月显得很能说。他左侧的任守一只顾低眼低眉,似乎在心里念着佛。他右侧的梅若云也是低眼低眉,似乎不胜酒力。
婚礼热闹也累人,钟园的婚宴结束,送新婚夫妻到小院,又在楼上新房里闹了一会,众人走了。终于,只有新郎独自面对新娘。想着执子之手与之偕老,陶羊子心中有着带有永恒的期待。
任秋喝了一点酒,脸红红的。陶羊子也喝了一些酒,头虽有点晕乎乎,心里还是清楚的。他乘着酒兴鼓足勇气坐到任秋身边。任秋移了移身子。陶羊子心想,她应该是他的妻子了,便伸手一把抱住她,并用另一只手按到她的胸脯上。任秋朝他瞪了一眼,晃了晃身子,大概发现她无法摆脱他,也就由他了。想不到这个老实男人也会这样。
陶羊子泄了一点气,松手对任秋说:“我们睡觉吧。”
任秋让陶羊子先躺到床上。她到床后马桶处摸索了一会,又去卸妆取头饰。隔了好一阵,她才上床。脱了外衣,躺了下来。陶羊子伸手去帮她解内衣。任秋按住了他的手:“你怎么?”
陶羊子说:“我怎么呢?”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多少年养成的君子模样此时就像画皮一样脱落了,不由分说地动作着,有点急乎乎的。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她,只顾把手伸到她的内衣里去。一个新鲜的,软乎乎的,暖乎乎的感受“嗖”的一下钻进他的感觉,又“轰”的一下传遍浑身上下。整片的快感带着痛楚似地涨满他的内心,淹没了所有的意识。
接下去的一切,是他想到过但绝对想不到的,那想到的仿佛是梦中才有的,没想到的是想象中根本不存在的。一切似乎都不对头,他像对着一片空白的棋盘,不知如何下子,又像是对着满盘的黑白棋,同样无法下子。最后,他在盘外把子投了。
他在她身体之上而不是身体之内泄了。
任秋一声不响躺在那里,看看他,由着他。随后抬腰皱眉朝下面看看,宽容地擦净了自己。陶羊子也讪讪地去擦洗了。于是两人重新躺倒下来。她由着他抱住,向下埋埋身体,伏在他身边睡了。
陶羊子却很长时间因不习惯而未入睡。她的声息悠长,带着一点轻轻的呼声,合着的眼睫毛长长,微微地颤动着。陶羊子睡不着,便觉得有点热,掀开了被子。她没再穿衣服,他却穿上了一条短裤,陶羊子久久地看着她的身体,想完全看进内心中去。相对陶羊子来说,任秋的身子白白净净的,一对黑白的躯体相依在一起。陶羊子想着,我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是伴我一生的女人。
快天亮的时候,陶羊子在朦胧中醒来。任秋还睡着,仰面闭着眼,被子半蹬开了,露出一条手臂与一只乳房,陶羊子小心地伸手去抚她。她立刻睁开了眼,移手推他。陶羊子的男人欲望膨胀起来,感觉完全清醒,奋力地把那欲望插进任秋身体里去。昨夜他已从外形上悄悄研究过她的身子,想定了行动的路子。
任秋在他进入的时候,睁着眼没有表情地看着他,承受似地由着他。也许她内心是阻拦的,陶羊子感觉到无法前行。他坚持用着强劲,她突然在他身下叫起来,声音短而急促,似乎害怕惊动了人。
她的声音低低地:“拔出来,你拔出来吧。”
陶羊子在奋力冲刺,哪里顾得上应答。似乎她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着,伴着她身体的抗拒,他欲退出的同时,他的欲望却迅速喷射出来。他弄不清算不算完成了男女之事。虽然有着喷射的快感,他心理上却是失败的。在他原来的想象中,男女相交的快感是无可伦比的。他不知道哪儿不对。
这种感觉的影响似乎影响着白天里的小夫妻俩。新婚期间,两人都在家里,陶羊子总是去看她,任秋却不再正眼看他,似乎他是一个完败的棋手。他感觉着她的身体,多少还有着迷惑。她只是完成对他必须的应付。
陶羊子想到这男女间,也如进攻的黑棋与防守的白棋。
任秋为父亲做素餐,买了好多新鲜的野菜来。吃过午饭后,任守一提出要去栖寺,住到那里。
任秋恋恋不舍地拉着父亲,这才朝陶羊子看过来。陶羊子不知该怎么劝任守一。自婚礼开始,任守一一直没有说什么话。
陶羊子对任守一说:“爹爹是不习惯俗世的生活了吗?”
任守一说:“人生八苦,只是深感心苦。家里已安,磨合有日。社会之上,歌舞升平。然总有一劫。凡尘不可久待。”任守一说栖寺不远,他总会回来看看的。拍拍陶羊子,自顾自走了。
任守一走了,任秋坐下来。陶羊子想搭话,任秋就说:“你为什么不拦住爹爹,你是不是嫌他在……”
陶羊子说:“我是那样的人吗?他是和尚,把庙当家呀。”
任秋说:“这里就不是他的家吗?他就不能多住吗?还是你,你不留他,你为了你爽快……”
陶羊子实在不知怎么应答妻子,她严词厉声,尽情地撒着气。陶羊子此时觉得女人像棋盘上一着定式不熟的棋,充满着变数,根本不是常态的棋型,走来走去,都走不好。他们不是融合着的一盘棋,明显分着了的黑白。
以后的几天,他总是涎着脸费好大神,才得允解她的衣裤。她唯一的需求,只是想他抱着她。而一旦他想解决欲望,她身体便僵硬了似的。有时他的感觉膨胀起来,她像安慰他似地说:“你又想了吧。好吧,来吧。”他在她的勉强同意下,急乎乎地想突破阻碍地进入,却感觉她的那里有着层层阻碍。慢慢地,这成了一种常态。陶羊子怀疑古书上共效同飞的描写是假的,也疑惑是不是他们哪里不对,同时疑惑她是不是会感到快乐。要不她永远只是献身。对女人来说,献身这个词看来是有道理的。
陶羊子有些天没有去围棋研究会。方天勤也在新婚头上,自然也顾不上去那里。
这一天,陶羊子来到钟园。一到便成了别人的笑料,棋手们说着新婚男女的笑话。陶羊子不由琢磨那笑话里面,真的有点经验之谈。
有人过来拉陶羊子下一盘棋,说看看他的精力是不是都用到房里了。
陶羊子几天没摸棋,自然有兴,似乎好久没有感受到下棋的快乐了。这一盘棋下得尽兴,待下完,时间已到正午。陶羊子这才发现围看的一圈人已散开了,正三三两两地聚着,在议论报上刊登的有关七?七事变的消息。
陶羊子赶着回家来。任秋不在楼下,看灶上锅碗都没动静。陶羊子叫了两声,任秋从楼上下来。
陶羊子说:“日本人在卢沟桥开战了。”
任秋说:“那又怎么呢?他打他的仗。”
陶羊子说:“我去钟园下了一盘棋。”
任秋说:“我知道。你当然去下棋了。”
陶羊子没话说了。
有时陶羊子看着任秋,觉得这就是个家了,这就是他的女人。她穿着衣服的时候,比她脱了衣服在他身边更有妻子感。白天与她同吃同做,一家两口,夫妻双双。夜晚贴近了,反倒只有一塌糊涂的欲望,和难以融合的分割。然而现在这种距离感在白天也出现了,大热天里,她却冷冷的。陶羊子觉得去下了一盘棋,便有着了罪恶感。因为下了这一盘棋,听说中日开战了,因为下了这一盘棋,似乎任秋也向他开战了。
陶羊子去做饭。他不怎么会烧菜,过去的单身生活都是胡乱对付的。他把饭菜端上桌,陪着小心叫任秋过来一同坐下了。陶羊子心里却还想着卢沟桥事变,中日终于开战了。一个国家强了,总要表现出它的力量来,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一仗,到底会打成怎么样呢?
任秋以为他还想着棋,更是气忿,吃了两口,觉得不好吃,丢下碗,自去做了一碗面条,吃完上楼了。
陶羊子跟着上楼。任秋却把房门关上了。陶羊子下楼来,正见有人找他,传口信让他去围棋研究会。
穿着副官服的方天勤谈了有关与日本人打仗的事。听说芮总早已去了前线战场。
到晚陶羊子才回来。任秋见他出去了,以为他生气发火,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的,下楼来做了晚饭。待陶羊子回来,与她搭讪,她又只是不理,陶羊子向她解释,她也不听。到晚两人还是一张床上躺下了。任秋背身朝着他,陶羊子头一次没有去抱任秋,欲望一下子冷了。在这种状况下,陶羊子不知该怎么做,他没有经验,也不想任秋对他更加反感。两个人虽然躺在一起,却有着了身体的距离。陶羊子又想到中日开战的事,这个世界似乎一下子变了。人生的一切总在变化中,让人捉摸不透。陶羊子久久没有睡着,迷迷糊糊地看着南窗外,月光下的槐树枝叶影影绰绰地摇曳着。
陶羊子满心以为结婚是人生大快之事。现在觉得结婚不是这么回事,家庭也不是这么回事,一切都不是这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呢?
方天勤对围棋研究会作了新安排,让棋士们陪达官贵贾下棋,他的理由是围棋研究会本来就由这些人物的资金赞助而建立,他们出资养了棋士,棋士陪他们下下棋,还不是应该的么?
陶羊子去围棋研究会陪过两次棋,本以为是临时的活动,那些人物哪来那么多时间?谁知来的人不断。人物越大,悬的心也越大,本不是来下棋,借着场地来探信息,借着棋来麻醉自己。少不了也谈战争,一片悲观言论。
与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下棋,陶羊子感到纯粹是一种折磨,有时对方走了一步棋,就停下,和旁边的人聊起天来,又不能催他,到对方想起来再下时,都不知道刚才是下在哪儿了。陶羊子这才感到,当初与芮总下棋时所有的难处,放到这里来根本不算什么了。因为芮总毕竟还算个棋人,他下棋时是全心全意在棋上。
到第三次陪棋,陶羊子便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这根本不是在下棋,而是在一步步地凌迟棋,他也参与了对棋的凌迟。在对棋的凌迟中,他的棋感也被凌迟。过去下棋时所有的快感都成了痛苦。
这天陶羊子陪棋的是一个大胖子,总和身边的人交谈着,战争一来,油价可以抬到多高,他说得兴奋,棋子随手摆,发现陶羊子一子点下去,对他的棋有威胁,于是,什么话都不对陶羊子说,就把陶羊子下的白棋拿开来,又把刚才下的黑棋放到白棋的位置上,就这么,连着悔改了几次。陶羊子一下子立起身,朝在门口抱胸站着的方天勤走去。
“我要走了。”陶羊子说。
方天勤问:“去哪里?”
“回家。”
“就是新婚,也用不着时时陪老婆吧……你的棋还没下完呢。”
“这不是下棋。我不想这么陪下去,宁可不要这个棋士。”
方天勤看着陶羊子,这才收起了带笑般的神情,他眯着眼盯着陶羊子,随后说:“这不算下棋,你以为什么算下棋?你这个人就是太把棋当棋了,你坐那儿摆摆子,不比你原来在戏院里端盘子拿扫帚挣钱来得好?”
陶羊子觉得与方天勤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执意告辞出了门,他感觉满心轻松。
回到家来,陶羊子才想到无法向任秋交待。他做了芮总府的棋士,才有能力成家,成了家,他却不是芮总府棋士了,任秋会是什么感觉?再说,女人在家经营生活,没有钱的来路怎么办?总不至于还让她做绣品养家吧。陶羊子本想瞒任秋些日子,但面对任秋,他还是脱口说出了此事。任秋听了,似乎无动于衷,使陶羊子大感意外。
陶羊子觉得自己很没用,这么快就让妻子失望与气恼。他太把棋当棋了。他以后也只有多去钟园,靠着在那里下棋获得收入。同样是下棋,钟园下棋的人,毕竟是在下棋吧。
在这当口,棋还有什么意义?陶羊子突然觉得棋盘很小很小,装不了一个家,更无法与一个大社会比。说是棋如人生,其实棋只是棋,小得很。他一直只是在做一点小事,有着一点小嗜好。
战争的传说像无限黑色的阴影,一团一团地逼近来。人们开始购买各种物品,物价一下子翻了几倍。又传日本军队从陆地从沿海侵入中国,中国军队到处在撤退。城市的歌厅舞厅里,依然夜夜笙歌,仿佛是享受着最后的醉生梦死。
陶羊子更多的心思,还缠绕在他的新家中。战争仿佛是报纸上的事,既实在又遥远。
这天,陶羊子从钟园回家,见任秋在房里一边流泪,一边收拾着包袱。任秋看到陶羊子,便说,爹爹要走了。陶羊子一时没弄明白,听她细说,才知道任守一要去昆城。他前几年作游脚僧常在昆城的庙里落脚静修,在那里待过不短的时间。
陶羊子看着任秋的眼泪一串串下落,觉得女人就是不同,让人怜惜。任守一常年在外东奔西跑,每一次她都是这样流泪伤心的吗?
在楼下房间里的任守一,独自盘腿坐着,见了陶羊子,说:“我要回去了。你和秋子也可以考虑到昆城去。东北之覆,早有先兆。眼下便会有东南之倾。战祸是心之大乱。这段时间,我无法静下心来,满眼都是乱象。按说我已入空门,应把尘世之事搁到一边,但还是无法抑止外心之乱。只有先回那偏静地方去。其实也知道水未动帆未动,只是心动,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却还是想回去。”
陶羊子心想,这里有与任秋新婚的家,有钟园的棋友,有南城的熟人,一时要走还真是不舍。再说,南城毕竟是都城,都城都战争失守,恐怕就要亡国了吧。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么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乱的呢?
陶羊子说:“爹爹,你再多待些日子吧。任秋还不习惯新婚生活,她念着你。只有你来的时候,她才那么快活。”
任守一摇摇头说:“我是一准要走的了。她如今是你的妻子,应与你祸福相依。三世因果,人生各有命,又有什么不能舍的呢?”说完他又闭了眼,不再说什么。
陶羊子只有转身去,帮任秋在厨房忙活,给岳父做一餐素食。
南城地理环境是北面临江,三面环山,夏季与秋初常有的偏南风被绵延丘陵遮挡着,刚入秋,天气依然闷热。
任守一吃完了饭,便背着包袱出门了。他身穿那件任秋在婚礼前为他赶做的僧衣,飘然而行。
陶羊子和任秋一直送他到城北的江边码头。任守一朝陶羊子点点头,移眼看着满目泪光的任秋。童年任秋的脸显着小妇人模样,现在的任秋已作妇人打扮,却显着了女孩单纯的神情。看了一会,任守一摇了摇头就要离去。
任秋说:“阿爹,你不想对女儿说点什么吗?”
任守一将手放到任秋的头上,摩顶而道:“人生苦短,惜福惜安。”说完转身走上软晃晃的踏板。
看着轮船驶离江边码头,渐行渐远。陶羊子与任秋回头朝家走,还没出码头,就是一场暴雨,淋得两人透湿。秋雨即寒,陶羊子搂住浑身湿冷的任秋,把衣服脱下来顶在她的头上,任秋就像一只小鸟依在他的怀里。他们两个在雨里走了一段,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回到了小院,真正感觉是回到了家。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家。
陶羊子放开任秋,让她去换衣。任秋却还在他的怀里说:“爹爹他才是苦,一直独身,而今又入空门,做了和尚,也不知吃了多少庙堂拘束的苦,吃了多少四处飘泊的苦。”
陶羊子想到任守一最后对任秋的话,人生苦短的“苦”,并非作单纯的苦来解的,是指时间的长度。又何尝不能作苦来解呢?
任秋似乎一感父亲远离,二感丈夫雨中的一路呵护,怯生生的柔情顿生,一任陶羊子帮她脱衣,不由打了一个喷嚏。陶羊子把她包在了被子里,这次脱衣解带是她身心柔顺的。脱了衣服,感觉她的体表有点寒冷,陶羊子脱衣进被,用身体裹着她,慢慢地让她暖和起来。这一来一往,她的身体有了一点从来没有过的积极反应。于是他们交合了一会,这一次她的下面是温暖湿润的,再没有阻隔。两个人这才都感到了夫妻谐和之美妙。如黑白之棋,下得紧凑,妙趣横生。
起身来,任秋还粘着陶羊子,不时在他耳边说着话,说得含糊,宛如喃喃自语。她给他做好各种吃的物品,端到他的面前来,说是补身子的。陶羊子觉得好笑,原来他是费力还费神,现在没费神也不觉得力亏在哪儿啊。
后些天,陶羊子便如在温柔乡里,似乎忘了有战争,只觉着无边风月。好过的日子过得快,一晃就过了一个多月。陶羊子在家里,有时看到任秋的眼光,里面是无限的依恋,仿佛是过去对着她父亲的眼光。每天晚上,他都享受着夫妻之幸福。夫妻恩爱这四个字,他这才真正感受。
南窗外的天空已现曙色,陶羊子醒来看着任秋。任秋说:“我该起床做事了。”陶羊子跟着穿衣服。
任秋下楼去,说:“我要出去。”陶羊子也跟着她下楼。
任秋说:“我去买菜呢。”陶羊子还是跟着她出门。
任秋说:“你跟着不好看。”
陶羊子说:“我才不管别人看不看呢。”
任秋看了他一会,搂着他,抚着他的头发说:“你真正是我命中的魔星。都说是战争要来了,我要准备一点吃的东西。你还是去钟园下一盘棋。你好久都没下棋了吧。棋瘾该上来了。顺便叫胡桃来吃晚饭。这家伙也有些时间没来了,就想看他的馋相呢。我做鸡蛋饼给他吃。”小镇的鸡蛋饼远近闻名,任秋也知道并学会了做,上次胡桃来一边吃一边赞,说秋姐的鸡蛋饼世界第一。
陶羊子来到钟园。他从芮总府出来后,钟园老板就把棋室交给他管理。陶羊子根本不管事,都是胡桃举着他的名号当招牌。
钟园里这些天下棋的人不多,大家都在谈与日本人的战事,议着会不会打到南城。谁都认为南城是都城,军队总会抵抗的。
在棋盘上摆着一步步的棋时,陶羊子突然觉得,那棋子轻得很,飘得很,棋盘上十九道横竖线,也就是划着的一道一道线,而棋子只是一个个黑白的圆点,在线点上那么无意义地摆着。
陶羊子难得地感觉到与棋有了隔隙。
好些天,陶羊子都在家里陪着任秋。这一天又去钟园转一圈,听几个棋人聊战事。淞沪会战以后,南城里也开始有防空警报声,听说前日里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南城又有人被炸死了。也有人提到了芮总,听说他带部队打了败仗,有说他战死了;有说他战伤了,被马弁背出战场;也有说他打败了没脸回头,自杀了。
回来后,陶羊子对任秋说:“明天我要去一下芮总府,曾在那儿拿过酬金的,想知道芮总的确切情况。”
任秋说:“你去吧,我明天也出去一趟。”
陶羊子说:“你也出去?不会是逛街吧?注意一点。现在街上乱,日本人的战争太凶了。”
任秋说:“昨天我还在想,我们还是去昆城吧。到阿爹那里去。”这些天,任秋用一层一层的布糊了衬底,一针一针地扎着鞋底。陶羊子很少见她做乡下女人做的事。任秋说父亲是云游和尚,到处跑,太需要一双合脚的布鞋了。
陶羊子说:“要鞋,可以去街上买一双。你看你扎得手指上都起茧子了。”
抵针脚的中指虽然套着针箍,一不小心还是会被扎破的。
任秋说:“我小时就会扎鞋底,都说我的针脚密。你现在是穿皮鞋的了。”
陶羊子说:“我还是很想穿一双你做的鞋。”
任秋把做好的鞋用力扳扳直,笑说:“那也得排在后面了。”
陶羊子不说话了。任秋靠近着他说:“你总不会吃爹爹的醋吧。我知道你很会吃醋的。”听这口气,她又在提天勤那档事了。陶羊子这才发现好久没想到天勤了,也不知他最近副官当得怎么样。
任秋其实是不想离开南城的。她早说过她喜欢南城,活在南城,死就在南城边的山腰上找块地埋下,还可以看到城里。她喜欢南城的楼街,喜欢南城的店铺,喜欢南城的口音,也喜欢南城的生活。这时她却提出要去昆城,陶羊子想到是应该准备一下了。任秋也听到外面传言,说日本人来了,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会干出来的。
陶羊子说:“你要出去?还是等一天吧。要到哪里去?我陪你去。我不放心呢。”
任秋说:“不用你陪了。我已和胡桃说好,他带我去看一位老中医呢。”
陶羊子忙问:“去看医生?你病了?你哪里病了?”想到胡桃大概又在胡吹什么世家老中医。
任秋虽是城里人,毕竟从小在乡下长大,从来不进西式医院见大夫,害怕那里医院的男大夫检查。她身体一直很好,偶尔伤风咳嗽,过几天就好了。
任秋说:“也许不是病呢。”任秋难得地红着脸,露着羞怯的神态。
陶羊子想了一会,这才想到她说没有病的含意。他激动地问:“真会是有了吗?是吗?”
任秋说:“我也不晓得。我又没经过。有点像又觉得不怎么像。不过那个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陶羊子禁不住一阵激动。只是他也有所疑惑:他就会有孩子了?他真有本事让妻子怀孩子了?这个事太大了,他确实不敢过于自信。陶羊子一直觉得男人女人在一起会生出孩子来,是很奇特的事情。他与任秋相谐的日子也不久啊。
眼下任秋似乎也不确定,她不想让他一起去,是怕两个人同时失望。陶羊子心想胡桃嘴上不牢靠,但做事有热情还算细致。如果自己跟去,三个人郑重而行,倘若不是,让人笑话不说,任秋会受不了。任秋就是脸薄,最爱面子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陶羊子也想听她而不是听医生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