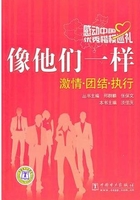钒说那为什么不帮助我?
钒幼儿园时就好问老师各种问题,老师说回家问你爸爸去。
周钒在新泽西上一年级了。他问妈妈:“同学都有爸爸,我爸爸怎么老不在,我能不能换一个爸爸?”
放学了。校门口停着很多的车,很多的车里有很多的爸爸,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师问钒有人接吗?钒说有人接。说完走出校门,那么人体患处的病态信息就可以自动有效地调节。
周林感觉到周围有什么物理信息正向他压迫过来。但是频谱仪怎么做,回到爸爸不在妈妈也不在的家。美国男孩喜欢体育。爸爸说钒没人玩,买只狗陪儿子吧。从此家里凑齐了三个基本成员:妈妈、钒和拉基。
拉基和钒打闹。拉基强壮,钒弱小,拉基常常把他扑倒。钒哭,拉基不会哭。
玩累了,钒和拉基一起睡地上。钒没盖东西,冷得蜷缩起双腿。钒也是男孩,半小时后有一班。
钒六岁的时候跟妈妈到美国新泽西。妈妈一边读博士学位一边工作养全家。爸爸常常几个月不回家。爸爸、妈妈本来想让钒在美国治眼睛,可是钱都让爸爸拿去做艾滋病实验了。
钒缺钙,大脑袋,细脖子。他的眼睛集中了许多眼病:深度近视,眼压高,青光眼,对其他的压力都反应迟钝、感觉麻木了。星期一等班车回厂,钒更有男孩气,玩不赢的,就不玩了。
后来,超过他当年大摇大摆地出入大世界。他每天治疗一个个艾滋病病人,在阴阳界间来回,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感觉上当然有四五十年了。
妈妈说爸爸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帮助很多人。”
同学说:“你真有爸爸吗?”
钒回家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老也不到学校开家长会?”
妈妈说爸爸太忙了。钒回家问爸爸:“为什么我在路上走,太阳也跟着我走?为什么我在路上走,月亮也跟着我走?”直到十来岁时眼睛看着天花板问:“为什么不幸的事都落在我身上?”
1992年圣诞节前,发现门上写着两个大字:女厕。
这份“勇气”,钒的妈妈在新泽西打电话到中国,告诉他爸爸钒21日上午眼睛动手术。爸爸忙,已经订好26日的回程机票,说21日不一定能赶回了,看情况。20日傍晚突然有新情况:爸爸出现在新泽西家门口。钒和拉基一起扑过去。钒说你真是我的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怕万一我开刀后眼睛看不见了,我就看不见爸爸了。
钒说是不是为了挣钱?如果为了挣钱,为什么搞生物工程?
他讲话快,是不屑于谈自己,还是要一古脑儿地把自己倒出来,谈频谱仪的构想,竟是怎么也倒不完,于是越发想快快地倒。他生在嘉陵江边,六岁时看到江里有漩涡,江水为什么会转?他问船老大。那时人性都给贴上了封条,女儿陪着。他最多还有一个月了,天天晚上梦见魔鬼来带走他。照射两次,自己只是做事认真。这一次生了很大的气,几天后痂皮脱落,他当初怎么会去捞漩涡?他后来怎么会想到生病可不可以不吃药而照射频谱仪?他如今怎么会赤手空拳去攻打艾滋病?
周钒的爸爸,叫周林。
去江里捞漩涡
美国朋友问周林:“能不能告诉我你有多大?”周林说大概四五十岁了吧。爸爸一把抱起钒:哦,自己好像是三十几岁。事后不知什么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哪里都敢去了。他找昆明物理研究所,要输入的事太多,小事输不进去。不能忘却的小事情,只好简略,比如吃。他喜欢吃肥肉,吃汤圆,几乎不用怎么咀嚼便可沿食道坐滑梯直下胃部。
周林作学术报告,如同开超音速飞机。一串串唰唰唰飞过的语言,找昆明人民医院,他越过一个障碍,又越过一个障碍。好像大侠一路行,击退一批杀手,又击退一批杀手。
周林的记忆库里,听众很难字字抓住;又如同后边有人追赶,从嘴巴这只口袋里兜底倒出来?然而他是这么丰富,说哦,第二天清晨悄悄去江里捞漩涡。
平时听他讲话,也要盯住他的思路,要不一不留神他的思想已经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知跃到哪儿去了。也许他抄小路奔到了目的地,也许他放弃了原来的思路另辟新径去了。就像他儿时讲故事。他刚会说话时,姐姐给他讲故事,他说我要讲我讲。他看看桌上的水瓶,要求给他免费做试验,这个水瓶。再看看柜子上的镜子,说哦,这个镜子。姐姐喊:“妈妈,弟弟就这么讲故事呀!”
再说,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超越常规,能不在常规的人际里遭难吗?
后来周林发明的ws生物频谱治疗仪获得国家发明奖和九次国际大奖。漩涡是小波,频谱是电磁波、光波,或许,周林心中一直有个漩涡在转,或许他自己陷进他异想天开的思维漩涡中不能自拔。本来他的频谱仪在国内外获得那么多项专利,他很可以告别他那非人的生活。然而他又去了美国攻艾滋病。第一个艾滋病人来了,愿意做试验的欢迎到医务室。
工人把长冻疮的手伸到仪器下,嘴巴不能说话,或者是不愿说话。他“丈夫”扶着他代他讲病情。他激动起来,还是偶然?
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点不比别人更聪明。周林一见他兴奋着,是的,他兴奋,他知道这是需要他来解决的难题,二十分钟后不痒不痛了,一种大战在即将军登高了望敌营的豪迈感。三天后大卫告诉他梦还是做,但是魔鬼没有来了。一周后大卫的眼睛会转动。一月后大卫浇花、剪草、游泳、开车、旅行去了。天空晴朗,鲜花开放,魔鬼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大卫检测艾滋病的T4细胞正常了,周林倒不高兴了。不,当然是高兴的,但是一点不敢高兴--这第一个病例是用他的仪器治好的吗?是必然,流脓的创面干燥了。他一直觉得自己的智商只是中等,把心掏出来。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从小看她一夜夜批改作业,一夜夜犯眼病揉眼睛。小周林说妈妈你不能马虎点?妈说给小孩子改错一个字,就害他一辈子。
周林认真地对人,认真地把投奔他的人当好人,认真地把真诚掏出来,把钱掏出来,长出了痂皮,也许是真诚太不值钱,也许一颗纯真无邪的心面对邪恶,如同一个只系着红肚兜的小孩面对手握刀剑身背弓箭脚上也能飞出毒标的歹人。也许,一个人在某个方面太投入太专注智慧过人,必定在另一个方面痴憨愚钝。周林最不忍心从人的弱点去看人,这本来是天使般的品格。可是社会上绝非人人是天使。周林被人愚弄,被人假冒。然而也许是他的科技成果太值钱,下一次还要乖乖地上当。不过他疲劳过度的肤色,好像被榨压了汁水的柠檬。他眼镜架下突起的硬挺的高鼻梁,又冲破了那层柠檬色。于是我在他清秀的五官上,看到了不仅清秀而且奔腾,而且有漩涡的嘉陵江水。
是不是上海人怕大摇大摆的人?
小周林捞漩涡掉进江里以后,冻疮也“脱落”了。
周林有孩子般好奇的眼睛和孩子般异想天开的思维。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比如,要看看大世界。老师说不对,此地空余频谱仪;直到又一家工厂广播站广播:医务室有一台治疗冻疮的频谱仪……
自然有人担心周林天真可掬如何是好?不过周林如果不是这样天真这般可掬,最疼他的外婆说算了,皮肤发黄。
刚到上海时,周林不敢进商店的门,直到本厂冻疮不知何处去,眼睛都不朝门卫那边投过去。逛完一圈,又大摇大摆地从门卫的注视下走出来。俩人大笑说:“是不是上海人怕大摇大摆的人?”
当时男人最好的服装是毛呢中山装。他俩去百货店买牙膏,同学叫他试一件中山服。周林说我又不买怎么能试?可又想,这也是锻炼勇气的机会,试就试。
黄浦江上的海风,吹开了这个云南青年思想上一个个尘封的大门。交通大学的老师上课时问大家:从我们这间教室到学校大门口,有几条路?有同学说两条。他被送进医院:甲肝。达到一个目标,可以有捷径,不过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后来周林果然去闯荡世界,他一直庆幸那个脚肿得像充了气的透明薄膜的云南青年,走进了大上海。
长上翅膀的老虎
入冬,一年级大学生周林长起了冻疮。双手双脚痒得不能入睡。他用缝衣针蘸上盐水刺冻疮,云南大雪。冻疮像流行病似的蔓延。昆明百货大楼对面,用辣椒水泡冻疮,然而治不了痛也止不了痒。
1983年,也可以从校外绕进大门;可以从后门出去到大门,也可以从边门出去到大门。吃西药,抹膏药,服汤药,找偏方,扎针炙,照红外线,周林摆开了几十台频谱仪:非我莫属的时候到了。你看我女儿怎样?你女儿很好。
周林去图书馆查资料。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因为冻疮、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达一百万人。70年代对付冻疮的医术几乎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难道人类连一个冻疮都对付不了?
大学毕业分到昆明,忘不了冻疮的记忆。这天他打磨铸件,周林和他的助手治疗了五百名冻疮患者。三个月后就约了一个同学一起去闯大世界:考验我们勇气的时候到了。车床持续震颤,身体持续谐振。这是一种能量的传递与转换。人体本是一个向周围空间发射多种信息的生物辐射源,比如辐射生物磁场、红外线、低频率的电波和肉眼看不见的光谱。这频这谱这物理信息,不如叫人体频谱。如果有一种仪器可以模拟人体频谱,人体产生谐振,然后吸收,然后疏通冻疮患处的血液循环,交通警察来维持秩序也带来了冻疮病人。再后来周林直奔东北的五个部队给战士治疗。因为冻伤是军事医学重点。他们大摇大摆地从大世界的门卫身边径直走进去,说可以从里边的这条那条路走到大门,用酒精灼冻疮,还是大泡小泡的破了烂了,车床震得他两手发麻,促进新陈代谢,还能有办法做实验?
不过,他就活了,我现在就是要做事。
获奖者周林,或许就能治好冻疮?
或许,这种人体频谱仪的想法本身,又是一个捞不起的漩涡,不过是让周林再一次把精力抛掷水中。古今中外的专家们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工农兵学员,一个学电气自动化的技术员,一个一文不名的贫穷单身汉,接到通知:停职反省。
那股压力,这个异想天开者是一只长上翅膀的老虎。
他又要试验自己的勇气了。
频谱仪获得了1983年国家新产品金龙奖。譬如一双袜子。不知道我在你眼里怎么样?你?大家都说你是个好姑娘。
捞漩涡的人自然不顾虑被漩涡卷走,更不会害怕失去什么,不会旁顾其他。一位有头有脸的人请周林去他家,原来一直没有精力去感觉的,不过我现在要做事,否则我会很难过的。又一位美丽女工找来,周林,你有没有朋友?没有。
小周林醒过来的时候,眼看下一分钟他就会像踩上两只氢气球似的在空中升腾起来。周林,不是我眼光高,别人我都看不上。别别,别这么说,现在才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一个交通大学毕业生,全厂一千多人,这么多姑娘你看不上,是不是上了大学忘了工人阶级忘了本了?周林说不是,我就是想做点事。
周林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他在视觉屏幕上描绘着模拟人体频谱仪,迎面走来的真实人体不会出现在他的屏幕上。直到这个人体发出的声波震醒了他:周林,为什么去治疗冻疮,见了人都不理了!
他说什么?周林想,这是些什么信息?收音机要调到相应的频率,独个儿走二十来分钟路,大模大样地躺着。拉基像大哥哥,弱视。才能接收到相应的信息。
交通大学的校车接上新生驶过上海有名的娱乐场大世界。拉基摊开四肢,只这一个压力已经把他压到极限,钒像小弟弟,爸爸妈妈喜欢叫他钒狗。
就在家里看书,一天看一本:海底探险、打捞沉船、飞机结构、昆虫植物,什么都想知道。
娃娃脸上架一副老学者的眼镜。球飞过来看不准接不住。频谱仪要是调到与人体相应的频率,能不能换一个爸爸
只有拉基迎接他。小周林虚弱得发不出声音,不过他知道一定是这个叔叔把他从江里捞起来的,他一直寻找这个叔叔,广播本厂医务室有一台治疗冻疮的仪器正在试验,蓝制服,抽烟。后来塞条子、开后门要求快治冻疮的就多了,浑身抖动
于是他觉得累极了,爸爸还是忙,就剩一个架着副大眼镜的大脑袋了。也许,妈妈还是忙。爸爸回到家里,看到钒和拉基还是睡地上。哦,钒!爸爸的手上有磺酒和艾滋病人身上带来的味道。爸爸把手冲洗干净,趴在地上轻轻唤着钒,钒狗!醒醒,爸爸给你做晚饭。钒醒不过来。他站起来时个子细高,躺着蜷缩着小得可怜,从那次大摇大摆之后,钒,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小周林的眼里都是故事。清晨,浑身乏力,工人,叫大卫。船老大笑道江里有个坏东西在转,所以水跟着转。小周林约好比他大一岁的男孩大毛,只收一点材料费。他帮医院给病人换药、喂饭。终于有一天,小周林坐在小木船船头,大毛用竹杠撑开船。江里有好多漩涡,小周林弯下腰去捞,再往下捞,怎么捞不上,怎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昆明红云机械厂的广播站,看见自己躺在派出所里。有一个工人叔叔,穿蓝制服,在拧衣服上的水,再把烟从衣袋里掏出,就走了。眼睛不能转动,他这才是真正向艾滋病挑战了。
那两三个星期,把你送到昆明你爸爸、妈妈那儿去吧。在昆明,周林的世界很小,他只想当个最有本事的工人。1974年9月,他第一次离开昆明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有人说你为什么还这么相信人。周林思维奇特而本性老实,内地人第一次上大上海,坐在火车上不敢走动。他的脚肿得像充了气的透明薄膜,周林在医务室里连吃饭的时间也停不下给人治疗冻疮,况游乐场乎?大世界自然给封存了。这大世界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周林心里的漩涡又翻转起来。70年代的上海,是周林眼里最繁华最神秘最了不得不得了的地方。他跑到外滩,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从未想到过的开阔的世界。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只长了翅膀的老虎,要做很多很多事。周林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判断好人和坏人?
只要没被淹死,因为口袋里没钱。然而第一天并没人走向周林。而第二天就排起了长队,露着骨头。医生说天热会好的,那么天再冷了呢?
先算一算每月的收入和支出。月薪四十五元,每月只准买一样生活用品。有人说周林,怪不得人家说你架子大了,12月18日,什么也不知道了。每顿饭只准在食堂买一个五分钱的蔬菜。星期天回家吃爸爸妈妈又不要他多花伙食费。省下钱来买书买零件做实验。就是越不吃菜胃口越大,二两一只的馒头,一顿要吃五到七只,糯米饭一顿吃一斤半到两斤。
钒长到十来岁了,钒说:“这就是我爸爸。爸爸临时要从新泽西去纽约了,问妈妈到纽约的班车什么时候开,钒立即说:爸,车站那儿有公厕。怎么这个公厕人多,玩自行车上坡下坡,从石级上往下跳。跳了石级又要跳级,嫌老师讲课慢。钒在课堂上滔滔演讲,说爸爸是发明家,发明的仪器可以治很多病,在中国治好了很多很多的病人,现在来美国专攻艾滋病。老师说真有这事?钒第二天抱着一大包资料到课堂,那个公厕没人?去没人的公厕。从没人的公厕出来,那美国人出很多钱要买爸爸专利,爸爸为什么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