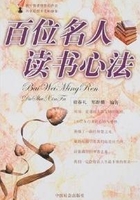大家知道,衣服,一般地说首先是要“舒适好用”;其次,在“舒适好用”的同时要求“美观耐看”。前者是衣服的实用性,后者是衣服的审美性。譬如说,夏天的衣服要求穿上凉快;冬天的衣服要求穿上暖和;军人的衣服要求富有隐蔽性,所以在色彩上避免使用惹眼的颜色而取同土地相近的黄色或同草木相近的绿色;骑马民族的衣服就要短,以便于骑射,等等。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汉族一般是穿较长的“深衣”;但北方少数民族多骑马,所以他们的衣服(“胡服”)特征是衣长至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这就说明当时汉族学习少数民族骑马,不得不改革服制,以便于实用。但是,在讲究实用的同时,还要讲究衣服的美。在世间一切生命存在形式中,惟有人是懂得审美的族类。诚然,动物似乎也有“美丽”的“衣服”(鸟的好看的羽毛,兽的好看的皮毛);但是,那只是它们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是为吸引异性,或者是出于自我保护,同人类按美的规律设计、裁剪、制作、穿着衣服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动物羽毛或皮毛的美,完全是人“加”在动物身上的,是人的意义的投入,人的价值的辐射。在动物自己的眼里,无所谓美丑。日本板仓寿郎在《服饰美学》中曾经引述了弗里克·吉尔《衣服论》中一段十分精彩的话:“其他动物虽然大多数也穿着美丽的‘衣服’,但从来不是自己装扮自己。虽然有为适应不同的气候、风土而更换‘衣服’的动物,但是为满足自己去更换衣服的,除了人以外,其他动物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里说的“自己装扮自己”,就是审美活动;为了“满足自己”、“装扮自己”而制作衣服并不断更换衣服,就充分地表现了衣服的审美性。
一般地说,衣服既要讲究实用性,又要讲究审美性;好的衣服,应该是实用和审美的完美结合。李渔既注意到衣服的实用,同时又注意到衣服的审美。譬如,在谈到“青”色衣服的优点时,说它“宜于体而适于用”。“宜于体”,指其“合体”,和谐,即美观;“适于用”,即实用。再如,在谈到“云肩”时,他说:“云肩以护衣领,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须与衣同色,近观则有,远视则无,斯为得体。”云肩的实用性在于保护衣领“不使沾油”,但同时又要注意使它“得体”,即美观。李渔关于实用与审美关系谈得最好的,是谈女人裙子的这段话:“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往来局促,有拘挛桎梏之形;折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飖,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亦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则折纹之不少可知。予谓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观,尚须十幅。盖裙幅之增,所费无几,况增其幅必减其丝。惟细瀔轻绡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则为滞物,与幅减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与他费不同。”显然,李渔既强调裙子“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的实用性,又强调其“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飖”的审美性。他要求把两者完美结合起来。要做到既实用又美观,在设计、裁剪、制作裙子时,关键是掌握好“折纹之多寡”。只要折纹适宜,则实用、审美两全;而折纹不恰当,则实用、审美两伤。李渔此论,深有见地,表明他十分了解衣服的本性,对衣服的美学规律也有确切的把握。这对我们今天的服装设计师和制作者,以及服装美学家,仍有启示意义。
这里,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李渔有关服装的流变和流行色问题的思想。
服装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本节的开头部分,我们简略谈到中国服装的发展史,读者可以看到服装随社会风尚、民族交融、经济发展、当权者的提倡、审美文化的变化等而不断变化。外国的情况大体亦如是。世界各民族的服装基本都是从“包缠型”向“缝制型”发展;就穿着方式上看,大体又是从“套头型”向“前开型”发展。但对此又不可“胶柱”,印度妇女服装至今仍保留着“包缠性”习惯;而各种“套头型”衣衫,尤其是内衣,至今仍层出不穷。从美学角度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审美风尚,很难论优劣高低;但从历史文化内涵和制作技术的精粗、简单与复杂等方面来看,还是大有不同的。古希腊的基本服装“希顿”(CHlTN)和包缠型长衣“希马纯”(HlMATlON),同现代西装相比,虽然就美的风格来说各有千秋,但就技术水平来看,却差别很大;尤其应该看到它们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氛围的产物,包蕴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审美内涵。
李渔是注意到服装随社会文化和审美风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情况的。关于这种变化,他是从服装的形制、款式和服装的颜色两个方面来把握的。我们前面曾提到李渔论述女人裙子时,点到“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和吴门最新式样的“月华裙”,对这两种式样的裙子,从审美、实用和经济角度作了评述,并且同古代的“石榴裙”作了对比。李渔从自己的道德取向、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出发,对裙子形制和款式的变化作出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在另外的地方,李渔更详细地谈到服装的流变问题。他说:
迩来衣服之好尚,有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请并言之。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讳,故易之。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可谓‘齐变至鲁,鲁变至道’,变之至善而无可复加矣。其递变至此也,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趋到尽头处耳。……反复求之,衣色之妙未有过于此者,后来即有所变,亦皆举一废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谓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则零拼碎补之服,俗名呼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缝,古人非好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长短之不同,不能像体而织,是必制为全帛,剪碎而后成之,即此一条两条之缝,亦是人身赘瘤,万万不能去之,故强存其迹。赞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无缝’,明言人间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条两条广为数十百条,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类人间世上,然则愈趋愈下,将肖何物而后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为之,盖由缝衣之奸匠,明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厌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则而效之。毁成片者为零星小块,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现出家之相?
李渔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所谈的“水田衣”,是就衣服的式样、形制而论衣服的流变,并认为这种变化自崇祯末年始。李渔给“水田衣”以否定的评价,也许自有其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似乎也并不正确,表现出相当大的片面性。其一,“水田衣”作为一种样式流行,为那么多人所接受和喜爱,自有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审美的原因和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缝衣之奸匠”的个人行为所致。我没有见过“水田衣”实际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从李渔的描述看,其特点是缝多、片杂。这种特点是不是为了剪裁得更合人体的轮廓、更符合审美的要求呢?是不是表现了当时人们某种新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呢?其二,李渔还谈到这种“水田衣”的流行“常有关于气数”,即象征明朝的统一江山被割为碎片、“土崩瓦解”,这不仅牵强附会,而且近于迷信了,完全不可取。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谈衣服色彩的流变,倒是十分精彩,不失为真知灼见之言,而且留下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李渔描述了从儿时到写作《闲情偶寄》时大约五十年间衣服流行色的变化情况。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出版《闲情偶寄》大约在六十岁左右,即康熙十年(1671)。他的所谓“儿时”,大约是万历末年(1610-1620左右),那时少女衣色“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过了几年,大约是泰昌(1620-1621)、天启(1621-1627)年间,由“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过些年,大约到崇祯年间(1628-1644),“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清朝建国(1644)之后,“石青”与“紫”已经非常少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衣服色彩流变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和文化的变化,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审美趣味自身的演变,等等。例如,中国历史上因政权的变动导致衣服色彩的变化,就不少,某一朝代的统治者往往崇尚某种颜色,并进行色彩“专政”,强行规定色彩的贵贱高低。秦代服色尚黑,囚徒穿赭色衣服。魏文帝定九品的官位,“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隋尚赤。唐尚柘黄,等而下之为红紫、蓝绿、黑褐,以白为贱;普通百姓不许用鲜明色彩。宋朝官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明朝则以皇帝的姓氏的朱为最高贵的颜色。官方对衣服色彩的硬性规定和大力提倡,必然对某个时代或时期服装色彩的流行产生影响。李渔所描述的明末清初数十年间民间女子服装色彩的流变,历史学家、服装史专家可以通过精心考证和研究,科学说明其原因和意义。此刻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李渔指出服色流变的无意识因素,即他所谓“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趋到尽头处耳”。李渔此论,深有见地。不只是服装色彩的流变,而且服装式样、形制的流变,也都有无意识因素在起作用。现代的服装美学家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日本板仓寿郎在《服饰美学》中就指出“流行是受人们的非理性感情支配的”“有时尽管是有害于健康的流行,但也制止不了,18世纪(欧洲)妇女使用的紧身胸衣,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还流行一种用莫斯林的质地软薄的绢绸做成的长袍,腰线紧靠胸部之下,表现出布料柔软的特点。“但是,当时许多人为了赶时髦,在冬季也穿这种薄薄的长袍,因此不少人患了肺炎,被叫做‘莫斯林病’。于是,1803年终于在巴黎酿成了一场流行性感冒。可见,流行是个多么违反理性的东西啊!”
最后,我们谈一谈李渔的色彩美学思想。
在有关仪容美的整个论述中,李渔特别注意色彩美,不断谈到色彩美。例如,在谈人体自身的美时,李渔详细论述“肌肤”黑白的美学问题;谈修容,谈首饰,又多次谈到色彩。而谈服装时,又集中谈到服装的色彩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谈服装色彩的流变之外,李渔还对当时人们特别崇尚因而广为流行的“青”色,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说:“然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但就妇人所宜者而论,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此其宜于岁者也;贫贱者衣之,是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极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腻之痕,非染不能复着,染之即成旧衣。此色不然,惟其极浓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觉;惟其极深也,凡浅乎此者皆纳其污而不辞,此又其宜乎体而适于用者也。贫家止此一衣,无他美服相衬,亦未尝尽现底里,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艳,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则一缕欠精,即彰其丑矣。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穷其底蕴。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此独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里衣之文越着,有复古之美名,无泥古之实害。二八佳人,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反复求之,衣色之妙未有过于此者。”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李渔是很懂得通过色彩的组合原理和心理效应来创造服装美的。
第一,通过色彩的对比来创造美的效果。例如,李渔所谓“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就是用衣色的“青”,衬托出面色的“白”和年龄的“少”。李渔所谓“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所谓“因外色最深,使里衣之文越着”,所谓“二八佳人,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等等,也是通过色彩之对比法,衬托出衣裳的美。在其他地方李渔也谈到色彩对比的问题,如谈“修容”时,说到点唇,红似“樱桃”的嘴唇被白色面孔一衬托,更显出审美效果;谈首饰时,说到以簪之浅色衬托头发之黑;谈到鞋与袜的颜色,也指出要“袜色尚白尚浅红,鞋色尚深红”,以对比而造成审美效果,等等。当然,色彩对比既可衬托出美,也能突显出丑,对后者则要加以避免,这也是李渔再三加以告诫的。
第二,通过色彩之调合或融合,来掩饰丑或削弱丑的强度。李渔所谓“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就是通过“青”与“黑”的调合或融合(年老者,面色多黑,其理相通),削弱“黑”或“老”的程度。李渔所谓“惟其极浓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觉;惟其极深也,凡浅乎此者,皆纳其污而不辞”,也是通过青色以“浓”、“深”的吸纳性,而消除或减弱丑的效果。李渔在其他地方也谈到类似的意思。
第三,通过色彩的心理学原理,创造衣服之审美效果。青色是最富大众性和平民化的颜色,正是青色给人的这种心理效应,可以转换成服装美学上青色衣服的如下审美效应:“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