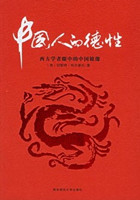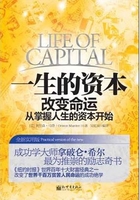女人不能生病
年前有人来电问我春节怎么过,我特豪迈地说,不过也不买菜,关起门来赶文章。
挂了电话便到部夜,我开始感冒发烧:果然不能买菜,果然不能过年,而且不能写文章:大年夜下午,梦溪走出书房说:我们家里有什么菜?我说有一棵白菜:他看着已经东倒西歪不成气候的我,说一定要为我做好吃的:东坡肉。
我立刻想起两年前的年夜,我大病一人家辛苦一年下来该过节了,我辛苦一年下来该病了,几乎逢年必病:那回梦溪说要为我做一只香酥鸭,也是他在单位聚餐时刚听人说的:印象里,大年夜他把一只鸭放进大油锅,乒乒乓乓一通炸,吓得我直怕别引起煤气爆炸:然后再蒸,然后从大蒸锅里端出滚烫的鸭再炸,然后再怎么着:他说是他听来的程序:历经苦难久经考验的香酥鸭终于出现在餐桌上时,全身乌黑,像涂了金鸡鞋油似的。只好请鸭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
不过这番香酥鸭历险记还是给家里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我不会忘记梦溪一会儿端下大蒸锅,一会儿端上大油锅的特技动作和敬业精神。
梦溪忘了那个壮烈的年夜了,他很得意地买回一块带皮带肥的肉:东坡肉是杭州名菜,一层皮一层肥一层瘦。我虽病,还是想起来都觉得好吃。不过他怎么会做呢?
傍晚他走出书房去厨房,又走出厨房喊糟了,说不知道买来的肉是冻的,要化了冻才能烧,今晚吃不上了:我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开始了,梦溪也像节目主持人那样特喜兴地宣布:东坡肉有希望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开始化冻了。
凌晨我歪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春节晚会,就箅过完了节:梦溪把烧了好几小时的肉端上阳台:他说东坡肉成功了,我说是吗?他说煮烂了就是成功了。
初一上午他把肉从一大锅汤汤水水里捞出放进另一只锅,加上酱油又煮:下午近两点,我们过年总算有一块肉吃了:我晕乎乎地夹了一点肉吃了就要喝热粥,他说你没有什么感觉吗?他期待的目光,定格般地、大特写般地挡在我面前:我才想起他为了这块肉从大年夜忙到初一:这块烧了一年的肉浪费了太多他做学问的时间:我的脑子霎时间清醒了,我清晰地说好吃:他笑道那你多吃:我说东坡肉怎么没有皮?他惭愧地一笑,说皮和肥肉全烧化了:怪不得,一块瘦肉泡在一锅油汤里:我想我总得多吃才对得起他:好吃吧?他的眼睛又大特写纖:好吃!我笑:他大得意,说你一吃上东坡肉就笑了,这人也不能这么势利呀!
初一晚上他回到书房,说他感觉中离开书房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我感觉中也觉得好像他已经牺牲了一个月做学问的时间:只求自己快退烧,好为他做饭,虽然我的水平决不在他之上,更不具有从东坡肉到香酥鸭的想象力。
初三我退烧了:中午一点他走出书房问我吃什么饭呢一一不到肚子饿了他不会想起买菜做饭的:我想只要不吃冰箱里剩的东坡肉就好:他说那么他出去买点什么吧!
这个买点什么,常常会给人带来美好的期望他买回了水果和速冻饺子,因为饿过头了,下得快吃得也快:不过,好像是生的?不生,他边说边快快地吃:我还无力去分辨是生是熟,就是一边吃一边总觉得是生的:他说你吃的时候不要去想是生是熟:也对:速食完毕,我笑问:这就是我的病号饭?他说陈小姐,你要是想提高伙食标准,还得增加预交金。
然而那生的感觉一直未能淡出,直至连着去洗手间,相信一切均付之东流。而梦溪在他的书房里并不知道部分速冻水饺的去向。
我实在希望只是我为他做饭。虽然我一直想象着科学发达后能有一种药丸,每天吃三粒便可免掉一日之三餐。
说起来,女人有一个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做饭的丈夫,是一种难得的福分。于是生活更加生动,生命更加实在,情感更加饱满,脚步更有力度。不过,女人不能生病。
香港机场告诉我
昨天就对自己说,我离港前可能要出什么事:因为这次来港顺利、快乐,该傲的事做了,想写的文章写了,要看的电影看了:晚间电视里英语对白中文字幕的电影也看了几部,很多的惊险镜头,一个人吓得冲着屏幕哇哇叫。
才松下一口气,就想到乐极生悲的古训,告诫自己不要粗心大意:人家有为的人,胆大而心细,我偏不幸,胆小而心粗,而且有一种爱护小零碎丢失大物件的特长:昨晚一边看电视一边收拾行李,相信全部收拾妥贴,再不会落下外衣在壁柜里:这是我最可能犯的错误:这次把大衣和上飞机要穿的衣服、旅游鞋放在一起,绝对忘不了。
到了机场,和两位香港好友道再见,过了海关,过了安全口,好了,这下真正的什么事也没了:只等上飞机。
找到飞往北京的07登机口,排上队,把背包放地上,还有大衣呢?我的大衣呢?北京与香港有温差,我特地随身带着准备飞到北京就披上的:可是,大衣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这件大衣是我在西单商场看到的,那天本是去文具柜台买东西,偏偏远远地看见这件大衣孤单地挂在高处,或者说这件大衣望眼欲穿地看见了我。是的,就这么一件,独一无二,像洒脱的短裙像放大的童装,是为我而生就等着我向她走去:她的身上已经落了些许尘土,大概很多人不明白这件衣服谁能穿:大人?小孩?都不对:赚谁也不能穿,当然,因为她只属于我。
可是她呢?我要找到她!在港的一切顺利、快乐都因她的离去而消失了她充塞了膨胀了我的头脑我离开登机口顺着来路寻找。
等等,还有比大衣更重要的事一一别误了登机的时间。到底还是应了昨天的预感。上天不会让事情十全十美:如何叮嘱自己,到底还是生悲了。
飞机开始滑行,机翼好像从海面划过,机翼如桨,飞机靠划水前行。想到人们常常在出行时遇到不测,我嘛,再怎么情有独钟也就是丢了件大衣。不如拉出初上小餐桌写文章,把不悦从身体里转移到稿纸上。写完了,这是这次来港的第十五篇随笔:高兴起来,当然,如果不丢失大衣……
正在北京家整理从港带回的资料,收到一封皇家香港警务处寄来的信,一惊,立即觉得好像进入了一部什么电影,髫如国际贩毒网或是什么喋血什么猛龙再穿插很多口语丫伪,5斤,香港警察说是,先生时常说英语。
信的下款写着香港机场警署指挥官的名字。信中详尽又简括地告诉我机场警署发现了一件大衣,经过调查相信是我的。请我核实一下,然后可委托什么人来办理,怎么委托人办理,还有机场警署的电话电传地址和本署档案号等。
机场警方把取回丢在香港的大衣这件我够不着的事,帮我分解成几个具体可行的细节。也就是说,我只需给香港的随便哪位友人写几行字的授权书即可。
是说,我丢失的大衣自己找回家门来了。我早认定我已失去了她,我告诉自己对于一切无可挽回的事不要懊丧,我告诉自己生活总要有一些不完美。
我告诉自己,不,是香港机场告诉我,世上有很多本来叫人伤脑筋伤心的事,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丽很动人的。
第一件事是大哭
和梦溪在香港会合后,就着手进行一项重点工程:买书:梦溪得正经八百地在九龙参加学术会议,我权充侦察兵先到附近一带寻觅新书店和特价书店:我本来喜欢没头没脑地跟着别人走,不认路也不想认路:当傻瓜是人生极乐境界:但这一次,我真想变成方向盘变成活地图变成书店感应器。
从九龙的油麻地站,走到地铁的佐敦站,又走到尖沙嘴,然后再返回到旺角站。发现一家图书中心,记下标记:旁边是大新银行;发现中南图书市场,记下一侧是荷里活商业中心;发现商务印书馆,记下对面是远通泰大酒楼。一个下午找到了大小5家书店,凯旋宾馆,告诉梦溪一像那流行歌曲《在雨中》里唱的:请跟我来--
我手持那张写面店的八卦图拐弯,棚弯……天,怎么糊涂了?梦溪说书店呢?我说糟了,找不到了:我直看八卦图,譬如这家书店,我记的是中艺国货斜对面,香水中心隔壁,可是书店的名儿呢?没写。另几家写了书店和附近商店的名称,可是没写街道,更没记方向。
也许,走反了,走拧了走岔了走迷迷瞪瞪了:迷迷瞪瞪地走在九龙的弥敦道上,越来越发虚,害怕那些书店是不是和我捉迷藏躲起来了。哇,好大一家中华书局,这可是我原先没找到的。歪打正着,梦溪很挑选了一些书。提着沉沉的书再上街,心里好像有了点底儿,再走,果然找到了图书中心。
买书买得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后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才想起怎么给亲戚朋友什么也没买?
书从香港出关到广州进关,再到广州机场办托运到京的手续。这一路,进关出关地运啊,拖啊,搬啊,觉得人生就是过了一关又一关。
终于踏踏实实地双脚着地站在首都机场大厅里等着取行李了:大厅袒开宽阔的地面,大厅投来温暖的灯光,我感觉着到家的轻松和快乐,我的脚滑来滑去,滑出欢快的音符来要是能社行李面转一圈,一定特来劲。
我们的衣箱取下了,别人的行李一件件取走了。我们那满满一旅行包书呢?传送带空了,人们走了,我们那包书呢?
没了?
从九点三刻,等到零点,没有。梦溪在办查询行李手续,剩下我一人,站在空漠的机场大厅里,被黑夜包围的机场大厅里,双腿绵软疏松,脑袋麻木痴呆。书丢了,不是钱买得回来的。有的学术书,也许目前港岛仅此一本,给梦溪捕获了:有的虽薄薄一小册,都是从密密书林中发掘出来的。一切都无可弥补这是1月初的凌晨,严寒是一把无形的扫帚,把乘客和接客的人扫得一个不剩。空漠、冰冷的大厅,吞噬着我这个一息尚存的微生物:我缩着脖,双手深深插进衣兜里。
摸黑回到我家那幢楼,自然没了电梯。我们拖着衣箱,走几级停一停,互相关照不要黑咕隆疼地栽下楼梯。第二天清晨梦溪要赶往比颐和园还远的西郊开学术会议,他说他夜里几乎一直未睡,一睡着就惊醒:那包书丢了?我说我也是梦溪又提着旅行包出去开会了:我攒下太多的东西要写,得吃点什么把身体撑起来才好:书的丢失使我变成一只瘪掉的气球,才觉得这半个月采访下来怎么这么累:去食品店买袋奶粉吧,虽然明白鲜奶的营养比奶粉好,然而煮鲜奶需要时间。
卖奶粉糕点的柜台,正有顾客要装一盒点心。售货员一块块地称分量:点心为什么不可以做成一样大小论块标价?在香港的小水果摊上,到处看到标着苹果每只几元,芒果每只几元。按大小分类就是了,买什么都快。如果有时间等着别人一块一块称点心,鲜奶也能煮上几袋了。不买了!走到附近一家小店里,没顾客,好,买袋奶粉。平时我从不在小店里买奶粉,生怕不新鲜。我对新鲜不新鲜也没知觉了。
回到家,打开包,奶粉呢?压根儿就没拿?这已是常事:交了钱不拿商品,或是拿了商品不交钱。当然,后者总是给人喝住,非常非常地不好意思。交了钱不拿商品,就箅上上大吉。我的脑子只在那包丢失的书上。我已经没有脑子了。
傍晚机场来电,才知包在广州找到(大概是那边的脱落,没了目号)并已速运至京。机场一位先生把包送到我楼下,我说太胃你了。我把包拎回家里,撞上房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哭,对着这包书大哭,就像对着一个失散后的亲人。
电视机里有人喊我
无论如何,春节总是一个节日。放假放得最长,冰箱里最是熙熙攘攘,物价要涨也好歹得过了这几天再涨:年纪嘛,皇帝与庶民一样,每人加一岁,绝对平均老少无欺。春节属于每一个人。
春节历来从零零落落的鞭炮开始。鞭炮我从小就怕。倒不是现代文明意识的超前觉醒,而是怕响声,包括也怕街头的爆米花。不过每年鞭炮声声中,重温我们祖先发明火药的自豪,重享我们古代文明的灿烂:至少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钱买越来越响的鞭炮,至少我们燃起了越来越灿烂的愿望。
春节,提醒我看到自己节日意识的低下。前不久在深圳阳光饭店与友人共贺元旦。自助餐厅像个气球种植园。屋顶上密植着气球,还有两大面用气球砌起的墙:自取水果的长桌上方飘动着丰硕的果子般的大气球:在这里吃饭,主要是吃气球吃气氛:深圳与香港的界限日见模糊,节日气氛比内地要浓:好像内地越来越过圣诞节送情人卡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海外过节偏偏比中国还中国。人们总是追求那够不着得不到的,即便好像得到了,事实上在得到的同时追求的目标已经前移了,已经又够不着得不到了。
这几年春节,我或是大病或是南下。今年决定不南下而且无大病,就想可以做事。我认真会做的事,也只有一件:写和读,终归离不开文字:春节这几天我可以做多少事?或者说我做事难道就差春节这几天?差这几天就能把事做完了?还是傲这几天事情更做不完?
不过如何想做事,也不会放弃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夜全家傻笑着看这台晚会,这是真正具象的过年了。虽然常常由傻笑变成傻瓜觉得不好看了还看,不是傻瓜吗?然而一年一度在电视机前懒洋洋傻乎乎无所用心。
好吃懒做低思维高卡路里头脑空空大腹便便,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晕乎乎飘忽忽的,忽听电视机里有人喊我,就是说有人在喊亲爱的观众们当然包括我,说舂节到了:哦,是了,零点了,我飘飘悠悠地从旧年进入了新年:然后呢?
然后晚会就要结束了。舂节就要结束了:常常有一种看完了中央台的晚会春节束了的失落:因为于我,春节还有什么呢?舂节果真到来之时,感觉里春节已经结束。或许,人之所以不安定不安分,就因为在获得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失落。
于是又会带着新的希冀,在又一个除夕到来之际,傻笑着赖在电视机前,赖在电视机前。
哦,潇洒傻一回,新春快乐!
参加公牛队
我抱着篮球向篮板跑去。我轻轻跃起,双手把球一投,中!我又抱着篮球跑去,这回几乎是贴着篮板跃得高高,高过球筐,把篮球放到球筐上。球在筐圈上转了几下,中!哇,整个儿一个芝加哥公牛队的水平!
但是,本公牛突然想起,医生不是说了,三个月后我才能打球。我一下退出了芝加哥公牛队。本公牛醒了。
醒了后不仅不能打球,而且不能快走。慢慢走到阳台上,坐下。脚下的大海扑过来,翻卷着白浪。好像宠物狗,抖动着翻滚着雪白的身子向我表示它的欢喜。可我不能和它玩,我的眼泪一下涌满了眼眶。不不,做了视网膜手术后才眼睛不好,我把抽动着的嘴唇,一下镇压了下去。好像,很长时间以来,我常常想,什么时候,哪怕有一两天,让我好好喘口气,什么也不想也不干。让白云托起我,让海水驮着我,随风飘荡。平时我就是看报,也是两只眼睛大挣着,好像打开着扫描仪,飞快地把大堆的报纸一页一页地扫过。
5月下旬去湖北前,有人来我家,进门就脱鞋。我说厅里不脱鞋的,进书房才脱。他说那你怎么光着脚满屋走?我说我太忙了,来不及又穿拖鞋又脱鞋的,把脚伸进拖鞋也得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