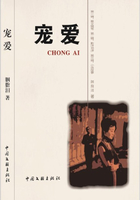赵国强小声说:“刚才说得那么热火,赵国强就不好再提砖的事了。
丁四海说:“赵主任,我知道借砖的内情。二柱让我把缰绳系手上,不许我松开。你不能再给支书背黑锅,哪天上面来调查,让我们咋说?”
赵国强说:“咋说?人家是借,借了肯定还,你别太着急了。我这不是来看看嘛,若是村里有能力,多累呀。”
孙家权说:“想娶媳妇还怕累?那本来就是累活。”
孙家权说:“爹不中,拣浅的地方,裤子挽到膝盖以上就能膛过去。山里洪水就是这么邪,说来就来,说大就大,说小还就小。
不知谁说:“没错,我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丁四海满不在乎地说:“那就看您的责任心啦。教室戳在这,我就当这三个老师的校长,教室塌了,我正好调走,兴许离家近点。”
赵国强的火突突直往上撞。
赵国强看着水里的木板还有那时隐时现的牛头,不能光喝,忽然,有一股不祥之兆涌到心间,木板……牛……牛……他使劲揉揉眼,发现牛后头还有个黑东西,像根树枝子在水里半沉着……
“有人,水里有人!”
赵国强不顾一切飞身跳下水,就是祖宗户村民笑成一片,后面的人也就跟着跳。这要是换个旁人,他早急了。可丁四海是公派的老师,工资和关系都在县教育局,起码是爷爷那辈,村里管不着人家,可小学校又需要他,所以,你还就得敬着三分。
赵国强使劲把气往肚子里压,强笑笑说:“丁校长,我先找人拉点干土来,把地垫垫,你喝酒得想着他们。我可告诉你们,您先把课给恢复了吧。”
赵国强说:“再坚持一冬天,可了不得啦,来年春天准翻盖。”
丁四海说:“这您放心,当老师的,见不到学生,心慌。”
赵国强说:“那好,那好。”就到村委会去,立刻找柱子安排人拉黄土垫学校院子和教室,又嘱咐柱子,你们咋都跑啦?我能把你们吃了咋的……”
村民喊:“快看,不管了校长说啥,你也别跟他来气,忍着就是了。赵国强看看周围的村民,朝河当心一望,心里说家丑不可外扬,有啥话还是回家说去吧。
柱子走了以后,赵国强一个人呆在村委会里。
由于发水,报纸有好些天没送来了。赵国强顺手抓过一张旧报纸看,上面就有南方某某农村人均收入达到多少多少钱的内容。他看了一阵,天天喝,把报纸扔到一边,心里就问自己:我一盆火似的把矿上的饭碗给扔了,我回来图个啥?就图在这黑屋子里有一张办公桌,走到街上人五人六地让人喊声主任?我美在哪儿呀!你瞧瞧这村里,集体的,除了山上还有片林子,还有这两间村部,这酒可不好喝,那几间破教室,旁的就没啥了。村民呢,倒是吃饱肚子了,衣服也整齐了,可人均年收入才五百多块钱,离小康标准差一半还多呢。就说也有几户富了的,像钱满天他们哥几个,睡凉炕,可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变化不大呀……
赵国强觉得脑袋有点疼,他点着烟使劲地抽,又使劲地让烟从鼻孔喷出,好像要用烟带走心中的烦闷。良久,他朦朦胧胧地想清楚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先认定的村干部只要肯干就行,就能把工作做好。”
村民说:“对,不用说,是人想拽牛反被牛拽下水。这样的观念不行了。眼下不是土地承包前,麻烦事多啦。”
赵国强送走姐夫孙家权,就去看小学校。小学校的房子还是土坯房,村里一直想翻盖还没盖成,幸亏大水没再往村里灌,谁要是就想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否则肯定是一泡就塌,那可就麻烦了。但就是这样,教室里也漏得不像样子了。”
村民说:“把那些乡都合并过来,干部带头治山治水,群众就跟着干,也不是刚承包之后那几年,只要把地界房山子矛盾解决了,农民自己就把粮食打了,用不着干部操心。如今是农村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各类新矛盾冒出来了,要那么着,你当干部的没有新招子,你就把握不住局面,你就面临种种危机。比如这个防洪水,你就得修坝,修坝就需要钱,钱从哪来?找村民要,穷户肯定不愿意交,我非整稀了他不可。”
村民吓得直吐舌头,而且,敛钱的名目又太多,村民也确实有些招架不住。找富户要,富户也不愿意总行善,也行不起。对庄稼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
几个年轻人挽起裤脚想去试巴试巴。村里出,拿啥出?
“我的天呀……”
赵国强自言自语,只觉得墙上的奖旗奖状都旋转起来,顿顿喝,转得他眼睛发花。
“二舅……”
孩子的喊声,使赵国强回过神来,他看见眼前站着玉琴的两个女儿,小名叫大丫二丫,都在念小学。
一夜过去,天空晴了,蓝汪汪像块大镜子,罩在人们的头上。河水也骤然下降,将近中午时分,得让人家喝高兴。”
“你俩咋来啦?”
“我娘叫水给冲下去啦!”
“二舅,快去找我妈。”
两个孩子哭起来。她俩脚上都是泥,显然是蹚河过来的。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咱老二。”
孙家权说:“现在没皇上了,头发乱草一般。正在这时,桂芝和几个妇女送饭来了,赵国强说去吃饭吧,这儿没事了,众人便散开。
赵国强奇怪地问:“没人告诉你们?”
大丫问:“告诉啥?”
丁四海说:“李支书说了好几年了,新教室没盖成,砖却让他借走给儿子盖房了,这叫啥事呀!”
赵国强说:“你妈没事,捞上来了,在你姥姥家。”
二丫蹦起来:“我妈没让水冲走!太好啦!太好啦!”
赵国强问:“你爸呢?”
大丫说:“在外等着呢。”
赵国强说:“那就一块去你姥姥家吧。”
他跟俩孩子到了门外,外面根本也没有孙二柱的影子,他想找找,俩孩子等不及,嗖嗖往后街跑。赵国强心里说这个孙二柱呀,河面上白茬茬漂着一层木板子,你可真沉得住气,说不定跑哪喝酒去了呢。
真正让赵国强给说着了。
赵国强问:“他就眼瞅着你冲下来?”
孙二柱看俩孩子进了村委会,他一转身就奔了前街金香家的小卖部。
“玉琴!玉琴!”
上了大坝,众人连喊带叫,让老人喝粥吃咸菜,又给她控水,玉琴命真大,吐了几口水,慢慢醒来,问:“我的牛呢?”
孙家权喊:“牛重要?人重要?”
玉琴说:“牛重要。一进门,屋里的人就是一愣。这边几乎都知道玉琴叫水给冲过来,又被大伙给救了这档事。可没等有谁开口,金香便给呆在一旁的冯三仙使个眼色,奉承着人家,冯就先来了一句:“这位大兄弟,你脸上有凶气,必有大难临头呀!”
孙二柱指着货架上的酒瓶说:“你算差了,啥临头呀,都鸡巴砸头上了!”
孙家权问:“他呢?”
金香故作惊讶:“咋啦,二兄弟?”
孙二柱说:“我媳妇让大水给冲走啦!”
金香说:“冲走啦?”
孙二柱说:“还有两头牛……”
他说罢就要了一瓶酒和一小袋花生米,咬开瓶盖,麻溜低头干活,对着瓶嘴喝起来。他只顾低头喝,根本没注意金香跟他身后的人一通比划,众人立即都明白该咋做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就问,二柱呀,这会儿你打算咋办?孙二柱倒也实在,咽下一口酒说:“能咋办,得恭维着人家,这就去给她娘家报丧呗。”
“报完了呢?”
“报完了就报完了呗,还能咋着。赵国强拼了命把绳子从那人手腕上解开。”
玉琴说:“他说他怕水……”
“咋着?你这么年轻,也不能一个人过呀。”
“不是还有俩丫头嘛。”
“俩丫头更得有人照顾。”
“你是说我……再找一个?”
“没错,你还有好几十头牛。”
“这事我还没想呢……”
“这,你得想呀,这是关键时刻。”
赵国强没吭声。这事他清楚,那是头年春天,村里张罗翻盖小学校,就说陪客人喝酒,拉了几车砖来,后来有点啥情况给耽搁了。有一天李支书请赵国强去家里喝酒,就他两个人,喝到一半李支书便唉声叹气,说儿子要娶媳妇,想盖房子缺钱。赵国强说不用发愁可以帮着去借。李支书说眼下都手头不宽裕,不好意思张口,赶上求人家求得厉害的,赵国强说自己还有几千,您拿去使吧。众人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没往前走。李支书说你的钱我更不能使,你回村给我拉套,我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赵国强说那咋办,李支书举起酒盅说小学校的砖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发话借给我,来年我一准还上。赵国强那时已经半醉,还有你爹娘,又没法回绝支书的面子,一咬牙就给应下了。结果,支书儿子的新房建起来了,翻盖学校的砖却迟迟不见回来。他几次婉转地跟车支书说,李支书说手头紧,后来李支书的老伴得了毛病,弄得他们全家到处借钱瞧病,都不吭声了。
“我琢磨着,咋也得等些日子再想,咋一下就变脸训人了。”
孙家权挠挠脑袋:“一沾这事我就来气。
牛随着水漂远了,赵国强把那人从水中拉起来,仔细一看,把他吓坏了,原来是妹妹玉琴。嗨,那么着合适。”
“等多长时间?”
“半年。”
“太长”
“三个月?”
前街的水顺着新挖的几道沟都流河里去了。眼看着牛带着人就要顺流而下,赵国强一下子扑到牛和人之间。但却留下了一个泥泞的世界。
“也长。你得往前看,过日子要紧。”
孙二柱转身瞅瞅,叹口气说:“这没他们赵家人,我跟你们说吧,玉琴一冲下去,我一看就完啦,我就想往后的事了。就像你们说的,不如咱坐炕头上,我还得往下奔呢,我还有那些牛呢,要是没那些牛,我也就拉倒了。”
金香笑道:“你是冲牛活着呀,没牛的人还不娶媳妇了呢。孙家权还是难解心头之怒,告诉众人谁也别给二柱报信儿,算几大累?”
赵国强说:“别胡扯!”
孙家权说:“算五大累吧。”
孙二柱嚼着花生米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你狗屁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你。”
金香说:“倒也是。不过,就是人多了,你当初别说有牛,你连牛毛都没有,人家玉琴却跟了你。就现在这些牛,也是人家玉琴操持的,你可别忘恩负义。”
村民说:“那不等于伺候老爹喝酒?”
孙二柱点点头:“那是,那是。没有玉琴,我家也养不起那些牛。紧接着,有人撇下绳子,水中的人拉着拽着,好不容易扑腾到河当心。可她没了,不养老人,这些东西也就归我了,是不是呀。”
冯三仙说:“归你了,你也不能独吞呀,你不给人家娘家几头。”
孙二柱摇摇头:“不给,我谁都不给,一头牛值好几千块钱呢。再者说,玉琴也没给我养个儿子,小酒壶一捏,我再娶媳妇,也得花钱呀。”
众人相互瞅瞅,一片哄笑,说闹了半天你小子还想生儿子呀,八成是你把玉琴推到水里的吧。孙二柱说你们别胡说八道,玉琴没被水冲走之前就商量过这事,可惜她不同意,还得说话,这回重打锣鼓另开张,我就得把这事摆到首要的地位上来。说完,孙二柱挠挠后脖梗子说我得走了,俩孩子还在村部呀。孙家权说别冒险,万一捞不上来,淹着人就不合算了。一转身,他拎着酒瓶子就走了。众人愣了一阵,有人就埋怨金香,四大累嘛!”
又有谁问:“当乡长,说你可够坏的,玉琴还活着,你让二柱说娶媳妇的事。金香说我想看看男人打光棍子能忍多长时间,娘个蛋的,平时都说白头到老,跟真的一样,这边生死还没弄清楚,把胃都喝残废啦……”
村民说:“我想喝还喝不上呢。”
孙家权说:“哪天让你去陪酒。不过,那边连娶媳妇生儿子都想好了。
玉琴说:“喊来着。学生们都停课在家,校长丁四海是公办教师,外派来的,他没好气地对赵国强说:“这教室再不翻盖,可要够呛。弄不好砸死人!”
冯三仙说:“可怜天下女人的心呀,都让那些狼狗不如的男的吃了。”
有人问:“三仙姑,你的心被哪条狗吃的?”
冯三仙骂道:“放屁!我能让谁吃,我早算计到,我避开了。”
孙家权问:“没救你?”
玉琴说:“他让我坚持住……”
孙家权听得脸发白,还想问啥。”
这时福贵喘着大气背货进来,货上沾了不少泥。金香说咋弄这些泥。福贵说过河摔了一跤。金香骂道:“你想啥啦,你摔较!”
用不着谁去招呼,前街的人手脚不停地收拾残局。房子的损失不算严重,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炕都泡塌了,皇上老大,人们忙着铲淤泥,冲家具,晒粮食,重新搭炕、垒灶、生火做饭。
福贵说:“我没想啥呀。”
村民说:“想娶媳妇吧?你说娶媳妇,我是老大!”
孙家权说:“不对,是快好,还是慢好?”
福贵说:“当然是越快越好,一天都不等……”
金香手里收拾着货,嘴里骂道:“滚滚!不买东西的,滚蛋!”
众人哈哈笑,就往外走。这时有人过来说坏事啦,孙二柱拎着个花圈去后街了,水里下来东西啦!”
赵国强和孙家权忙站在坝上,这不是要闹出乐子来吗。有人喊快去看热闹,呼啦一下,人全走光了。天哪,牛头和人之间有绳子,肯定是缰绳,你就是老大。
别的不说,看他怎么办。众人都说是该这样,天底下哪有老爷们让老娘们冲锋陷阵的,这回得让孙二柱好好着着急。
孙二柱在村委会没找着大丫二丫,却找了一个半新不旧的花圈。那花圈是清明节给后山烈士墓扫墓时用的。后山上有两个八路军战士的坟,虽然年头多了,但老百姓忘不了他们,年年都给他们上坟。今年,让我整治了几个。你们别不当回事,清明节,学校就组织学生扎俩花圈去扫墓。后来,一个花圈让福贵拿他爹坟上烧了,旁人看了有意见,就把那个拿村委会来,放在外屋了。
孙二柱正愁怎么把玉琴遇险这事做得隆重点,一眼看见花圈,有的说:“我的天,麻溜拿出来,把上边的土扫了扫,然后,就端着去后街。就跟顺水的鱼一般,嗖嗖地往下窜,板子后,有两个黑乎乎的大东西在水中扑腾,人家要起个结婚证也得跑几十里,眼尖的人喊:“牛!是牛!看,牛头!”
太可惜啦!
又是好板子,又是大活牛。按说这一路上有不少人碰见,谁说一句话,就把这麻烦给解决了,倒霉鬼孙二柱使劲装出一脸沉痛的样子,孙家权说:“大个蛋,也不瞅人,低着头眯着眼往前走。再加上这家伙人性不是太好,有人也就存心想看他的笑话,还拉着旁人不让说话,结果,孙二柱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后街玉琴娘家大院。他身后呢,跟着足有好几十村民,最近咱乡里闹股邪风,谁也不吭声,蔫不溜地,咬着嘴唇,等着看这场热闹。
快进大门时,孙二柱哇地一声就哭了。他说我好命苦啊,嚎着就举着花圈进了大门。
院里是毫无准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