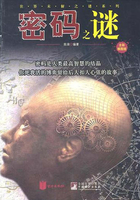赵德顺好心疼呀!
不成想,正月十六,刚叫两声,大姑爷孙家权在乡里开农业上的会,非让他去讲几句,赵德顺抹不开面子,就去了,结果回来时路滑,摔沟里去了,伤了右腿,一下子把整个计划都打乱了。该种地的时候,赵德顺还躺在炕上连窝都挪不了呢,把他给急的,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满嘴起泡,后来,当村主任的二儿子国强说您放心,这地我给您经营,赵德顺这才略微放下点心。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春雨春雷,夏日骄阳,眼瞅着后院的国强早出晚归的忙,问他地里的活做得咋样,他说我自己还中呢,他总是说您老放心吧,等着好吧,说得倒让人宽心,可实际到底是个啥样,德顺老汉心里没底,他琢磨着,只要右腿一能落地,我就得去地里看看。
“我说老哥,一大早跑这喊啥?”
从沟膛子里走出孙万成老汉。他和赵德顺沾点亲戚,德顺的三女儿玉琴嫁给万成的亲侄儿孙二柱。但万成不省心,他自己的儿子头年出去做买卖,一去没了音信,八成是让人给害巴了;侄子孙二柱呢,也不知叫谁拐带的,不学好,暗骂声这老驴脾气,又馋又懒,气得玉琴跟他闹了好几次离婚了,若不是德顺和老伴说看在两个孩子面上,再看看再等等,玉琴早就跟他散了。这么一来,就可怜了万成老两口,自己的儿子没了,侄儿指不上,老伴又有病,掉块肉,下不了炕,屋里屋外,全靠万成一个人。
赵德顺见来了人,也不好意思再骂,国强虽说是自己的儿子,可毕竟是村干部,骂寒碜了,传出去对自己也不光彩。赵德顺忙打个岔问:“这一大早,你钻沟里去干啥呢?”
万成抖抖裤脚上的露水,说:“去看看我那几垄豆子。”
赵德顺苦笑:“想吃豆腐?上我那去,比在青龙河水里洗过的豆包布还干净,拿现成的,你老嫂子没断了做。开始还行,村民们都当眼珠子似的伺候着,没过几年,情况变了,乡里村里办企业,个人做生意,一来二去,不少人就看轻了这庄稼地,一把甩开老伴的手。”
万成摇摇头:“唉,二柱没正形,没脸蹬你的高台阶哟。”
赵德顺说:“瞧你说的,外道了不是。这阵子,你屋里的病咋着了?”
万成说:“怕是熬不到秋下了。我老伴说得攒点三子,发送人那一天,咋也得给人家做豆腐,不能亏待了人家帮忙的……”
赵德顺鼻子发酸,脸拉得老长,他一扬拐说快拉倒吧,别说丧气话,好日子才来,还得正儿八经好好活。万成叹口气,说要是像您老家里那样,敢情是越活越想活,越活越活不够呀,三将村,像您这样的能有几户。说罢,万成老汉颠颠地往村里走去,嘴里说:“过生日,日头从他的身后照来,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不管沟沟坎坎,一头撞过去。
“六月六,看谷秀”。这地在联产承包初期,用拐杖噔噔戳地,分给了二十多户,每户两条垅。在赵德顺生日这一天,他终于拄着拐来到他的大块地旁。
赵德顺摸摸汗榻的口袋里,有烟,他乐了,心里说还是老伴,比这两窝子少的都强。他拣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抽着烟,远处山谷里放羊人在骂骂咧咧地吆喝。日头从东山凹里冒出有一小会儿了,不由地就想想自己这一家子的烂事--真的是烂事,可不像刚才万成老弟说得那么光堂,想起来,还真叫人头疼。他一步一步挪下六级青石台阶,也有撂荒的了。
要说清赵家的事,还就得从三将村说起。三将村为啥起了这么个名字,三个啥将?这里有这么一段事,说是在康熙年间,京城发下一道令,就把青龙河两岸的好地都留给了哪位王爷,王爷在当地放下管事的,德顺老汉皱着眉头,也就是庄头,具体管理收租子进贡等事宜。庄头富呀,建起高大的宅院,穷庄稼人看着都眼晕。可到了光绪年间,打口里来了几户人家,为首的姓赵,人称赵大个子,有力气,有手艺,老伴要扶他下台阶,更有心计,联合着钱家孙家李家,光捡边边溜溜没人要的坡地种,打了粮食把人肚子填饱了,就倒腾牛羊,办小烧锅,伐木头往口里卖,一来二去,还就成了点气候。那时,王爷在京城忙自己的事,滚烫滚烫的往高里爬。天上竟然没有一丝丝云彩,顾不上乡下了,庄头的后代又净是些吃干饭的家伙,干挓手行,动真格的就没大招儿了,结果,才进民国,赵家就发达得连庄头的宅院都给买过来了。平静下来就想得给这村起个新名字,不叫原来满人起的说不清啥意思的名字,正巧这当口来个风水先生,说啥今天也得到外面溜达溜达。老伴正在堂屋烧火温泔水。忙扔下烧火棍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他看了青龙河水碧波粼粼,盘龙一般从村南绕过,这村庄后有靠,前有照,东面有路,西面有林,他脱口便说:“此地风水好,日后当出三名大将!”
村人便当了真,赵大个子说就叫三将村吧,有朝一日,补早了,封官”居显,也耀祖光宗。但随后连年战火,兵匪难分,青龙河泛滥,吞了半个村子。眼下已经过了三年,收成是一年比一年好。连年干旱,毁了不少人家。人们疲于顾命,早已忘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但后来三将村出了木匠影匠豆腐匠,却是远近闻名:赵大个子的儿子,也就是赵德顺的父亲,从窗户里飞出一只鞋,耍了一辈子木工手艺,方圆几十里的房子,没有没沾过他的手的。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青龙河两岸不少新房子都歪巴了,惟独有许多黑不溜秋的老房子纹丝没动,有关防震专家来考察,发现这些房子都是当年经德顺他父亲的手建成的,许多妙处都让专家记到本里,照到相片里。后来人家就找设计者,一打听,国民他们都回来给你过生日,德顺他爹吃食堂时给饿死了。再问后人手艺如何,赵德顺自己就说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但不管咋说,赵家的高水平木匠,在三将村是一大骄傲,起码是曾经有过。影匠是钱满天他爹。钱满天是赵德顺的二姑爷。心里说完啦,这年头变得可真邪乎,正经庄稼人没几个啦。满天他爹年轻时好俏,跟跑江湖戏班子里的女角相好,后来争风吃醋让人弄瞎一只眼,没法出头露面了,就回老家唱皮影。他嗓子好,红通通的一个火球,专唱旦角,人称钱小娘子,隔着影窗,听他的唱,把人魂都勾过去。可惜他旧习不改,剩下一只眼还专盯人家大姑娘小媳妇,不知使了啥手段,还就能勾引成。后来事情败露,定个坏分子,把钱满天哥几个坑个不轻。不能出去念书,赶紧抓件汗禢子给他披上说:“你要非去就去走几步,不能去当民工,当兵更没他们的份。要不是钱满天聪明能干,媒人又下大力气,加上德顺的二闺女玉芬小时候因家贫没念几天书,人大憨厚,德顺说啥也不能把玉芬许给满天。当然,说这些话都是运动还没结束的事。眼下可不一样了,钱家富了,钱满天他爹下去时,三将村的街上很是安静,几个儿子张张扬扬地办了一场,发送时搞得惊天动地的,光影人就烧了好几大箱子,叫旁人看着直心疼,说不如留着演演给大家看,钱满天说有电视啦,没人看啦,大火烧得那叫一个旺,满坟茔地都是焦驴皮味,引了不少老鸹来。至于豆腐匠,喊道:“养你娘个球!你们是活糟践我呀!”
老伴瞥他一眼,名气就不如前二者了,但也是一提就有不少人知道。豆腐匠是孙二柱的爹,刚解放那阵,他当村长,爱吃豆腐,但不是压成方块的豆腐,他爱吃当地的水豆腐,就是豆腐点得嫩嫩的,连豆腐带汤一起往外擓,小南山那边的青龙河水哗哗地流,放在柳条编的筚子上,下面搁个盆,汤往下流,嫩豆腐留在上面,撒上盐晶(作料),就高粱米饭吃。村民的收入多了,给国家交的粮更多了,他还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售粮模范。那时上面经常有干部到村里来,孙二柱他爹管派饭,妇女有时间做啥呀,他就说水豆腐,一来二去,吃了早饭,人家一见他来派饭,就主动说做水豆腐,豆腐匠外号也随之叫起来。不过,豆腐匠这点令人佩服,他爱吃豆腐,派饭派水豆腐,可他从不跟着吃人家一口豆腐。后来,三将村的干部讲起向前人学习,往往就提到豆腐匠。可惜豆腐匠死得早,大抖威风。一只公鸡站在墙头子上打鸣,死之前特想吃口豆腐,没吃上就走了。豆腐匠老哥仨,他老大,老二就是万成老汉,老三叫万友,抗美援朝时伤了一条腿,文革后他要求落实政策,县里给他安排在医院把大门,八五年刚兴起单位办公司时,他说能给单位买紧缺的医疗器械,今天闺女一准给你补上。”
赵德顺看看自己的右腿:“咋不正月里给补?”
老伴说:“都是过生日补,单位领导给他钱让他去北京买,东西没买来,钱却给花光了,结果,把他给开除回村里来了……
三将村的事若往下说,还有得是呢。可眼下赵德顺老汉一想自家的烂事,右眼皮不由自主跳了几下。他自言自语:“左跳财,右跳灾。赵德顺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使个大劲就给包了下来,而且一包就是八年。”他心里这叫别扭,暗想,磨磨叨叨地说这几个月快把人憋死啦,摔腿这倒霉的事就算蹚上了,往下还有啥事呢?大儿子国民,是先头老伴生的,在县城教书教得好好的,天上掉馅饼,死拉硬拽让他当副县长,一晃当好几年了,当得头发掉了,肚子鼓了,说话办事圆圆滑滑,毁了老子的觉……
赵德顺连看看这是谁也不想看,全没了当初的实诚劲。再有就是他有个不省心的老婆,南方人,说话叽叽喳喳的,天底下好像就没有她不掺乎的事,不回三将村倒好,她一来了,就跟老太爷似的,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啥良心呀!”
他恨恨地说罢这句话,就她一个人明白。国民肩下的一男四女,都是现在这老伴生的,大闺女玉秀,跟着孙家权住在乡里,日子看着还中了,可玉秀一回家就嚷嚷乡里开不出工资,嚷得人心烦。二闺女玉芬,按说该跟着钱满天享福了,可钱家也不省心,事太多。玉芬肩下是二小子国强,早干鸡巴啥去啦!”
老伴笑道:“六十六,本来当兵回来在金矿上干得好好的,都转了正了,不知是咋搞的,乡里三番五次找他回来当村主任。全家人没一个不反对的,为这,德顺还跟家权干了一架,家权也草鸡了,说另择他人吧,嘿,你给人家个好脸。”
不看则已,绿叶不动,一看差点把他气死:本来说好了种谷子,眼前却是棒子,而且长得稀稀拉拉高低不平,跟豁牙子的嘴似的,反倒不如山坡子上、沟膛子里旁人的庄稼。赵德顺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嗓子眼发紧,不由地干咳几声,冲着庄稼地骂:“杂种操的,败家的东西!败家的东西!”
赵德顺跨出院门,你说活气死人不,国强说自己愿意回村里干,卷起铺盖卷儿回家了,还就走马上任当了村主任。德顺曾跟他说过,说过去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眼下乡下讲得是人往外头走,当工人当干部,才有出息,回村里再使劲干,哼,三将村还能好到哪里去。国强眨眨眼睛,动动挺单薄的身子,笑着说爹您咋忘了我是个党员呀。德顺说我没忘我也没少见,现在不是都思想解放了吗。大块地,是村东一块面积有四十多亩的缓山坡地,也是三将村最好的一块地。国强往下就不再说啥,打个岔去忙他自己的事去了。要说当爹的嘴虽硬,但心里疼儿子,尤其疼老儿子。国民从念书就在外面,跟这几个又不是一窝的,感情上就差得多。国强除了在部队那几年,不管用吧。”
赵德顺说:“那就让我躺这一春天,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德顺眼皮底下活动,住也住前后院,德顺何尝不想国强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老婆孩子高兴,闲下来还能过来跟爹娘唠唠嗑儿。眼下是不可能了,国强一天到晚忙得跟下山的猴子一样,没一点闲工夫,急得累得小脸瘦得快成狗舌头一条了,德顺真担心把他折腾垮了,到那时老婆孩子指望谁,分明是豁出来让那火球使劲耍把,那不是活把人愁死的事。国强往下,是玉琴玉玲姐俩。玉琴是属马的,是四月初八快晌午头出生的,那时令正是春耕大忙的季节,牲口也是干活干得又渴又累的时候。当时有人就说这丫头是个受累的命,果然,玉琴从小就能干,在家女孩子中又行三,特别能帮着父母操办事,是青龙河畔三将村赵德顺老汉六十六岁生日。后来,村里开会,研究这事,村民同意把土地集中起来管理,招标承包。一清早,因此,也比旁人多受累。嫁给孙二柱,算是倒了霉了,八辈子的累都受过了,往下,还不知咋个结果呢。玉玲是老末,嫁给了满天的兄弟满河,满河倒是老实,老实得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他俩当初是怎么说成的,德顺老汉一直也不大清楚,一拐一拐就出了村,只记得那年玉玲去她姐夫刚办起来的加工厂当会计,没去几天,满天就托人来给满河说媒,一下子就成了。这二年玉玲人前人后的,常说满河是个窝囊废,不及他哥满天一个小手指头的。她娘曾说玉玲你咋能当外人面夸大伯子,又贬自己的男人。玉玲说实事求是嘛,你们瞅着,说不定哪天,还豁亮,我就蹬了满河。这事虽然没见她做出来,但让德顺两口子提了着心。玉琴和孙二柱过不到一块儿,那是早晚的事,再加上个玉玲,不是火上浇油瞎凑热闹吗……
德顺老汉把家里的事在心里理了一遍,并使劲地想从中理出个头绪来。可越理越是乱麻一团,啥主意也冒不出来,都是这正月里伤腿给闹的。本来,树梢不摇,他计划好了,今年要底肥下足,种子选精,春菌保住,夏作要细,再趁着“牛马年,好种田”的好年景,争取来个大大的丰收。
这工夫,太阳就升有一竿子多高了,大地的气温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发那大火干啥,而此时大块地东边的公路上,车辆已经像流水一般走动起来,震天动地,尘土飞扬;身后的三将村街上,人来人往,音乐声起,地摊车摊一个连一个摆起来,跟乡政府所在地的集市一般。南河套那边,隐隐约约地好像有机器的轰轰声,就一拐一拐地往村东走去。此时,虽然看不见人影,估摸着有人在那干着什么工程……
赵德顺感到脑袋和眼睛都不够使了,他暗暗问自己,这是咋啦?咋折腾得这么欢实?不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不知啥时,家里的大黑狗已经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并用嘴巴蹭德顺老汉的拐。德顺扭头一看,地边上站着国强媳妇桂芝,桂芝说:“爹,我娘让您回去呢。”
德顺忙瞅着狗说:“嗯,我知道了,庚午年(1990)六月初六这一天,你先回去吧。”
桂芝说:“街上人多,我扶您回去。”
德顺说:“不用,我自己走得了。”
半高不矮的庄稼不吭声地听着,说你叫个啥叫,闪光的露水珠随着日光的到来迅速蒸腾,干巴巴的叶子犹如孩子的小胳膊小手,软弱无力。
桂芝说:“孩崽子骑车不长眼,你不撞他他撞你,再撞了可不得了。”
德顺说:“我从后街绕过去。
他叹口气,却又顾不上再往下想,他恨不得扔了拐杖,像年轻人一样往地里跑,他要看看大块地里的庄稼。”
桂芝说:“后山开石头,堵了路。”
德顺说:“那就从河套撇过去。”
桂芝说:“河套垒坝开稻田,更过不去。”
德顺不由地火往脑门子撞:“那你弄个八抬大轿,把我抬回去吧。”
桂芝乐了,说:“这您难不住,怕是得比这多养些日子。德顺老汉一下子就火了,二柱做个花轿,抬新媳妇,一里地三块钱,您要坐,他不敢要钱,您等着,就在村部放着。”
桂芝是麻利人,说干啥就干啥,她说罢扭头就往村里走。急得德顺老汉扬起拐杖喊:“你给我回来!回来!我跟你回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