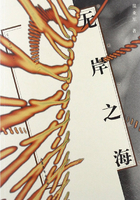这条河里的鱼现在并不多,罗红泥盯着水流有些时候,仍不见一条鱼,偶见一片红东西,是塑料袋,河的上游是城市。
“罗队,他是不是不来啦?”
罗红泥看下表,快到十点钟,打鱼人未出现,大概是不来啦。他回到岸边。
“我俩等下去?”她问。
“不,找他去!”罗红泥说。
四间房屯在河对面,七八里路的样子。刑警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走过去,要么开车过去,需绕回城边,罗红泥决定道:
“我们开车去!”
三
屯子叫四间房,房子可四间不止,三五十户人家,房子傍山造的。车子开到屯头,见一个老年人正在路口张望,他好奇地望着车顶警灯,嘴里嘟囔着什么。
“老大爷,打听一个人。”罗红泥下车走到老者面前。
“谁呀?”老人耳朵挺灵的。
“打鱼人的,姓周。”
“我儿子。”老人紧张起来,问,“他犯啥事啦,你们开逮捕车(警车)找他。”
“您老误会了,我们找他有点事儿唠唠。”丁小益说。
老人眼睛离开警灯,说:“打鱼去了,起早就走啦。”
“噢,起早走的?”刑警问。
“嗯哪,他说早点回来,屯里老王家窜瓦(换房盖瓦)等着吃鱼,这不是,都快晌午啦,我来迎迎他。”老人说出他站在屯头张望的原因。
“我们回河边吧!”丁小益说。
回河边?罗红泥考虑搭档的建议,打鱼人去了河边,在河边怎么没看见他?刑警分析某个河段还有捕鱼的地方,他可能去了那个地方,如果返回河边,容易走两岔(一致而竟错开)去,他说:
“还是等他吧。”
老人是个热心人,见警察呆在车里等,说:“大热天的……到家喝碗水!”
“谢谢老大爷!”罗红泥说。
开车带上老人回家,进了一个宽敞的大院,房子不错,瓷砖贴面,铝合金窗户,在国外应称乡间别墅了。
“我儿子从小就爱打鱼。”问起捕鱼人,老人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过去鱼多呀,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这么说吧,车道沟、马蹄窝积水都有鱼。”
丁小益偷偷望眼搭档,意思不信。车道沟有多深?马蹄窝有多大?鱼苗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的吗?
“千年的草籽,万年的鱼子……”老人说土里有草籽鱼卵,下雨就发芽就出鱼。
刑警等到中午,仍然不见打鱼人回来,周家人坐不住了,等着鱼吃的人家过来问好几次,老人埋怨儿子道:“没长心啊!人家等你的鱼下锅呢!在外边磨蹭啥,抓紧回来呀!”
罗红泥觉得该走了,他对老人说:“你儿子回来请告诉他,明天上午我们过来。”
“哎哎!”老人答应道。
刑警驾车离开四间房屯,罗红泥说:“小益,你没嗅到气味?”
“气味?什么气味?”
“危险。”
丁小益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跟搭档的差异就在这里了,罗红泥见打鱼人出现异常情况──没按时回家,敏感到了危险,约好跟警察见面,他人不见踪影。
“你怀疑打鱼人出现什么不测?”
“像。”
虽然不能证明打鱼人真的出事了,罗红泥凭职业的经验和直觉,打鱼人可能出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意外受伤,甚至是……推测的几种可能未必一种正确,因为没得到证实。
“罗队,打鱼人真的出了事,例如受害,说明什么?”丁小益抓住一切向老刑警学习的机会,她要做一名出色的侦察员。
罗红泥一边开车,一边思考。打鱼人心藏的秘密与小秃命案有关吧?也许见到凶杀场面或凶手,他出于某种原因不敢讲,搪塞说今天见面,忽然又不见了他人,家里说他起早去打鱼,在河边并没见到他。躲藏起来了吗?如果不是,他会不会遭毒手?大胆推测,凶手知道他要见刑警,怕他说出实情,杀人灭口。但后一种猜测立即被否掉,打鱼人即使见到凶杀场面,凶手也不知道他要见刑警,除非他昨天对凶手说。这种可能不存在!怎样回答丁小益?他讲了他的分析。
“周发还是躲藏起来。”她说。
“理由呢?”
“正如你猜测的,凶杀灭口什么的不存在,打鱼人不可能对凶手说警察找他,明天他对警察说什么。”丁小益说,“打鱼人闪烁其词的样子,他肯定见到了什么,犹豫一个晚上,决定不跟我们说,于是躲藏起来。”
权当躲藏起来,罗红泥说:“我们重新回到河边去。”
车过桥,出现岔路,一条通向城里,一条去河边,罗红泥开车驶向城里。
“罗队,不去河边?”
“人以食为天。”
丁小益明白先回城里吃中饭,她说:“我请你,罗队。”
“你是女生,相当然我做东喽!”
“歧视妇女!”
罗红泥说跟女同志吃饭,男同志就该结账。
“我不和你争,请我吃什么?”
开车来的路上,罗红泥看到一家路边饭馆,位置特殊,在城边上,叫河边人家。外边看很不起眼,门前停几辆高级轿车,大老远赶来吃饭,应了那句老话: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是不怕巷子远。
“河边人家。”丁小益下车望饭馆牌匾。
客满,饭馆老板倒热情,说:“来,给你们安排一张桌子。”
丁小益望搭档,意思是不是走?
“在这儿吃。”罗红泥说。
做生意的人就是不一样,河边人家的老板将自己的卧室腾出来,放上桌子招待食客。
“吃点什么二位?”老板问,别的桌子服务员管点菜,这个临时加的桌子,他自己充当起服务员。
“你们的特色菜是什么?”罗红泥问。
“鱼,当然是鱼啦!瓦罐鲫鱼是我们的当家菜,还有炒河虾。”老板介绍起菜来。
罗红泥问鱼新鲜吗?
“保证现打现做,”老板说,“我把饭馆开在河边,就是冲着河里的鱼虾来的,你看,天天满员。”
“瓦罐鲫鱼,葱炒河虾……”罗红泥点了四个菜。
“酒水?”
“两瓶美年达。”
老板复述一遍客人点的菜名、酒水,说句请稍等,便走出去。
“今天来正道(对)啦。”罗红泥兴奋道。
四
喜欢鱼的人到以经营鱼类菜肴为主的饭馆就兴奋,丁小益开始这么理解的,她说:
“对你来说,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就是鱼。”
“你把我当猫啦。”
谁都知道猫爱吃鱼,有小猫钓鱼的故事,没有小狗钓鱼。还有什么动物钟情鱼,丁小益不清楚,除了猫就是眼前这位。听到鱼双眼立马放光。
“伸筷呀小益,鲫鱼炖得不错。”罗红泥说。
“我又不是猫!”她反唇相讥道。
“小益,”罗红泥降低声音说,“饭馆的鲜鱼活虾哪里来?”
“河里,老板说清河。”
“鱼虾直接游到大马勺(炒菜用的带把大勺儿)里?得有人把它们从河里捕捞出来。”罗红泥启发式地说,“这一带谁在捕鱼啊?”
“罗队是说……”丁小益幡然道。
“我们跟饭馆老板好好聊聊。”罗红泥说。
饭时过后,饭馆冷清下来,罗红泥亮明身份后,说:“老板,问你一个事儿。”
“喝茶。”饭馆老板端杯水,等警官发问。
“谁给你们送鱼?”
“周发。”
罗红泥惊喜,正如所希望的,饭馆老板认识打鱼人周发,问:“今天几点来给你们送鱼?”
“就今天没送。”饭馆老板也奇怪说,“也不知道怎么啦,今天没给我送鱼。周发一向守时,十点前准送来。”
“你认为会是什么事?”刑警问。
饭馆老板说周发一直是他的供货商,别人的鱼他不要,三四年来,都是准时送鱼虾过来,风雨不误。对于今天没来送鱼,他解释为有什么事。后又补充一句:
“大概没捕到鱼。”
一天甚至一连几天捕不到鱼也属正常,清河的鱼虾昨夜集体休眠,呆在原地未动,自然捕不到鱼。
“除了周发,还有人在这一带捕鱼吗?”刑警问。
“据我所知没有。”饭馆老板说。
清河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少,靠打鱼为生的人转了行,只剩下周发,偶尔也有人到河里钓钓鱼。
饭馆老板提供的信息就是这些,刑警离开河边人家饭馆,车子开到小秃命案现场附近,离周发打鱼的地方更近。他俩走向捕鱼地点,河坝周围空荡荡的,没见人影。
“我们沿河找找,看周发在别处还有没有下须笼的地方。”罗红泥说。
他们沿河走去,大约走了一两千米,河面渐宽,水流很急,无法叠坝,也不适合捕鱼。
“我们回去。”罗红泥说,再走下去也没意义。
再次回到水坝前,丁小益说:“我认为,周发要藏也不一定藏在河边,山里,城里,哪儿都比荒河野渡强。”
“藏身是这样。”罗红泥说,“我们再等等,他也许能出现。”
等吧,头儿说等就等吧。丁小益觉得等也徒劳,守株待兔嘛!细想想,不守株,到哪儿去找兔子?
时间过了午后三点,丁小益焦躁起来,心里像长了青草。她的心飞到医院,惦记湾湾。
“小益,你有什么事儿吧?”
“喔,没有。”
“不对,有事儿。”
丁小益掩藏不住了,或者说给搭档揭穿,承认道:“是有点儿事。”
“你别说,让我猜猜。”罗红泥煞有介事地道,“湾湾躺在医院里,你放心不下他。”
“是,才六岁的孩子,住院……”
“军阀不是在医院照顾他吗,还有啥不放心的。”
“男人心粗。”
“我不否认,女人……”
丁小益说出她的担心:“我怕他缺岗。”
“军阀喜爱这个孩子,会悉心照料的。”
“他最近很忙,郎队调走,他主持支队工作。”刘宛泽对待湾湾,丁小益一百个放心,只是禁毒支队领导班子调整,他忙工作顾不过来湾湾。
“翁队过禁毒支队去,他们搭班子……”罗红泥说缉毒工作定规错不了,“眼下是要忙些。小益,今天我们早点儿收工,你好去医院。”
“谢谢罗队。”
“谢什么,谁还没个事儿。”罗红泥通情达理,“再等一个小时,四点我们就撤,那时周发再不来,今天就不能来啦。”
“罗队,事情就那么寸(凑巧)。”她说。
“什么?”
“我们找周发,周发就出事。”
“尚不能确定周发就出事了。”罗红泥说,一切推测只是推测,距离事实真相究竟有多远,谁也不知道,“小益明天我们还来河边,他不能总是躲避吧!”
太阳朝西行走,河水的颜色加深,鱼群过来,它们到达堤坝时,有的鱼跳跃起来,再次落水的声音很响亮。
“雾天经常有鱼飞起来,不过都是鲤鱼。”罗红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