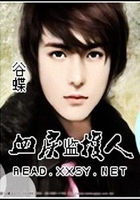古典舞练了十多分钟,白晶晶被高豆豆老师叫了出来。“白晶晶,你的腿伤好像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要休息一段时间?”一听到要休息一段时间,白晶晶流泪了,她说:“老师,我的伤能承受。我不想离开。”高豆豆看了看这个倔强的姑娘,担心地说:“白晶晶,我知道你很用功,但再这样下去,你的脚可能会出问题的。”“我不怕。”白晶晶说。“我还是要对你的身体负责的。白晶晶,我观察你一段时间了,你的柔韧度不够,如果坚持练下去,你要吃很多苦头的。”高豆豆老师劝白晶晶。“我不怕。”白晶晶还是那句话。
高豆豆不想把话说得太绝,走过来和慕容老师商量。慕容老师告诉他,白晶晶来自偏远的山区,没有一点舞蹈基础,但她肯吃苦,人也机灵。“你是说要把她留下?”高豆豆征询慕容老师的意见。“我们应该给她个机会,如果她真的不行,过几天让她退了也不迟。”慕容老师说。“可我搞不明白,以白晶晶这个条件,她怎么能入选呢?”高豆豆又问。慕容老师看了看我和欧春暖,说她也不清楚。
高豆豆又回去和其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她们也觉得白晶晶无论在舞蹈训练和形体训练上,都很难跟上课程。高豆豆走回到白晶晶跟前,轻声地对她说:“白晶晶,你还是退出吧。”白晶晶一愣神,紧咬着嘴唇,默默地走向排练厅的门口。姑娘们都望着白晶晶,她蹒跚的影子被窗外透进的阳光拉得很长。
“老师,你说话不算话,你答应给白晶晶三天时间的,现在时间还没到,你不能让她走。”李仪欣说,她跑过去拦住了白晶晶。“白晶晶,我答应过你,要教你完成舞蹈训练。你不能走。”李仪欣一把抱住了白晶晶。
高豆豆说:“我也希望白晶晶能留下来继续训练,可是……”高豆豆说不下去了。
“老师!”姑娘们一起喊着。
高豆豆还是摇头。李仪欣感到白晶晶的身子突然重了起来,两个人差点摔倒在地。原来白晶晶看到高豆豆不改变主意,她晕了过去。“白晶晶,白晶晶。”李仪欣大声地喊着。慕容老师跑了过来,按了一下白晶晶的人中,白晶晶醒了,她说:“慕容老师,我不想放弃。”慕容老师的眼眶李眼泪涌动。
“老师!”姑娘们又喊起来。
慕容老师把高豆豆拉到一边,小声地和他说了几句。我看到高豆豆的眼眶里也储满了眼泪。“我欢迎白晶晶回来,她是一位坚强的姑娘。”高豆豆说,“不过我说过的话也不会更改,如果她跟不上训练,我还是要她离开。”
“白晶晶,我们会帮你的。”姑娘们都这样说。白晶晶满是泪水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从慕容老师刚才的反应来看,我觉得白晶晶身上一定有故事,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既然慕容老师不想说,我也不好意思问她。但另一个人的故事,我迫切想知道。趁着慕容老师的课程还没开始,我决定和她聊聊。
“慕容老师,你认识东方月吗?”
“认识。她是个刺绣大师,对古典服饰很有研究。听说她在参加姑娘们的服装设计。”
“你觉得东方月老师怎么样?”
“你是不是?”慕容老师看着我,不说了。
“你别误会,我以前找东方月做过节目,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慕容老师,你是不是觉得东方月有点怪怪的?”欧春暖插了一句。
“没有啊。东方月人漂亮,脾气又好,大家都很喜欢她。”
“她有男朋友吗?”欧春暖又问。
“我不太清楚。东方月每天除了上课,就是躲在房间里刺绣,和老师们交往不多。大家都看到她一个人来来往往,没看到过她有男朋友。”
“这就奇怪了?”欧春暖说。
“什么奇怪了?”慕容老师问。欧春暖摇摇头,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慕容老师看看欧春暖,又看看我,笑了笑,去准备上课。
下午的礼仪课是巩固上午的内容,主要还是站姿。但是手的位置有了一些改变,由原来的垂直放在身体两侧,改成了左手交叠在右手上面,自然地摆在制服的最后一粒纽扣处,显得端庄大方而不呆板。慕容老师说,这是在礼仪服务时统一的站姿上做一些小小的变动,使有时候长达几个小时的站立看上去不至于太古板。
别小看这个小小的改变,姑娘们练起来也挺费劲的。连左手遮住右手的几根手指都有要求,过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手收起和放下时的曲线也很讲究,要有优美的弧度,不能太生硬。弧度过大就有夸张之嫌,弧度过小,又显得拘谨。而且手收放的速度也要注意,要不急不躁,自然大方。当然这个训练都是在头顶课本,双腿夹纸的状态下进行的。姑娘们既要保持身体的平衡,也要保证动作的完美。没多长时间下来,姑娘们的手就又酸又麻了。
慕容老师和同事们,不断地在姑娘们的队列中穿插,她们敏锐的目光挑剔地盯着姑娘们的每一个动作,哪怕有一点小小的缺陷,都要求重做二十遍。我对拍摄这些极细致的动作没感觉,就让欧春暖去。欧春暖到底是个女孩子,在姑娘们的队列里转来转去,没转多长工夫,她的T恤就贴着背了。
“江流儿,我服你了。”欧春暖在板凳上坐下把摄像机还给我,不停地擦汗,“你一整天是怎么扛住的?”
“我把摄像机想象成漂亮的姑娘呗。整天扛着,那有多幸福啊!”
“你别跟我贫嘴。哎,反正坐着没事,你和我说说东方月的故事。”欧春暖又惦记起了东方月,她打心底里认为我和东方月有不寻常的关系。
我摇摇头。东方月虽然有些古怪,但我真的和她没有一点故事。
“我不信。她照看你的眼神和动作就像妻子照顾老公似的,你不否认这一点吧?”
“这一点我也感受到了。但我也不知道原因。我刚才正向慕容老师打听,都被你打断了。可恶。”
“我比你还着急呢。”
“你着急什么?”
“我……”我一顶真,欧春暖无语了。
“她有个白玉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突然想起了东方月给我看的那个白玉锁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好像自己也有过似的,可想不起来在哪里。
“你再仔细想想,想得远一点,再远一点。”欧春暖不停地诱导我。
我十二岁以后,我家就搬到北京了。那时我就没见过白玉锁了。哪个白玉锁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的呢?我努力把时间往十二岁以前推。十二岁以前,我在乡下,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农村小学上学。那个时候有白玉锁吗?好像没有。我又继续把记忆往前推,可是推到六岁的时候,就推不下去了,那是一个空白点。但这个空白点极有可能和白玉锁有关,这段记忆的白和白玉锁的白竟莫名其妙地被我的潜意识联系在一起。
“怎么,想不下去了?”欧春暖问,“你是不是从小和东方月熟悉?或者可以说青梅竹马。”
“没有的事。我对东方月没有一点印象。我只对她的白玉锁有熟悉感,好像我也曾经有过似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白玉锁这种玉器很普通,一模一样的也很多。说不定小时候,你父母就给你戴过。”欧春暖说。
“也许这样吧。”我说。但是东方月脖子上的那把白玉锁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它白净细腻的光泽,让我过目难忘。我分不清是东方月细嫩的肌肤衬托了它的美丽,还是它让东方月显得更加典雅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