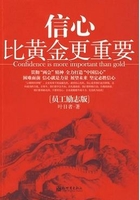进入异境的女人
在捷运火车上,我对面立着一位外籍中年女子,棕黄稀疏的头发,额角上有块葡萄色胎记。她背着硕大的旅行包,靠在车厢中部的铁杆上,嘴里衔着登机牌,手里捧了一本书。她的灵魂不在摆渡车上,也不在机场,甚至不在这个世界,而是漂游在书中。那些文字变成一颗颗尖利的刺,扎在她的心上。她的眼神由惊惧变为痛楚,最后凝固成深沉的忧伤。她的身体绽放着寒气,呼吸都像是一种叹息。到达E楼了,车身轻微一晃,她酝酿已久的泪滴,啪地落在书页上,迅速延展,留下椭圆形的印记。旅客们纷纷下车,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从她身边擦过,而她一动不动。车里的中英文广播提示到站,请全体旅客下车,她浑然不觉。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啊?我好奇地弯身去看,乳白淡雅的封面,西班牙文。无法破译。在车门快关闭时,摆渡车引导员急忙向她挥手呼唤,她微微抬起头,抱以歉意的微笑。随后,她并没有下车,而是把登机牌夹进书里,把书贴近胸口,缓缓地坐到车厢座椅上。她被艺术击中了,无法继续行程,需要缓冲。车门关闭了,载着她返回C楼。
我惊呆了。回想曾经在校园的图书馆,度过许多安静的时光。坐在窗边,为一本书、一篇文章流泪,完全忘记身在何处。那是一种相当落寞但幸福的感觉。工作以后,再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像多数人一样,迷恋图像胜过文字,喜欢喜剧胜过悲剧,在嘈杂的、变幻莫测的环境里找乐子。兴冲冲、急匆匆地赶车,把日程排满,生怕自己被落下,生怕为情所困,生怕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而这个颇为沧桑的异国女子,在旅途中走进小小的岔道,肆意享受她的感动和悲伤。那到底是什么书呢?小说么?讲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一种荒诞压抑的境遇?还是一个民族的灾难?总之,作者通过这些文字,和她的灵魂瞬间相通,疼痛在两个人的心跳之间传送。
突然,我心里涌动起深切的渴望,渴望被感动。
可爱的母女
下班时,我领到新式工作服,两套长衣长裤,四件衬衫,两条裙子,一件羊绒大衣。我抱了个满怀,踏上升降梯。除了我,电梯里还有三位乘客,一对母女,一位老先生。小女孩只有四五岁,靠在电梯门口,按下关门键。她的妈妈对她说:“快问问大家都到几层。”女孩仰起脸问老者:“爷爷到几层下?”他微笑:“二层。”女孩按亮键钮2,又歪头问我:“阿姨呢?”我说:“也是二层。”这时,女孩的妈妈要帮我拿衣服,我看她行李也不少,连忙谢绝。电梯到达二层,妈妈对女孩说:“按住开门键,等大家都出去了,你最后下。”她请老人先下电梯,又侧身示意我先走,随后她才拖着箱子背着包走出来。小女孩一直乖乖地按着电梯,用水灵的眼睛望着我们,最后才一跃而出。
吓
一个乏味的午后,我在柜台恹恹欲睡。忽然觉得不对劲,猛一睁眼,卷发当场给吓直了。一张似笑非笑的面具!旅客的眼睛从两个黑洞里与我对视,鲜红的嘴唇歪咧到一侧。
快乐等待
航站楼虽然是一个能刺激表演欲的地方,但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停留的时间还是越短越好。据说一名神秘男子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的巴拉加斯机场候机厅中居住了至少3年。平时他主要靠机场员工和乘客捐赠的三明治果腹度日,夜晚就睡在长椅上。他会说六门语言,喜欢和世界各地的旅客聊天。这的确是一个例外。
即便没有要事缠身,旅客也不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航站楼无法使人放松,尽管休息室的皮椅和家里的沙发同样柔软,机场的咖啡和市中心的咖啡散发着同样的香味。航班延误、排队值机、缓慢的登机都令人厌倦,大家不由自主地皱眉、叹气、抱怨,一点微小的摩擦都像火药碰到火星般引起爆发。
我见过与众不同的一家三口。母亲排在长龙般的队伍里,父亲带着儿子在大厅里玩耍。他把儿子举起来飞快地转圈,儿子叉开两臂,伸展双腿,飞翔欢叫。他把儿子高高抛起,又接住。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儿子躲到柱子后面和他捉迷藏。他抬起儿子的双腿,让他像小狗一样在地上爬。他把儿子放在行李推车上,到处乱窜。年轻的母亲满怀爱意地笑望着父子俩,远远地给他们拍照。值机员宣布航班进入保护状态,暂时无法办理乘机手续。队伍一片骚动,充满了不安和焦虑。只有这一家子,像在公园里度假一样,继续忘情地玩乐。
飞行恐惧症
有些旅客在办理乘机登机手续时显得十分焦虑,反复核对自己的机票和登机牌,三番五次地询问相同的问题,一遍遍地检查自己的随身物品。我接待过一个瘦瘦的中年女子,穿带领结的真丝衬衫,黑亮卷发,看起来很精干,一张口却暴露了她的慌张。我给她打登机牌,她问我厕所在哪,我给她指明方向,她笑着说其实并不想去。她问我飞机几点飞,我说十点半。她问什么飞机,我说空客330。她一直笑,但面色冷白,嘴角有点僵硬。她问在哪登机啊,我说10号登机口。她说我找不到,怎么办。我说出了门上二楼,先过安检,标识很清楚,也可以询问工作人员。她哆哆嗦嗦地接过登机牌,一个劲说对不起,又问厕所在哪儿。我正要给她指,她可怜兮兮地问我:“现在必须去登机吗?最晚可以什么时候?”我把椅子搬出柜台,说:“您不舒服么?先坐一下吧。”她轻轻抓捏着自己的头发,说:“我不想上飞机,对不起,我有点乱。”我问:“您担心什么吗?”她抽着鼻子,眼睛红红地说:“只是不想飞,没办法……登机牌给我了么?”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情景,年龄还小,头昏沉沉的,只想睡觉。穿蓝制服的空姐像小仙女,来回飘,还发好吃的。我喝了一瓶软包装橘汁,甘甜可口。第二次坐飞机,是我高中毕业去三亚旅行。办完登机牌,我开始无端地紧张,手脚发凉。上了飞机,一眼就看到前排椅背上贴的救生图标,电视屏幕里也在演示穿救生衣的方法,我全身都软了。整个飞行过程痛苦不堪,心一直悬着,怀疑自己患上了飞行恐惧症。
据统计,美国约25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飞行恐惧症。症状表现为肌肉紧张,双手冒汗,两腿发抖,心跳加剧,有想大喊“我要下飞机”的冲动。无论飞机有没有遇上气流都提心吊胆,每次飞行都是一次炼狱的过程。轻度患者以镇定剂或酒精来安定自己,严重的根本不敢搭乘飞机。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患上飞行恐惧症,老想着“Crash”这个词,眼前不断出现恐怖景象。你也许会说,飞行恐惧症无非就是害怕从天上掉下来摔死。实际上,导致恐惧的因素错综复杂。有的人不喜欢飞机,是因为患有幽闭恐惧症,受不了狭窄的空间和封闭的环境。有的人则认为,飞机带来了原本不属于人类的高度和速度,由此会产生失控的恐慌感。有的人自己天天坐飞机都不怕,但极怕家人乘机,特别是孩子。曾有旅客把孩子送上飞机后,忧心忡忡地守在航站楼,三番五次问我航班是否正常,还问我机长是谁,估计飞机不落地,她是不会离开的。还有人把飞行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像R&;B歌手美雅在《fear of flying》中唱道:“我患上了飞行恐惧症,我想这是一种与爱情极其相似的症状。”也许,飞行真的与恋爱一样充满激情,挑战极限,逼近一个无视生死的高度。而一旦到达至高点,只能保持,不能坠落,否则粉身碎骨。
中式的飞行恐惧症则更多地表现为飞行前焦虑。有些老旅客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乘飞机,那时购买机票的手续比结婚登记还繁杂,除了相当级别的介绍信和公章之外,还要托人拉关系。提起坐飞机,就感到棘手。现在方便了,只要有证件和足够的钞票,航空代理会争着把机票送上门来。然而,一些旅客觉得从购票、前往机场、换登机牌、购买保险、安全检查直到登机的全过程,依然算是“一件事”。用他们的话说,得经过若干制服男女的检查,接受若干严肃的警告,举行若干紧张的仪式。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航空公司和机场相关单位不遗余力,陆续推出电子客票、自助值机、网络值机、手机值机……登机越来越快捷了。可惜正点率没法保证。旅客害怕的是和一群人莫名其妙地等候着完全无法预测的“起飞指示”,随之而来的是糟糕的旅馆、餐食,以及混乱不堪的行程。有句话说得好,飞行恐惧症到了这种状态,已不是惧飞,而是怕飞不了。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好法子能治愈飞行恐惧症。除了心理治疗,“虚拟实境”疗法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了,类似于在飞行模拟机里熟悉环境。据说美国有个叫马克的男子天生害怕坐飞机,为了治疗飞行恐惧症,他强迫自己在美国穿越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客机上生活一个月,每天在纽约和亚特兰大之间穿梭12趟,不知道见效了没有。
我的飞行恐惧症不治自愈。第三次上飞机,什么都没想,简简单单的,没有任何忧虑了。我坐在窗边,一个劲往外看。飞机穿越波澜壮阔的云海,浪尖被阳光照得银亮。云是那样柔软洁净,一刻不停地翻滚变幻,忽明忽暗。万米高空下的河流如带,把城市和田野切成各种形状。我在飞!每个细胞都无限舒畅,喜悦在心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