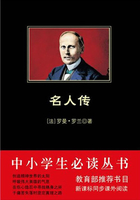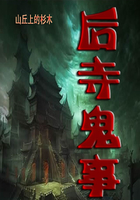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很多的机会接近当时最负盛名的这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自然乐于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的关系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然而,徐志摩与凌叔华一直含含糊糊地交往,保持着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关系,这种似雾里看花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知己关系维持半年以后,徐志摩便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征服。于是,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的“拿错信”事件发生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陆小曼的丈夫王赓同时前往看望徐志摩,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的时候,就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
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大惊失色。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便离了婚并回到北京,并很快与徐志摩结了婚。
后来,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的好友蒋复璁回忆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番话说明凌叔华只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
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尽管凌叔华自陈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但徐志摩与她情同手足,知己知心,让她对徐志摩心存一份难忘的相思。这份相思爆发在凌叔华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中的一段文字中: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柯,在这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你真的不回来了吗?”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社”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甚至想请凌叔华作林徽因的家庭教师。但在徐志摩逝后,她们却因徐志摩的一个“八宝箱”交恶,“八宝箱”事件也成了中国现代文人交往史中的一桩尽人皆知的“悬案”。
徐志摩的“八宝箱”其实曾两次寄存于凌叔华。第一次是1925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陆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L(凌叔华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久后,在武昌的凌叔华曾托人把箱子带给在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又把箱子寄放在了硖石老家。后来,徐志摩客居胡适家中,从老家拿回箱子,但感觉放在胡适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当时从武昌回到北平的凌叔华,托她保管。此时,箱子里比上次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也按徐志摩所嘱,以日记方式记录下了自己对徐的思念。不过据凌叔华证实(这说明凌叔华至少浏览了箱中的日记文稿,而是否得到徐志摩的允许,则不得而知),陆小曼的日记中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既有骂林徽因的话,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他有一个装有私人日记及和女友们往来书信的小箱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个“八宝箱”。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人自然是陆小曼和林徽因。
陆小曼想得到箱子是为了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而林徽因则不知何故,似乎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她亲自登门到凌叔华的寓所向凌叔华索要,不料遭凌叔华婉拒。只好转而求胡适帮忙。胡适以徐志摩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回信给胡适,同意把八宝箱交给他,并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但胡适从凌叔华手中得到这个箱子后,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但凌叔华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她声称,她交出了全部东西,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