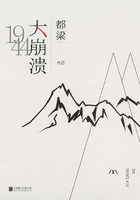“埃及姑娘,你真的承认了你所有的罪行了吗?包括巫术、淫荡,以及刺杀弗比斯·德·沙多倍尔卫队长吗?”代诉人雅克说完,庭长也接口问道。
听到这样的问话,吉卜赛姑娘的心里阵阵抽搐,只听见她在黑暗中啜泣起来,并用声音微不可闻的答道:“你们要我承认的一切我已经承认了,请赶紧处死我吧!”
“国王的代诉人,宗教法庭的检察官先生,”庭长又说道,“本庭想听听您的公诉状。”
随即,雅克·沙尔莫吕随手摊开一本厚得吓人的书,然后用控诉时的夸张声调,并配以频频的手势,开始宣读一大篇拉丁文演说词。其中所有的证词都是他从波拉特的作品中摘抄过来的,要知道,波拉特是他最欣赏的幽灵大作家,不过,非常遗憾我们不能把这精彩的片段呈现给读者了。大演讲家雅克·沙尔莫吕一开始就念得有声有色,可是引言部分还没有念完,他的额头便已经满是汗水了,就连眼珠子也开始往外冒泪珠了。忽然,他演讲到这中间一大段时,突然停住,他那平常看起来友善温和的脸孔和语调,一下子变得凶狠起来。“先生们,”他大声嚷道,不过这回讲的是法语,因为那个厚本子上没有,“在这个案子中,魔鬼撒旦是如此的嚣张,竟然胆敢肆无忌惮地在旁边做鬼脸,侮辱我们法庭和法官的尊严。看呀!”说完,他便用手指着小山羊。聪明的小山羊加里,看见公诉大人的手势,以为又是让它模仿他的模样,于是它后腿坐实,前腿舞动,还不停摇摆长了胡子的脑袋,竭尽全力地模仿起公诉人先生的模样。而它这一通表演,更加证实了公诉人话的正确性。于是,立刻有人上去把小山羊的四只脚绑了起来。
接下来,公诉人雅克·沙尔莫吕又开始了他那冗长的演讲,下面就是他演讲的最后一段内容:(读者们可以想象一下,雅克先生在宣读这份公诉状时肯定是气喘吁吁,并且绝对卖力认真。)
“各位先生,那个埃居变枯叶的妖术已经被证实,罪行也是相当明显,总之,现在一切证据和事实都已经确凿。我们现在就以最受人尊敬,且尊贵显赫的巴黎圣母院的名义,宣读各位在座大人的提议,并宣布我们的刑罚:第一,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第二,令罪犯在巴黎圣母院的门口谢罪;第三,判处这个女巫和那只小山羊死刑,将他们推至河滩广场,或者塞纳河中执行死刑。”(以上仍然是拉丁文内容。)
这一番话讲完,国王的代诉人雅克·沙尔莫吕又戴起他的帽子,然后郑重地坐了下来。
甘果瓦听到这个判决,简直伤心欲绝,不住地叹息道:“这拉丁文真他妈的垃圾!”
而就在这时,被告身边一个身着黑袍的人站了起来,他是被告的律师。但是,法官们现在太饥饿了,一看见这个人站起来,都纷纷抱怨了起来。
“尊敬的律师,希望您能抓紧时间,并简明扼要陈述。”庭长在这个时候说道。
“各位法官大人,”律师说道,“是这样的,既然我的当事人已经承认了她所犯下的罪行,那我也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我现在只是想补充几句,根据撒里克法典撒里克法典:即撒里克法兰克人法典,508年克洛维一世时颁布。其中一条规定女子无土地继承权。的一条规定:假如一个吃人的女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话,那她就要支付八千德尼埃,也就总计二百金苏的罚款。不知法庭能否批示我的当事人支付这笔罚款呢?”
“那条法律早已经被废除了。”御前特别律师反驳道。
“我否认!”被告的那名辩护律师说道。
就在这时,一个评议官提议道:“那就举帽表决吧。反正罪状已经无法更改了,更何况天色已经不早了。”紧接着,法庭就开始进行表决。各位法官均以举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赞成与否。由于他们已经急于回家填饱自己的肚子,所以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摘下了帽子并举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可怜的吉卜赛姑娘看似正在看着这一切,可事实上,她那满是哀伤的眼神已经告诉人们,她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等各位大人表决完毕,录事员也飞快地记录着,随即便把结果呈给了庭长大人。
这个时候,可怜的吉卜赛姑娘听见人群中一片慌乱,矛戈相击的声响。随后,便听见一个冷酷的声音说道:
“吉卜赛姑娘,你的行刑日期将由国王陛下亲自指定。记住,在那一天的中午,你不能穿鞋,只需身穿衬衣,脖子上套着绳索,手里拿着两个重重的大蜡烛,被送往巴黎圣母院的门口忏悔,随后你会被送往河滩广场,在那里的绞刑架上结束你的生命,连同那只被魔鬼附体的小山羊。不仅如此,你还必须向法庭缴纳三金狮币,以此来抵消你所犯下的巫术、蛊惑、行凶、淫乱等罪行,但愿上帝可以收留你的灵魂。”
“天哪!这可真是一场噩梦!”吉卜赛姑娘低着头自言自语道,随后她就被几只粗壮有力的手给带走了。
四、抛掉一切希望
中世纪称得上完整的建筑,大多数都是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的结合体,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各占一半,当然,像巴黎圣母院这种用木桩做地基的建筑除外。而这种混合形式的建筑,无论是它们的宫殿、堡垒,还是教堂,基本上都是两层结构:一座大教堂的下面,还有一座地狱般的教堂,这座处于地下的教堂不仅阴暗,潮湿,还神秘,又聋又瞎,它整日都在极其明亮和光辉的大教堂下面。有时候那个地方是一座坟墓,而有时候却又是一座牢房,要么就是两者都有。这种坚固又笨拙的建筑,除了有地基外,还有各种枝叶,比如在地下各处蔓延的房子和走廊的楼梯,可以这么说,地上和地下的建筑情况一模一样。这就好像森林山峰倒映在河流湖泊当中一样。身处其中,你根本不用考虑这是地上还是地下,因为你可以非常顺畅地在里面行走。
巴士底狱和巴黎司法宫这两座建筑,坐落在圣安东尼地区,它们也有地下建筑部分,只不过它们的地下建筑是监狱。这种监狱,越是往下,越是狭窄、阴暗,条件越恶劣。估计但丁笔下的监狱,就是以这种监狱为原型写成的。这种监狱呈漏斗状,它的最下端,也就是凹陷最突出的地方,通常关押的都是最为顶尖的罪犯。这些最为顶尖的罪犯最终的目的地,不是绞刑台就是干柴堆,甚至还有一些罪犯直接就在这里腐烂,变成一堆肥料,无人问津。如果一名罪犯被关押在这里,那也就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自由、阳光和所有希望,阻隔他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那坚硬的石头,和那些对他们呼来喝去的狱卒。这样说吧,与其说这里是个监狱,不如说这里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只有黑暗,还臭气熏天。
法庭在审判完爱斯梅拉达之后,为了防止她越狱逃跑,将她关押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穴中,它是由圣路易修建的,而这个地穴的头顶就是整个司法宫。爱斯梅拉达被关押在这里后,便绝望了,因为像她这样的“小苍蝇”根本连拱动一块小石头的力气都没有。
说实话,上帝和人世间一样不公平。因为对付像爱斯梅拉达这样的柔弱女子,根本无需这样大动干戈,更无须如此冷酷无情。爱斯梅拉达置身于这漆黑一片的牢狱中,她不仅完全被黑暗覆盖了、埋葬了,还完全被黑暗禁锢了。想想她在明媚的阳光下翩翩起舞的样子,再想想这座牢笼,天哪!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呀!可怜兮兮的爱斯梅拉达此时正蜷缩在一张破草席上,沉重的锁链残酷地压迫着她的身体。地牢里太潮湿了,墙壁上都开始往外渗水,以前渗出的水现在在她的脚下汇成了一个小水潭,而一个小水罐和一小块干瘪的面包此刻就摆在她的跟前。曾经热情开朗的吉卜赛姑娘现在却像黑暗一样冰冷,仿佛成了一个死人,根本感觉不到她身上有一丝动静。她缩成一团,就这样,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一切生机。曾经的弗比斯、天空、阳光、巴黎街道,以及为她博得阵阵喝彩的舞蹈,和弗比斯在旅馆中的悄悄话,那个持刀的教士,甚至还有酷刑、绞刑架,都一一在她的脑海中浮现,时而好似金光灿烂的欢歌幻景,时而又像奇特怪诞的噩梦。然而现在,她眼前只有黑暗,无尽的黑暗。
爱斯梅拉达自从被关进这里,她便完全失去了分辨能力:她分不清黑夜和白天,也分不清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更分不清这一切是梦境还是现实,总之,一切都是凌乱的,一切都是残缺的。她只记得,她每天都恍恍惚惚,她的思绪如同鬼魂般漂浮着,她甚至每天都在想,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之外,估计没有人再像她一样每天都深陷在空幻之中。她现在就好像一个化石一样,麻木,痴呆。头顶上那扇可以打开的门已经打开过三次,她都恍若未闻,而顺着门照射进来的几缕阳光,她也感觉不到,甚至有人从门口扔进来一块面包,她都没有看见。狱卒定时来查看,这是她与人类仅剩的最后一点联系了。
在这种地下监狱里,恐怕唯一能够机械地吸引她的听觉的,只有那从屋顶石板缝里渗出的水,每隔一定的时间水滴滴下来时,她便呆呆地听着那水滴滴在水潭中的声音。这滴答滴答的声音,是她周围唯一存在的声音,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声响中她唯一可以听见的动静。
不管怎样,在这只有黑暗和肮脏的监牢里,她总算还能感觉到那冰冷的水滴滴在胳膊和双脚上,当水滴滴在身上时,她就会浑身打着哆嗦。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在这里的,她已经不清楚了,她只记得她被一个人判了死刑,至于在什么地方判的,她也不记得了。她好像还记得当时自己昏过去了,等自己醒来时,她便被人拖到了这个鬼地方。真是鬼地方,这里寒冷彻骨,死寂无声。刚到这里时,她曾经试着在地上爬行,可该死的锁链响个不停,当时吓得她浑身打战。不过,后来她还是明白过来,这里只有冰冷的墙壁,就连身子下面的石板和草席都是潮湿的,不仅没有灯光,就连一个很小的通风口都没有。尽管到处都是潮湿的,但她还是选择坐在草席上,因为草席哪怕再潮湿,也要比石板上强。当然,偶尔为换一个姿势,她也会坐在地牢石头台阶的最后一级上。
有一段时间,她还试图去计算水滴告诉自己的时间,但最终没有坚持多久,她那脆弱的脑袋便替她宣告了这个行动的失败,于是她又恢复了那种呆傻的样子。终于有一天,或者是个晚上(因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在这座坟墓里都一样的颜色),头顶那扇门发出的声音传进了她的耳朵里,这次的声响比往常狱卒送水或面包的声音要大得多。于是,她便抬起头向上看,就在这时,门缝里射进来一缕光线,紧跟着门上那把生锈的锁便被打开,而与此同时,她也看见了一盏灯、一只手和两个人的下半截身子。因为门太矮,所以她看不见他们的头。另外,那一盏灯过于耀眼,不得已,她只能闭上双眼。
等到她再次睁开眼时,门已经被关上了。她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已经被放在石梯上的灯,还有一个人站在她面前,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被黑色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她无法看清这个人的模样,只感觉这个黑衣人像一个幽灵一样。就这样,她和那个人面对面注视着彼此,谁都没有说话,仿佛是两尊雕像。
“你是谁?怎么会来到这里?”最后,还是吉卜赛姑娘先开了口。
“我是一名教士。”这个回答让吉卜赛姑娘浑身打哆嗦。
接着,教士用一种沉重浑浊的声音说道:“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去死啊!”
“啊?很快了吧!也许就是明天,”吉卜赛姑娘说道,只见她高兴地扬起了头,不过很快又重新低了下去,“哎!时间还是太长了,为什么不在今天呢?”
“照您这么说,您很不幸了?”教士沉默了一下才说道。
“我真的很冷。”吉卜赛姑娘答道。随即她便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脚,这跟那些穷人感觉到寒冷时做出的动作一模一样,当然,罗兰塔楼的隐修女也经常会做这样的动作。同时,姑娘的牙齿也因为寒冷开始打战。
“没有光,没有火,还泡在水里,您还真是挺可怜的!”教士用那双包在黑衣服下面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地牢中的环境后,才说道。
“是的!”姑娘惊恐地说道,“我真的很不幸,全世界的人都有白天,可就我一个人没有。”
“那您知道您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吗?”教士又是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想我是知道的,”只见吉卜赛姑娘用苍白的手指按着脑袋,好像在努力回忆什么东西,“但我现在又不知道了。”她刚说完,就开始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我想出去,先生,你能帮我吗?我很冷,而且好像总有什么小东西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我非常的害怕。”
“那好。来,伸手,我带你出去。”一边说着,教士一边伸手拽姑娘的胳膊。可姑娘却被吓了一跳,她本来觉得这个地牢已经足够冰冷了,可现在伸过来的那双手比这里还冰冷十倍。
“啊,”姑娘低声说道,“这双手怎么这么冷?你到底是谁?”
她的话音刚落,教士便一把摘下了罩在脸上的风帽。可怜的吉卜赛姑娘一看,震惊得差点让自己晕过去。原来风帽下的脸就是长期以来一直纠缠着她不放的那张阴森森的面孔。她和弗比斯约会时,突然出现的就是这张面孔,而且当时这张面孔的主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害人的匕首。这个她视为魔鬼的人,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她,并且只要一有机会就迫害她。而且不止一次地把她从一个灾难推向另一个灾难,甚至还使她惨遭酷刑的折磨。一瞬间,吉卜赛姑娘马上就从呆滞状态中清醒过来,原先那些遮掩她痛苦回忆的厚厚的帷幔,一下子被眼前这个魔鬼撕碎了,她全部悲剧的经过也一幕幕再次出现在眼前——从小旅馆的夜晚到审讯室的严刑逼供,再到她被判处死刑……这一切细节都清晰无比。她本来以为这悲惨的回忆已经被她的悲伤所掩埋,可谁曾想这即将逝去的记忆又全部被这幽灵般的黑影召唤了出来。她仿佛觉得所有的伤疤又被残酷地撕开并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啊!”爱斯梅拉达双手不由自主地捂住自己的眼睛,浑身发颤,然后哆嗦着说道:“原来你就是那天晚上的教士。”说完之后,可能因为过度的悲伤,她无力地垂下自己的胳膊,同时,脑袋也耷拉下来,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死死盯着地面,全身更是不受控制地一阵阵痉挛。
再来看看教士。从他进到地牢开始,他的眼睛就没有一刻离开过可怜的吉卜赛姑娘,他好像一只盘旋在高空的老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麦田里蜷缩成一团的弱小的百灵鸟,等待着百灵鸟心理崩溃的时候,再一击而下,彻底将它打入永不翻身的地狱。
吉卜赛姑娘在一阵痉挛过后,终于又说话了,只不过她的声音仍旧无力,并且还充满了辛酸:“算了吧!算了吧!把你最后致命的一招使出来吧!”由于她过于惊恐,脑袋缩在两肩之中,那样子就和一只等待着凶残的屠夫宰割的小山羊没什么区别。
“难道我的样子很吓人吗?”教士开口说道。
姑娘没有回答。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憎恨我?”教士继续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