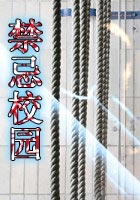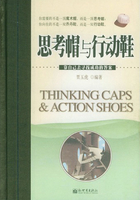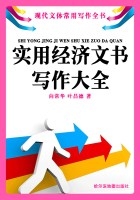这个时候,吉尔维斯也来到了小窗洞前面,三个女人就这样胆战心惊地看着小屋里的女人。三个女人的头恰好遮挡住从小窗口射进来的那几缕阳光,尽管麻袋女已经感觉不到阳光了,可她并没有注意到正看着她的三个女人。乌达德悄声说道:“千万不要打搅她,我想她肯定正在做祈祷呢!”马耶特太太看着眼前这个面容憔悴、形体瘦弱的女人,心里万分难过,泪水几乎已经充满了她的眼眶,她自言自语地说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要如此虐待自己?”她勇敢地把头伸进了那个小窗,可是那个可怜的女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从外面看不到的角落。当马耶特把头缩回来时,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打湿了面颊。
“你们平时是怎么称呼她的?”马耶特问乌达德。“我们都管她叫居第尔修女。”乌达德回答道。马耶特十分忧伤地说:“但是我想叫她巴格特·拉·尚特孚勒里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巴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示意此时已经是目瞪口呆的乌达德伸头进去瞧瞧。于是,乌达德也把头伸进小窗户,果然,她看见了一只小鞋,一只绣满了金银花线的粉红缎子的小鞋,它就放在隐修女始终盯着的那个黑漆漆的角落。随后,吉尔维斯也把头伸进小窗子观看那只小鞋。三个女人看着这个不幸的母亲,不约而同地都哭了起来。
但是,无论外面发生多大的事情,里面的那个女人依旧是一动不动,连看都不看一眼,她的眼中只有那个角落里的那只小红鞋。我敢说,只要是知道这个女人悲惨遭遇的,看到如今的一幕,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这个时候,小屋外面的三个女人谁也没有出声,她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又陷入了那无尽的痛苦回忆中,回忆那惨不忍睹的往事。她们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复活节或圣诞节的祭坛上,谁也不敢说话。她们几乎都要跪在地上了,好像在耶稣受难日走进了教堂一样。
最后,还是三个女人中好奇心最强,也是最没有耐性的吉尔维斯首先开口道:“教姐,居第尔教姐!”吉尔维斯连着叫了三遍,并且一遍比一遍的声音高,可那个隐修女依然不为所动,好像失去生命一样。乌达德也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更温柔,也更亲切:“教姐,圣居第尔教姐!”可她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沉默。“这女人可真怪,一动不动,恐怕这时就算外面有人放大炮都惊动不了她吧!”乌达德深深叹了口气,说道:“说不定她是个聋子!”随即,吉尔维斯也附和道:“说不定她还是个瞎子呢!”而马耶特太太却声音愈发低沉地说道:“也许,她已经死了!”
确实,就算此时这个女人还没有死,但她的灵魂绝对去了一个深渊,那里伸手不见五指,那里和外界完全隔绝。乌达德说道:“这样吧,我们既然来了,还是把这块饼放在这里吧。但是,如果待会来一群孩子,把这块饼拿走怎么办啊?”
话说我们的小男孩厄斯达谢,他之前一直被别的事物吸引着目光,此刻才注意到三个女人不停地透过窗口望着里面,便也凑了过来,说道:“妈妈,你们看的什么呀?能让我也看看吗?”就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屋里的隐修女苏醒了。确切地说,她是被厄斯达谢那充满童真、稚嫩却响亮的声音惊醒的,因为,就是在厄斯达谢声音响起的时候,她醒了。她马上抬起了头,而挡在脸前面的乱发也被她那干枯如柴的手臂拨到了一边,然后用一种惊讶中带着绝望的眼神看了看那孩子,可惜这种目光也是稍瞬即逝。“哦,我的上帝!就算你要惩罚我,也不要让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啊!”隐修女忽然大叫一声,不过她的声音中透露着无尽的憔悴。厄斯达谢却很有礼貌地说道:“您好啊,太太!”然而,这个时候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隐修女在听到厄斯达谢的问候后,突然变得惊慌失措,她浑身颤抖,就连牙齿也被咬的咯吱作响。在这一刻,她好像恢复了知觉,只见她双手捂着脚说了一句:“好冷啊!”
乌达德开口说话了:“可怜的教姐,你想烤烤火暖暖身子吗?”
那个女人摇了摇头。
乌达德又说:“那这样吧,我这里有点甜酒,你喝了暖暖身子吧。”
隐修女又是摇了摇头,她盯着乌达德,只说了一个字:“水!”
乌达德很显然是个善良的人,她说道:“那怎么行呢?这么冷的天,喝冷水会伤身体的。喝些甜酒吧,你看,我们还专门为你带了一块饼。”可是隐修女依然不肯接受,她推开马耶特递过来的饼子,说了一句:“黑面包”。这个时候,吉尔维斯也是怜悯地说道:“这件衣服你穿起来也许能比较暖和些,你先穿上吧。”说完,她从身上脱下了那件羊毛衫。可隐修女像拒绝甜酒和饼子那样,依然拒绝了吉尔维斯这一善良的举动,并生硬地说道:“我要麻布衣服!”
乌达德此时又好心地说道:“你知道昨天是狂欢节吧?”隐修女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当然知道,可又有什么用呢?我的罐子里已经两天没水了。”停顿了一下,她又无比哀伤地说道:“这里是一个被世人遗弃的角落,有谁还会在节日的时候想起我呢?再说了,我这里不但没有焰火,而且连水都没有。”说了这么半天,她也许感到累了,于是她再次把头垂到了膝盖上。心地单纯善良的乌达德太太以为这个女人想要取暖了,便天真地说道:“那你是想烤个火吧?”可那个隐修女用很奇怪的声音回答道:“火?那你们能帮我为我埋在地下十五年的女儿生个火吗?”
说话的时候,她的身体也是很强烈的颤抖着,说到最后连声音也发颤了,然后她朝厄斯达谢指了指,说道:“赶紧把这个孩子带着离开这里吧,埃及女人一会儿就会从这里经过的。”说完,隐修女的身体整个就倾斜在了地上,额头磕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三个女人大吃一惊,以为隐修女突然就死了,可过了一会儿,这具身子又跪立了起来,然后朝着那只小鞋艰难地爬去。之后三个女人便不敢再看了,也看不见了。她们在外面只能听见隐修女的叹息声,她好像正在狂吻那只小鞋子,另外还时不时传出梆梆的声音,这是用脑袋撞墙的声音。
乌达德这三个女人本来正在想,隐修女是否撞死了,可就在这时候,马耶特忽然一声大叫:“巴格特!巴格特!巴格特!”谁知道,屋里隐修女一听到马耶特说的话,便立刻全身颤抖着,赤裸着脚站了起来,她的眼中似乎有火光要喷射出来。突然出现的这一幕把乌达德三个人吓傻了,赶紧往后退了退。
与此同时,那个隐修女的脸已经贴在了窗户上,她狂笑着,大声喊道:“哈哈,是埃及女人在叫我呢!”而这时,她也透过窗户看见了耻辱柱那边的情形,便更加发疯般狂喊道:“又是你啊,该死的埃及女人!你把我的女儿偷走了,你还我的孩子!该死!该死!该死!”这个声音就好比一个人即将断气时的吼叫声。
四、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隐修女的那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串联在了一起。因为除了上面的人能够看到“老鼠洞”发生的一切外,下面的人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耻辱柱那边发生的事情。前一幕的观众是那三个善良的女人——乌达德、马耶特和吉尔维斯,而后一幕的观众则是聚拢在耻辱柱周围的无数观众。
自从早上九点钟那四名骑兵就站在耻辱柱的四个角后,这些围观的人便已经猜出这里马上就会上演一场惩罚犯人的演出。于是,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直到挤得水泄不通。最后,也许是围观的人太多了,挤压得实在没有办法,那四名军警只能举起自己手中的马鞭来维持秩序,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鞭子,一边大声厉喝:“走开,走开!”
很显然,这群围观的群众早已经习惯观看这种公共场合行刑的情形了,因此他们非但不着急,相反还很有耐心。反正站着也是站着,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这群观众便开始用审视的目光琢磨起耻辱柱。说实话,耻辱柱这个东西构造非常简单:一座石头做成的方形台子,是空心的,大概只有十尺高;有一条很陡的阶梯,用来通到台上;台上平行安装了一个橡木板大轮盘。行刑时,犯人跪在轮盘上,双手被反绑于木轴上;而木轴则连接下面安装的绞盘,由绞盘带动,大轮盘始终与水平面平行旋转,这样就可以让站立于广场各个角落的观众看清楚罪犯的脸。这在当时叫做“旋转示众”。
说实话,河滩广场上的这个耻辱柱比起菜市场的那个耻辱柱差远了,远没有那个耻辱柱有意思。这么说吧,菜市场的那个耻辱柱不仅具有浓厚的建筑艺术气息,而且还十分宏伟。因为它除了有铁十字架和八角灯,有雕刻在突出屋顶边上的花朵和叶片之外,同样还有神秘奇怪的水槽,甚至连雕刻精细的木架和雕塑都有。再来看看河滩广场的这个耻辱柱,一切都非常简单,除了一块高高的石头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不仅简单还很粗糙。
也许对喜欢哥特式艺术的观众们来说,这样的造型确实太过寒碜了,但对于中世纪的那群观众而言,就像现在这群人,他们的要求极低,他们并不关心刑台造得是否宏伟漂亮,也并不关心这些刑台到底给人多少娱乐,他们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只要能让他们看热闹”就够了。
犯人终于在群众的等待中被押解而来,他被拖在一辆车子的后边。随后,犯人就被一名军警推搡到耻辱柱上,并绑了起来。就在这时,所有的观众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只看了一眼,便已经认出这个奇丑无比的犯人来。他不是别人,他正是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
的确,这名犯人就是加西莫多。谁都没有想到,昨天众人才把他推选为愚人王,并在这里享受无上的荣誉。可今天在同一个地方,他却变成了众人眼里的罪犯,再次成为了人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但是,有一点肯定无疑,那就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意识地去比较昨天和今天的不同。这样的场面只缺少一个人,那便是甘果瓦和他的戏剧。
没过多久,国王陛下那宣过誓的传谕官米歇尔·卢瓦尔隔空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在场的观众安静下来。在一片寂静中,米歇尔高声宣读了根据总督大人的意思写下的裁决书,然后便带领其他穿着制服的手下回到车子后面去了,而耻辱柱上的加西莫多仍旧神态木讷,没什么反应。按照当时的惯例,罪犯在行刑前一定要被绑得结结实实,一动都不能动。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那些锁链都已经深深地陷入加西莫多的肉里了,可他依然是无动于衷。至今,这种刑罚仍在流传,脚镣手铐仍旧在我们这个文明而又高尚的社会中存在。
可怜的加西莫多,对于别人蛮横无理的推搡、拖抬,他都默不作声地选择了忍受。对于那些非常粗鲁地扒掉他衣服的人,他此时也是默默地选择了容忍。但是从他的脸孔上不难看出,他整张脸上现在已经布满了惊愕和恐惧。人们以前都知道加西莫多是个聋子,可现在又把他当做了一个瞎子。
加西莫多被几位军警拖到转盘上,军警让他跪下,他便跪下;说扒掉衣服就扒掉衣服。除了这些,军警们还用最新式的捆绑方法对待他,对于这些人对他做的一切,他都选择了听之任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不断听到加西莫多粗粗的喘息声,他现在就好像一只被绑在屠夫车上的牛,脑袋也朝下耷拉着。这个时候有人说话了,又是“磨坊”若望·孚罗洛·德·梅朗狄诺,他对站在旁边的同学罗班·普斯潘说道:“加西莫多就是个大傻瓜!他简直就是个白痴,任由别人的摆布!”加西莫多就这样光着膀子,赤裸着上身跪在转盘上,围观的群众看见他那畸形的骨骼和长满汗毛的肩膀,便爆发出阵阵的狂笑,好像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就在观众乐此不疲地欣赏和嘲笑着加西莫多时,一个人走到了加西莫多的身边。有人认出了这名男子,于是他的名字一下子便在人群中传开了,他便是小堡的宣过誓的行刑官比埃拉·多尔得许。
比埃拉·多尔得许一上去,一个黑色的沙漏便被他放在了耻辱柱的一个角落里,那是一个计时器,它的上层装满了红色的沙子,沙子通过中间的小孔不断向下层漏去。比埃拉先是脱去了他那件两种颜色的上衣,而他右臂上挂着的一条金光闪闪的皮鞭映入人们的眼帘,然后他非常娴熟地用左手卷起了右边的那条袖子,那条袖子一直被卷到腋下。
就在这时,我们最爱凑热闹,也最爱出风头的“磨坊”若望·孚罗洛·德·梅朗狄诺用双手撑着罗班·普斯潘的肩膀,把自己置于人群的最高处,然后大声地喊道:“快看啊!这个家伙马上就要粗暴地惩罚我哥哥,也就是若扎斯副主教先生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先生了。看看这个雄伟的建筑吧,脊背像圆拱顶,双腿像弯曲的柱子。”这些话引起群众的阵阵哄笑。
终于,行刑官比埃拉开始用力了,只见他使劲一跺脚,那个转盘便飞速旋转了起来,而跪在它上面的加西莫多的面部神情却是大为惊恐。就这样,加西莫多也开始随着转盘转了起来,可是每当加西莫多的身体转到比埃拉面前时,后者便会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上的鞭子,这条细长的鞭子就好像一条剧毒无比的蛇,恶狠狠地抽在加西莫多身上。直到挨了一皮鞭,加西莫多才明白过来,他终于清楚众人围观他的原因了,也终于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了。于是,只见加西莫多拼命地扭动着身子,试图躲过那恶狠狠的皮鞭。
皮鞭就是皮鞭,它绝对会效忠于自己的主人的,它根本不会去怜悯在它下面吃尽苦头的人。一时间,条条鞭影横飞,而一条条鞭痕也留在了加西莫多的背上,鲜血也随着舞动的皮鞭在空中飞旋乱溅,甚至有些鲜血都飞到观众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