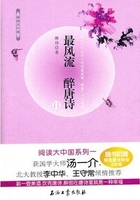福尔摩斯在沙发上思考,表情很严肃。早上天气晴朗,我闲得发慌,恰好福尔摩斯给我送来了信。走进那个熟悉的客厅后,我看到福尔摩斯在沙发上思考,表情很严肃。不知道他又接了个什么案子,好像是考虑一个悲剧性的严重问题。
“是个新主顾吗?”
“对。警察局办不了,像平时一样将皮球扔到了我这儿。现在这个老头儿的境况十分糟糕,许多人和他一样如此痛苦。”
“能说明白些吗?”
“来者是安伯利和布里克福尔公司的一个股东,曾是颜料商,名字叫乔赛亚·安伯利,他攒了一辈子钱在刘易萨姆买了幢房子,准备退休后过平安日子——按理说也能做到。可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他近来有很大的麻烦了吗?否则,他也不来找你的。”
福尔摩斯说:“你说对了,他很不幸。1896年退了休,可能是由于生活孤单,他第二年就娶了个比他小二十岁的漂亮女人。房子也有了,妻子也有了,钱也够花,这晚年应该很幸福了。可由于他娶了这女人,才使他人财两空,这是他的一大错误。”
“我清楚了一点,可我想知道具体情况。”
“实际也很普通,一个很古老的故事只是在安伯利家又重演了一下,因此我说得简单些。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有了富裕的物质生活,就不愿意只和一个老头儿过一辈子了,她还想另找一个情人来满足自己,所以就有一个男人闯进来了。”
我说:“因此他俩就情投意合了?”
“就是这样。这男人是个年轻医生,和安伯利是邻居。他们都爱下棋,便成了朋友。因此,这位叫雷·欧内斯特的医生没事时就去找安伯利下棋,因为经常去安伯利家,所以雷·欧内斯特和安伯利的妻子逐渐由熟识到有了不正当的关系,可我们可怜的主顾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在上周他们俩私奔后,老头儿才知道了。他的结局就是这样。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个女人竟带走了老头一辈子攒的钱,安伯利打算用这钱过后半辈子呢。他们的私奔还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假如咱们追不回这些钱,安伯利将怎样生活呢?”
“咱们帮一帮这个可怜的安伯利吧。”
“的确该这样。可是,华生,你得帮助我。我现在还有个更重要的案子,真没时间去刘易萨姆。安伯利坚持要我去,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难处,他才同意我派一个人去。”
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尽管你对我的工作未必满意,可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刘易萨姆,看看安伯利的家到底被害成了什么样子。
我那天很晚才回来,福尔摩斯仍在等我。
我说:“那儿只有砖路和破旧房子,太单调了。可安伯利的家非常漂亮,好像是一个村庄里的唯一农场主似的。他的宅子叫赫温,被一圈长满了苔藓的高墙围着。”
福尔摩斯说:“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我想听有用的。”
“可以。他家不很好找,街道拐弯抹角的。后来我问了一个高个子才知道。这个闲人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皮肤黝黑,留有大胡子。我问路时,他用一种我看不懂的异样目光看着我。
“我在安伯利家门口见到了他,他好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仔细看了看他,他真的很奇特。”
福尔摩斯说:“说一下你的感觉。”
“他那弯着的腰记载了他多灾难的人生。可他好像不像咱们以为的那么瘦小无能。他的肩膀和胸部很宽大,走起路来也不迟钝,尽管不很利索。”
福尔摩斯说:“你没发现他用了假腿吗?”
“我没注意。”
“我发现他左鞋上有折痕,而右脚没有,因此我认为他有一条假腿。”
“我看见他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头发花白,太多的磨难给他脸上留下冷酷的表情,这些给我印象很深。”
福尔摩斯说:“华生,你看得很仔细。你们谈了些什么?”
“他一开始讲他那不幸的遭遇。他领我进了院子。从外面看这房子还行,可里面到处是杂草,好像从来没修整过一样。我刚一进去,以为这儿没人住!房屋也长年没修了,安伯利正在修整。在客厅里我看见一桶绿油漆,他把木制部分大体油了一下。
“后来在书房里我们谈了很久。我就拣主要的和你说一说,一开始,由于你没去,他觉得有点沮丧,认为自己不受你这种大人物的关注,他好像特别在意。
“他看来的确很痛苦,老人真的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他家的情况很简单,只有夫妻俩,有个女仆白天做家务,晚上六点便走了。只有雷·欧内斯特偶尔去串个门,再没有人和他们接触。在他们私奔的那晚,安伯利曾准备带妻子去某戏剧院看戏。他在二楼预定了两个位置。可他妻子由于身体不舒服就没去看,他一个人去了。他说的是真的,他还让我看了给他妻子买的那张票。”
福尔摩斯很感兴趣地问:“那天晚上安伯利要他妻子去看戏?你看清票了吗?号码是多少?这是个新情况,华生,你做得很好。”
“我记着是三十一号,我上学的学号就是三十一,因此记得很清楚。感谢你的夸奖。一开始,我还怕你对我的任务不满意呢。”
“那他就该是三十二号或三十号了?”福尔摩斯一直问着号码的问题。
“肯定了。是第二排。”
福尔摩斯兴奋地说:“这个线索很重要。”
“他又领我看了他那所谓的保险库,的确很结实。他说一定是那女人偷配了一把钥匙,他们将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债券都带走了。”
“为什么要债券?他们是在逃命啊。”
“不清楚。他说向警察局报了丢失的财产,希望不要卖了债券。他们拿了也相当于废纸。他看完戏后回家,妻子就没了,保险库也被盗了。他这才知道失窃了,因此只好报案。”
“你去时,他正油房间?”
“房间的门窗都油好了。我去时,他正油走廓的柱子。”
福尔摩斯问:“长年没修房子了,这时怎么一下想起修房子了?”
在我面前他还撕了他妻子的照片。“他自己的解释是:人总需要一些寄托。他已经如此潦倒了,他本来也很奇怪,所以做些奇怪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面前他还撕了他妻子的照片,很明显他非常恨她,他还痛骂了一通这两个狗男女。”
“还有别的举动吗?”
“他倒是没有什么举动,可我回来时却被跟踪了。”
“谁跟踪你?”
“我刚才说的那个高个子。我问他路时,他的目光就挺奇怪。我见他在火车站附近跟着我,我下了火车他仍跟着我。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
福尔摩斯自言自语道:“黑皮肤,有胡子,高个子。”突然他问:“戴一副灰墨镜吗?”
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他戴灰墨镜?我从来没和你说过啊。”
他补充说:“他的领带上有共济会的领带扣针。”
“福尔摩斯,你似乎和他很熟。”
“先不说了。其实也很简单,以后再告诉你。还是说这个案子吧。根据你说的,我认为这个案子不简单了。一开始我认为这种私奔的事很简单,可现在事情复杂了。你说的那些都得仔细分析。另外,华生,你还没调查一些重要对象。假如你考虑全了,此案就会更好办了。”
我说:“我工作还是出了漏洞,你说吧。”
“别介意,我不是批评你工作做得不好,只是想让你更完善些。警方为我提供了大体情况,正好弥补了你的那些失误。照邻居们所说,安伯利特别小气,脾气暴躁,特别苛求别人。的确雷·欧内斯特常去找他聊天下棋,肯定也有机会和他妻子说说话,这就不难被认为是偷情。因此大家对私奔也不很奇怪,觉得是很自然的,可是——”
我问:“但你却不这样认为,对吗?”
“现在我还不确定,明天再说吧。今天已做了很多工作了。我们都很辛苦,该轻松一下了。先吃点什么,咱们再去听音乐会。”
第二天一醒来只看到福尔摩斯留给我的一张条子。
亲爱的华生:
我今天要和安伯利谈谈,三点你等我,我办完事就回去。做好准备,我需要你出门。
S.H.
我一整天就等着他回来,不知他干什么去了,神秘兮兮地不和我说清楚。他三点钟回来了,好像不太高兴,像在思考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等安伯利。”
“但他没来。”
“他会来。咱们就等着吧。”
真是这样。老头儿四点钟神情疑惑地来了。
“福尔摩斯,有线索了。我收到一封电报。”
福尔摩斯拿来念道:
接电即来勿误。可提供你有关近日损失的消息。
埃尔曼
牧师住宅
“太棒了,这线索确实很重要,”福尔摩斯说,“你的案子快清楚了,安伯利先生。小帕林顿的电报,那里应该距弗林顿很近。安伯利,你该马上去找那个牧师。既然是个牧师,那他的话就可以相信。”
福尔摩斯去翻了他的名人录,说:“埃尔曼,当地牧师,文学硕士。好,就这样了。赶快查一下火车时刻表,看开往那儿的火车最近是几点?”
我说:“五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