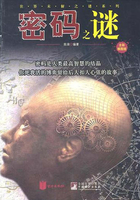雷斯瑞德走了,福尔摩斯这才欢喜若狂地对我说:“华生,你瞧吧!”他无法掩饰住内心的喜悦,精神抖擞,与刚才那平静的样子判若两人。他快速地把地毯拉开,趴在地上,尽力地想抓起每一块方木板。他连续不断地用手指掀木板,突然发现一块木板活动了,如同箱子盖般被翻起来了。下面有个小洞,我的朋友快速地把手伸了进去,不过抽回时,表情难看极了。没想到洞里是空的。
“快来,华生,把地毯放好!”刚刚把木板放好,地毯收拾好,就听见过道里有雷斯瑞德的说话声。我的朋友一副懒懒的样子,靠着壁炉架,无事可干,看起来很有耐心,一边用手挡嘴,打着呵欠。
“福尔摩斯先生,很抱歉,让你久等了,你有点不耐烦了吧!他招认了。麦克弗逊,过来把你办的好事跟他们两位讲讲吧。”
那个大个子警察,满脸通红,一脸懊悔、痛苦的样子,轻轻地走了进来。
“先生,我真的没想干坏事。昨天,有一位年轻女士来到这儿,她说她把门牌号给弄错了,我们俩就聊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在这儿守着不动,真的非常寂寞。”
“那么后来又怎么了?”
“她说很想看一看凶案现场,说她曾在报上看到过。她是个很体面大方的女人,我觉得让她看看又有何妨呢。她一看到毯子上的血迹,就昏倒在那儿了,如同死了一般。我赶紧跑向后边弄了些水来,但还是没能把她弄醒。后来我又去‘常春藤商店’买了点儿白兰地,但等我把酒拿回时,她早已醒来并走掉了。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不好意思,不敢再见我了吧。”
“可是地毯为什么会被移动了呢?”
“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地毯有些不平。你想想看,她倒在了地毯上,而地毯又没有固定在光滑地板上,所以就弄得不平了。而后我把地毯弄平整了。”
雷斯瑞德严厉地说道:“麦克弗逊,这回算作教训,下不为例。你肯定认为你对工作不负责不会被人发现,不过我只要看一下地毯,便知道有人进来过,没丢什么东西算你运气好,否则的话,少不了要吃苦头。福尔摩斯先生,为了这点儿小事,请你来真对不起。或许你对这两块不同的血迹会感兴趣。”
“是的,我非常感兴趣。警官,这位女士就来过一次吗?”
“是的,只来过一次。”
“你认识她吗?”
“我不知道她是谁。她是看广告来这一带应聘打字的,走错了门,是位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士。”
“个子很高,是吗?非常漂亮?”
“一点也不假,她外表非常好看,也很有气质。她说:‘警官,请您让我看一下吧!’她很有方法,还会套近乎。我本想让她从窗子那儿看看的,我觉得那样做没什么。”
“她打扮上有什么不同?”
“很高雅,穿了一件拖到脚面的长裙。”
“在什么时候?”
“当时天刚刚黑下来,我买酒回来时,人们早已点上灯了。”
福尔摩斯说道:“太棒了。走吧,华生,我们还必须到别的地方去,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
我们离开这儿时,雷斯瑞德依然留在前面的屋子里,那位警察为我们开门。福尔摩斯走到台阶那儿,转过身时,手里拿了件东西,这让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大喊道:“天啊!”我的朋友把食指贴在唇上,示意别讲话,而后把这个东西放进衣袋里,得意洋洋地走到街上,这时他放声笑了。他说:“你放心吧,绝不会有战争了。特里劳尼·霍普先生的光辉前景也绝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那位不太谨慎的君主更不会受到惩罚的,首相也不必担忧欧洲局势会有怎样的复杂变化了。只要我们运用些手段,这件事肯定会很好地得到解决的。”
在我心中,他真的成为一位特殊而又特别的人物了。
我忍不住大喊道:“你已经把问题弄清了吗?”
“华生,我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几点没有完全弄清楚。不过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已经挺多了。如果还不能把其他的问题弄清楚,那就是我们无能。现在我们得去趟白厅住宅街,来了结此事。”
当我们到达欧洲事务大臣官邸之后,我的朋友要找的却是希尔达·特里劳尼·霍普夫人。我们进了屋。
这位夫人一脸愤怒地说道:“福尔摩斯先生,你太不讲信用了,也不公平,更不宽厚。我已经同你解释清楚了,我希望你能为我保密,以免我丈夫以为我干涉他的事务。可是你为何要来这儿,以示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务联系,来损害我的声誉?”
“夫人,没有办法呀。既然我受人之托找回那封非同一般的信件,只能请求您把它还给我了。”
这位夫人忽然站起身,美丽的容颜变得非常难看。她那双眼盯着前方,身体不停地颤抖,让我以为她会晕倒。她勉强打起精神,尽力使自己保持平静,刹那间,她脸上极其复杂的表情完全被愤怒与惊讶掩盖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在侮辱我!”
“夫人,冷静点,你用这些手段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是把信交给我吧。”
她朝手铃奔去。
“管家会过来把你请出去的。”
“希尔达夫人,没有必要摇铃。如果你摇了铃,我所做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流言蜚语会紧随其后。你要是把信交给我的话,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如果你我好好合作,我会安排好一切。你如果与我作对,我就去揭发你。”
她似乎对此并不惧怕,显得非常威严。她那双眼紧盯着福尔摩斯的眼睛,企图把他看透。她把手放在手铃上,但是还是抑制住而没有去摇它。
“福尔摩斯先生,你想吓唬我,你到这儿来恐吓我,这不是大丈夫所为。你说你了解一些事,到底有什么事呢?”
“夫人,请你坐下,如果摔倒的话,会伤着你的。你不坐下的话,我绝不说。”
“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给你五分钟。”
“希尔达夫人,一分钟就足够。我清楚你曾去过艾杜阿多·卢卡斯家,你给过他一封信。我也了解到,昨晚你又一次巧妙地进入了那房子。我更清楚,你又把这封信从地毯下的隐蔽处拿回来了。”
她盯着我的朋友,脸色惨白,有两次她气喘吁吁,欲言又止。
过了一阵儿,她大喊道:“你疯了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硬纸片,那是在照片上剪下的面孔部分。
福尔摩斯说道:“我时常把这个带在身上,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那位警察已经把你认出来了。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靠回椅子上。
“希尔达夫人,如果信在你这儿,那还来得及纠正错误。我不愿给你找麻烦,我把它交给你的丈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希望你能采纳我的建议,并开诚布公,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她的勇气真的让我赞叹,事已至此,她还不认输。
“福尔摩斯先生,我再说一遍,你太荒谬了。”
我的朋友起身从椅子上站起来。
“希尔达夫人,我对你的表现感到非常遗憾,我已作了最大的努力,这一切都算白费了。”
福尔摩斯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特里劳尼·霍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十二点四十五分回家。”
福尔摩斯看了看他的手表,说道:“还有十五分钟,我在这儿等他。”
管家刚离开这屋子,希尔达夫人就跪在我的朋友脚下,她把双手摊开,仰头看着他,眼里饱含着泪水。
她苦苦地哀求道:“你饶过我吧,福尔摩斯先生,宽恕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告诉他!我非常爱他!我不愿让他心里有一点点不愉快的事,不过这件事肯定会把他的心伤透的。”
福尔摩斯扶起这位夫人。
“太好了,夫人,你总算明白了。时间太紧了,信现在在哪儿呢?”
她快速地向一个写字台走去,拿起钥匙把抽屉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封信,信封相当长,而且是蓝色的。
“福尔摩斯先生,信就在这儿,我保证从未打开过它。”
福尔摩斯小声说道:“怎么把它放回去呢?快点,我们得想个好办法,现在文件箱在哪里?”
“还在他的卧室里。”
“太棒了!夫人,快把那箱子拿过来!”
过了一会儿,她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扁箱子。
“原先你怎样把它打开的?对,肯定有一把复制的钥匙,是的,你肯定有。打开箱子!”希尔达从怀中取出一把小钥匙。打开箱子之后,里面装的全是文件。福尔摩斯把信塞到靠下边的一个文件中,夹在两页之间,关上箱子,上好锁,她又把箱子送回卧室。
福尔摩斯说道:“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你丈夫回来了。大概还有十分钟吧。希尔达夫人,我为保护你可出了不少力呀,剩下这十分钟,你应把一切坦白地告诉我,说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件不同寻常的事?”
这位夫人喊道:“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告诉你。我宁愿断自己的右臂,也不愿我丈夫有一点儿忧伤!我想恐怕整个伦敦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女人像我一样深爱自己的丈夫了。不过,要是让他清楚我所做的事,不管我是出于什么动机做的,他都决不可能原谅我。他很重视他的声望,所以他对任何人犯过的错都不会忘记或宽恕的。福尔摩斯先生,你必须救我!我俩的幸福以及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夫人,快说,时间不多了!”
“先生,问题就出在我在婚前写的一封信上。那封信写得不够慎重,也非常愚蠢,我是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写完的。我的这封信一点儿恶意也没有,不过要是让他知道了的话,肯定认为这是犯罪。如果让他读过的话,我想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我一直想忘记这件事,不过,后来卢卡斯这个混蛋写信告诉我,说信就在他手上,还要把它交给我丈夫。我恳求他不要这样做,他说我必须把他要的文件拿给他,才把信给我。我丈夫的办公室有间谍,说过有这么一封信。他向我发誓,这绝不会给我丈夫带来任何损害的。福尔摩斯先生,从我的处境来看,我能怎么做呢?”
“把这一切告诉你的丈夫。”
“不行,福尔摩斯先生!这不仅会毁了我们的幸福,而且事情会变得更加可怕。所以我才敢去偷丈夫的文件。不过在政治方面,我真不知会有怎样的恶果,而我也理解爱情与信任两者都非常重要。福尔摩斯先生,我拿来钥匙模子给了卢卡斯,而后他给了我一把复制的钥匙。我打开我丈夫的文件箱取出他想要的文件并送到他家。”
“那儿有什么情况?”
“我按照约定的方式敲了门,他把门打开后,我随他进了屋,不过因为我非常恐惧与这人单独呆在一起,我没有把大厅的门关严。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我进屋时,发现外面有个妇女。我们很快办完了事,我的信就摆在他的桌子上,我把文件交给他,他把信还给我。就在这个时候,房门那儿有声音,而后传来脚步声,卢卡斯赶紧掀起地毯,把它塞进一个能藏东西的地方。之后又把地毯盖上。
“那以后发生的事如同一个恶梦。我看见一个妇女,黝黑的皮肤,神色有些疯狂,我还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她用法语说道:‘我总算没有白白等待,让我看到你与她在一起!’他们两个非常激烈地打斗起来。卢卡斯手里拿起一把椅子,那妇女手里拿着把闪亮的刀子。当时太恐怖了,我赶紧向屋外冲去,离开了那栋房子。第二天我在报上看见他被杀害的消息。那天晚上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把我要的东西拿回来了,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只不过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过来,我又有了新的烦恼。我丈夫遗失文件后的焦躁令我不安。当时我差点就跪倒在他脚下,跟他说信是我拿的,但这就要把我的过去说给他听。我那天早晨去你那里,就是想把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搞清楚。从我拿走那封信的那一刻起,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它弄回来。如果不是他当着我的面把那封信藏起来,我是不会知道信藏在哪里的。我想自己怎样能进去呢?我一连好几天都去那儿,但门总是被关得紧紧的。昨晚,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想你已经知道我是怎样拿到的了吧。我把这文件带回来,本想把它毁掉。我无法把它还给我丈夫,而又不必承担这个错误。天啊!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了!”
欧洲事务大臣快速地跑进屋子。
他说道:“有什么消息,福尔摩斯先生?”
“有希望了。”
他的脸上显出惊喜的表情。“谢天谢地!首相正要与我共进午餐呢,他能够来听吗?他神经非常紧张,自从发生这件事后,他就再也没有睡过觉。雅各布,把首相请到楼上来。亲爱的,我认为这事与政治有关,我们一会儿再去餐厅吃饭。”
首相举止沉稳,不过从他激动的目光里与不停颤抖的大手中,我知道他非常兴奋。
“福尔摩斯先生,听说你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我的朋友回答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的地方我全都查过了,但是仍没有找到,但我确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福尔摩斯先生,那可不行。我们绝不能整日整夜地坐在火山口上,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才可以。”
“因为有希望找到文件,所以我才来这儿的。我感觉到这文件绝不可能离开你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被人取走了,那么现在肯定已经发表了。”
“难道有人偷走它只为在家中收藏吗?”
“我绝不会相信有人取走了它。”
“那么为什么信件又不在那个文件箱中呢?”
“我觉得信件很可能还在文件箱里。”
“福尔摩斯先生,在这个时候还开玩笑就真的不合适了。我确信它不在箱子里。”
“你从周二早晨起,是否再查看过箱子呢?”
“没有这个必要。”
“你是否想到也许你在查看时疏忽了呢?”
“这绝不可能。”
“我不是讲非得这样,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很有可能发生。我认为箱子中肯定还有别的一些文件,也许混在里面了。”
“我把它放在最上面了。”
“也许曾有人晃过箱子,把它给弄混了。”
“不,不可能,我曾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过。”
首相说道:“霍普,这还不好办,我们再把文件箱拿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大臣摇铃。
“雅可布,把文件箱拿到这儿来。这真的太可笑了,纯属浪费时间,但是我又没法把你说服,只好这样做了。谢谢,雅可布,放到这里来,钥匙在我表链上。你看看这些文件,麦马勋爵的来信,查理·哈代爵士的报告,马德里来信,弗洛尔爵士的信。天啊!这是什么?贝林格勋爵!”
首相急忙地从他手里拿过那封信。
“是呀,正是这个。信真的没有被动过!霍普,我祝贺你。”
“谢谢你,非常感谢!我现在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我实在无法想像。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个巫师还是个魔术师?你怎么会知道它在这里呢?”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快速地走到门那儿。“我的妻子现在在哪儿?我要告诉她事情已经结束了。希尔达!”我们听见他大喊。首相望着我朋友,眼睛不停地转。
他说道:“先生,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文件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避开了那双好奇而古怪的眼睛。
“我们有自己的外交手段。”他边说边拿帽子走向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