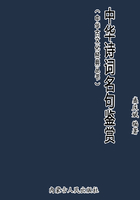上官府祁荣居,书房内,一玄色衣袍男子端坐在案几边,另一黑袍男子一手置于后背,神色凝重地打量着正在看着卷宗的男子,缓缓,寂静的房间里,手指苍劲有力地敲着案几,“上官镕谟,符羲山庄依然没有什么动静吗?”
上官镕谟紧锁眉头,声无波澜地应道,“回皇上,臣认为符羲山庄并非如皇上所想。”
“哦?”慕容展挑眉阴沉地冷笑道,“上官镕谟,你不会是心疼你的三妹妹,不想让她守寡,故意要为符羲山庄开脱吧?”
“臣不敢,男儿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区区一女子怎么可以和社稷相提并重。”上官镕谟从容地回了一句,瞧着慕容展缓和了脸色,上前将衣袖里面的画卷递给慕容展,“这是暗卫从漓宫窃取回来的。”
慕容展凝重地扫过一副简单平凡的山水墨画,若有所思地念道,“上官镕恺还没有归来?”
“二弟自四年前留书出走塞外未曾寄过任何家书回家,许是心性未定,无心官爵。”上官镕谟泰然自若地应答,慕容展将信将疑地察视了他一会儿,轻缓地合上字画,平心静气地起身。
“尽快查出上官镕谟的行踪,至于符羲山庄,让暗卫盯紧点。”慕容展威严地立于窗边命令道,上官镕谟点头应了一声,脸上仅有的一丝轻缓转而变成嗜血的森冷。
兰凝居的居所,一边思索一边和怜怜玩得不亦乐乎的上官槿夕眉头跳动了一下,整颗心莫名地悬到半空中,忽然惊颤地抖动了身子,一旁的云溪担忧地覆上槿夕冰凉的手,疑惑道,“小姐,你没事吧?”
槿夕摇头,看着在地上玩耍的孩子,紧锁着眉头,“怜怜最近没有什么异样吧?”
“回小姐,怜怜最近厌食得厉害,昨晚身子还忽冷忽热的。”云溪惊惊颤颤地将近日来的所有症状一一讲述。
槿夕听得心潮起伏,拽着衣摆,心痛不已道,“云溪,你让桐儿带怜怜到别处玩,你看跟我进内室。”
“是,小姐。”
云溪拉起扑在地面的怜怜,将她领到站在屋外打理着花草的桐儿,转身合上内室的大门,默不作声地跟在上官槿夕的身后。
上官槿夕思索了一会儿,将衣袖里面的手绢拿出来,端详了一会儿,云溪一头雾水地看着那幅山水画,不解地问道,“小姐,这是什么?”
上官槿夕睨了放在床头的白绢,递了云溪一个眼色,“云溪,你把那条白绢拿过来。”
“是,小姐。”云溪恭敬从容地走至床榻,一脸困惑地将白绢执起,好奇地将其递给带着淡笑地上官槿夕,上官槿夕接过白绢,轻轻地将白绢至于桌面上,平展,拂开褶皱,而后又把那画着水墨画的手绢至于白绢的旁边,手执湖笔,冥神专注着思量着水墨画上的每一笔一墨。
待上官槿夕将执起的笔放回笔架上,云溪目瞪口呆地看着白绢上的墨画,仰慕地盯着那毫无偏差的笔墨,赞叹道,“小姐画得太好了,连皇宫里的画师都比不上小姐。”
上官槿夕抿唇,睨了一脸崇拜的小丫头一眼,“要说画艺精湛,槿夕还不上二哥。”
“二少爷是神来之笔,不过二少爷都已经在外游玩了那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云溪嘟着嘴角怨道,要是四年前上官镕恺不突然离家到塞外游玩,她家小姐就不会老是被府里的人欺负,连带羽夕小姐也经常受大少爷上官镕谟的臭骂。
上官槿夕不是看不懂云溪眼中的哀怨,只是二哥虽然爱玩,但从不会像四年前那样留书一走了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书信寄回家中报平安。
沉思间,门外桐儿敲了敲房门,毕恭毕敬地喊道,“小姐,大少爷的贴身侍卫安鉴相见小姐。”
“好。”上官槿夕微笑着回了一声,低头看着墨迹已干的白绢,匆忙地将其折起,塞到云溪的衣襟里,压低着嗓音吩咐道,“云溪,找个时间将这白绢交给大哥,千万不能让被别人发现。”
“云溪明白。”云溪严肃地点头,将白绢塞好。
上官槿夕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小手握成的拳头依旧垂在身子两侧,屏息凝神地开门走出内室。
外室,立在桌面安看着低着脑袋走出来的云溪,黝黑严肃的脸上泛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红晕,毕恭毕敬地朝上官槿夕跪下,“大少夫人。”
上官槿夕被安鉴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让云溪将安鉴扶起来,安鉴莞尔一笑,拂开云溪的手,依旧跪在上官槿夕的身前,羞涩道,“大少夫人,请您将云溪许配给安鉴,安鉴定会一生一世照顾云溪,不会让她受一丁点儿委屈。”
云溪吓得一动不动地眨巴着眸子,整个人呆泄着立在一边,上官槿夕疑惑的脸上挂上欣慰的笑容,含笑的眸子转向云溪,轻柔地问道,“云溪,你愿意嫁给安鉴安侍卫吗?”
云溪心口扑通扑通直响,瞧了安鉴一眼,慌张地垂下脑袋,绞着手指纠结着,安鉴惶惶不安地盯着云溪那忽喜忽悠的脸色,疼惜地喊道,“云溪?”
云溪背脊一直,严肃地看着槿夕,决绝道,“小姐,云溪不嫁安鉴。”
“云溪?”安鉴慌了神,不顾礼节地站起来,紧握着云溪的手,云溪冷淡地扫了他一眼,踱步到槿夕的身边,决然地跪在槿夕的跟前,乞求道,“小姐,云溪对安鉴一点好感也没有,请小姐为云溪做主,云溪此生绝不会嫁给安鉴。”
安鉴听着云溪的话,心隐隐作痛,眼中泛着苦涩的滢光,上官槿夕拉起跪在地面的云溪,无力地对着安鉴念道,“安鉴,你先回去吧,这事我再和云溪说说。”
安鉴看着云溪那冷漠无情的脸,哀痛地留下一句话,“不管你以前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安鉴都不会嫌弃你,怜怜,我会待她如亲生女儿。”
上官槿夕看着安鉴垂着脑袋走出兰凝居的外室,拽起云溪的手,心疼道,“云溪,安鉴是个好夫婿,小姐不能再对不起你。”
“不要,小姐,云溪生死都是小姐的人,不能因为一个安鉴就小姐和怜怜至于水深火热之中。”云溪哭喊着拉着槿夕抽泣哀求,没有上官槿夕就没有她云溪,安鉴的情就当是她负了,下辈子再还。
“云溪,已经为我们牺牲够多了,反正怜怜的事迟早都会有人知道的,但是安鉴就只有一个,错过了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小姐也会自责不安的。”上官槿夕柔声地安抚道。
云溪不从,死命地咬牙摇头,扑通地跪在地面上,抽出发钗直对着自己的脖颈,“小姐,云溪曾对着夫人起誓,若是无法保护好小姐,云溪就以死谢罪。”
“云溪。”上官槿夕手足无措地嚷道,“你知道大哥为什么肯让怜怜跟着我们回符羲山庄吗?”
云溪摇头,槿夕无力地叹息着,含泪地倾诉,“除了在怜怜身上种下蛊毒威逼我们查出符羲山庄的秘密,就是要让怜怜有朝一日身份被人揭穿,让所有的人来羞辱我。云溪,大哥恨我不是一天两天的,在他的心里,我和娘亲就是害死他母亲的侩子手,他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我们的。”
“可是,小姐,若是安鉴和云溪成亲了,必定知道怜怜不是云溪的女儿,到时盟主一定会怀疑到小姐的头上的。”云溪梨花带雨地哭诉道,她未经过男女之事,但在上官家的下人里耳濡目染总会多少知道一些,是不是清白之身,只要一洞房,安鉴势必知道,而安鉴又是符廷的贴身侍从,对符廷毕恭毕敬,一定会合盘托出。
“云溪,这一次你就听小姐的话嫁给安鉴,至于成亲之后,一切就看天意。”上官槿夕不容抗拒地命令道,云溪摇头,忽而眸子一转,瑟瑟道,“小姐,不如试试底下里那些大婶的药草法子,那样安鉴就不会知道云溪是否是清白之身。”
上官槿夕不悦地蹙起眉头,转过身呵责道,“云溪,小姐不能让你做这样的蠢事,否则你就不要认我这个小姐。”
“可是,小姐……”云溪努努嘴抗议地直起腰板。
“云溪,你不要再说,我这就去和盟主说这事,你就乖乖等着当安鉴的妻子。”槿夕急切凌厉地命令道,不等云溪开口,已经小碎步踏出外室,只要在东窗还事发前拿到解药,那么她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带着怜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至于云溪,有安鉴护着,她就不用太担心。上官槿夕凝重地下定决心,脚下步子迅速地往前迈,心情沉重地往靑珽阁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