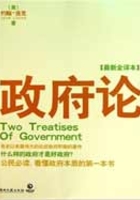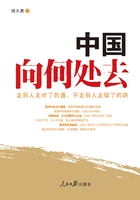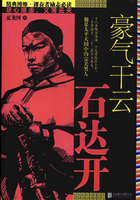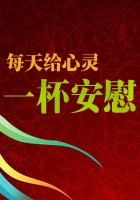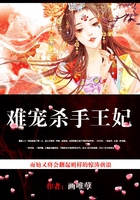一、毕生的血汗谋求的只是臆想的“安全感”
现在,人们几乎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和“拥有安全感”划等号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才算有了自己的家,所以,从城市到农村,谈婚论嫁的首要条件就是男方是否拥有住房。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打工者在农村和老家的房子只是给了打工者一个拥有安全感的安慰,其实并没有给打工者真正的安全。打工者为了建房和买房付出和预支了毕生收入,但是结果是,这个安全感其实也只是个想像。
打工者虽然无法回归农村也不想回归农村,但是因为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最后很多打工者还是把“物质的家”(房子)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为了偿还买房的贷款或者欠款、为了维持自己和孩子的花费,打工者不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必须继续打工,也就是说即使打工者真的有一天回到自己建设的“家”(养老院)也一定是在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但是那时候就需要被人照顾了,但是谁会照顾这些人哪?现在80后的父母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照顾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但是不久的将来谁来照顾这些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80后的在农村的父母?同样,等到80后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回农村吗?如果回去谁来照顾他们哪?所以,我的想象是70后和80后现在在农村建设的“养老院”将来都会是空巢,都是巨大的浪费。用毕生的血汗钱谋求臆想的安全感,这不仅造成的是“生活不在当下”的精神问题,而且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很多打工者用一辈子的血汗为自己建设的是回不去的“养老院”。
二、断裂的社会制造分裂的人
2002年孙立平老师提出了“断裂的社会”的概念135。在断裂的社会里,人们虽然处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却处在不同的时代。在北京和上海,是高度城市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在深圳和东莞是工业化的社会;而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却还处在落后的农耕时代。
在断裂的社会里,人们虽然身在同一个地方,但是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却有天壤之别。在北京城市的中心是林立的写字楼、金融中心、商城和高档公寓;在城市中产阶级公寓的地下室住着保洁工、保安和小时工;在5环外和6环外住着从事着各行各业的打工者。
在这样断裂的社会里,生活优越的人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觉不到也不想感觉底层人们的生活;相反,这些人故意或者假装无意地维持社会的不公,因为这样的社会可以为有权有势的人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便利便宜的各种服务。
过去,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限制,生活在农村的人也许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对外界的认识和感知很少很少,那个时候社会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即使有社会差异,也不会直接产生社会断裂和人格分裂。现在2亿多的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他/她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到优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她们和这些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直接制造了无数生活和人格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制造无数充满失败感、对社会不满、迷茫和躁动的人:打工者下班不能“回家”;打工者的孩子在农村是留守儿童;打工者的孩子在城市是流动儿童;打工者预支一辈子的血汗钱建设回不去的“家”;狭窄破旧的城市边缘的出租屋旁最重要的广告是“宽带上网和有线电视”;在水泥围墙和林立的厂房中生活的打工者热衷名牌、时尚、手机和婚纱照。
在断裂的社会里产生的是分裂的人。
打工者从身份上是分裂的。打工者来自农村,户籍属于农村。对于户籍来自农村的人,我们不按照他/她们做什么来称呼他/她们,而是一律称呼他/她们为“农民工”。如果说一个人兼职农业和其他行业,那么这个称呼还有情可原,但是我们这样称呼打工者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工作的内容,而是对于身份的一种标签。来自农村的人就是农民,这些人即使从事其他的工作也还是农民,因为社会只愿意给这些人农民的待遇。所以这个标签的含义不是行业的称呼,而是身份的标签,目的是达到歧视和不支付这些人的劳动的社会成本。这样的称呼造成了打工群体身份分裂。社会中的歧视、利益至上和冷酷在维持着这样的一种分裂。
打工者与土地的关系是分裂的。并不是所有的打工者在农村都有土地,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在农村盖房。不能成为农民,没有土地,在那里也找不到工作,但是却要在那里预支所有的血汗钱盖房子,这就是打工者和土地的“爱”与“恨”的关系。打工者虽然从名义上没有放弃土地,但是从行动上已经放弃农业了,每个人不到1亩的土地,小农户不放弃土地能有什么出路哪!如果国家不做长远打算,土地将被资本掳获,最后有的打工者也许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农场主打工。
打工者的“家”的概念是分裂的。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是想像中老了以后才能回去的地方(养老院)。我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开始有几次我不经意地问:“你的家有多远?”工友说:“坐火车20多个小时”,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工友理解的家是老家。还有几次,我问工友:“每天什么时候下班回家?”工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哦,下班时间?一般是晚上9点,然后回出租屋。”我意识到,工友不认为出租屋是家。我还发现,对于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工友,工友会对孩子说“放学回家”这样的话,感觉是:无论在哪里,如果一家人在一起也许也可以勉强称之为家,而且对于孩子来讲父母就是家。
三、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下的“用工荒”
当人数巨大的打工群体处在这样断裂的、分裂的、躁动的、貌似有很多可能性却别无选择的社会里,“离开”和“流动”成了打工者别无选择的选择。离开可以只是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流动也许是从城市回到老家然后又回到城市。这就导致了中国现在不缺劳动力却存在“用工荒”的现象。“用工荒”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的断裂和人靠臆想来生活。
前面分析了“用工荒”的三种表现形式,“春节前后阶段性用工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断裂导致的,而“持续性用工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导致的。打工者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不能安居乐业、又不能回农村也不愿意回农村,所以只能在迷茫和躁动中流动,去寻找可能性或者哪怕只是太腻烦了去换个环境。
四、让新工人在城市住下来
在打工者工资这么低的情况下,很多打工者都可以用自己一辈子的血汗钱花10万20万买房子、盖房子,如果社会和资本的运行稍微健康一点儿的话,打工者不用任何人的恩赐就可以在城市建立新生活。但是在权钱结合和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社会没有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这些在资本的运作下,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噩梦。
官员们为了赢取产业转移落户本地的机会而四处奔走、专家学者们论证着产业转移的趋势、优势和障碍,但是我们很难听到打工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声音。在资本和权力共谋下,不仅大中城市的房价一路攀升、一些小城镇的房价也已经大幅度上涨。为了能够拥有一个家,哪怕只是臆想中的、哪怕只是符号性的,打工者都要支付和预支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
当我读到李昌平老师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解决打工者在城市居住问题的可行性出路,但是这个出路只有在资本和权力受到社会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下面就原文摘抄李昌平老师的文章136:
“‘农民工’其实是‘新工人’,已经有1.7亿人到了城里,但没住下来;未来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新工人’。每一个‘新工人’都有享受基本住房的权利,不能指望市场去完成,落实这项基本人权是政府的头等责任之一。
“主要的做法就是,政府在城市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建设‘新工人’的居住区——‘新工人公社’,每个‘新工人公社’以30000人为上限,每套住房的面积在40~5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过800~1000元/平方米(和县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当)。也可以由‘新工人公社’的社员自组工程队,自主建房。
保证‘新工人公社’的住房价格控制在800~1000元/平方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土地价格15万元/亩,容积率按5计算,每平方米分摊地价46元/平方米;地面建筑费用约为650元/平方米;其他辅助费用105元/平方米。在中小城市,价格可以更低一些。一对‘新工人’,工资在1600元左右,每月用400~500元供房,大约6-8年可以还清3.2万~4万的住房贷款。‘新工人’就可以在城市长期住下来了。6-8年后,如果还清房贷的‘新工人’需要更大的房子,‘新工人’可以将面积在40~50/平方米的旧住房按原价转让给‘新工人公社’,申请‘新工人高级公社’的标准房,每套标准房以70~8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还清标准房贷款的‘新工人’,如果需要更好的住宅,可以将标准房照原价转让给‘新工人高级公社’,并申请政府住房(按照工龄)补贴,进入市场买房。
“政府还应当扶持‘新工人公社’和‘新工人高级公社’发展成‘消费合作社’,扶持农村‘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新工人消费合作社’联盟,降低‘新工人’生活成本。政府也要帮助‘新工人公社’建立社区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体系、文化体育设施等。
“在城市建设‘新工人公社’,有利于政府集中资源有效解决‘新工人’的各种困难,也有利于‘新工人’团结互助应对城市生活,还有利于节约城市管理成本,并实现有效管理。
“让‘新工人’在城市住下来,还需要农村农业政策的配合:需要逐步将农民和农村纳入公共财政覆盖范围,让农民、农村享受市民、城市同等待遇;需落实宪法‘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给村民集体发放土地产权证明。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和村社土地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土地金融体系,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产权,获得土地产权‘证券化’资本收益。”
在结束这一编的时候,摘录2011年“新工人艺术团”出品的第五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来表达我们对社会现状的疑问和思考:
为什么
词:孙恒
陕北民歌曲调改编
为什么高楼越来越高,
盖楼的人一辈子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教育都和世界接轨了,
孩子们上学却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人和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物价不停地在上涨,
可怜我口袋里的工资却永远也赶不上?
为什么经济飞速地增长了,
贫富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了,
有钱的人有闲的人却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精神和内心却越来越空虚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