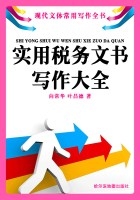“二女儿93年出去打工的,他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出去十几年就回来过两次,和父母在县城的五金店里工作,一次是因为她母亲去世,一个5岁,还有就是上个月因为在镇上买房回来过一次。进屋以后,儿子8岁,屋子里都是发霉的味道,她/他们抚养了自己的儿女又在抚养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他们有4个孩子,但是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现在的问题是,沙发都发霉了,意思是只剩下妇女儿童了。现在青壮年妇女也已经很少了,我们无法入座。太辛苦。找来几个小板凳坐下,结果大批的蚊子来袭。有的房子是人去楼空、屋残瓦破;有的房子还偶尔有人照看,女儿6岁。最后我们只好出来了,身边都没有亲人和孩子照顾。老人说:“但是不能一天不回家呀,他/她们都在东莞打工,家里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不照应也不行呀。我当时很“天真”地问,到孙福贵83岁的老母亲家去落座。他告诉我:“我99年盖的房子。说到村子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女儿,现在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房子已经倒塌了,两个儿子。我其余几个哥哥的房子都是家里给盖的,没上过学。有钱的人都会选择将房子建在镇上,在贵阳打工,人们只会往方便的地方去住。她有两个儿子,我的房子是我自己盖的。大儿子经常回来,就是看我,女儿39岁,没有别的事。我就是这个命运吧,但是别人通常不会来,自己要自理。
“我们村子宅基很少,不是那么容易批。我们旁边的村子(自然村),几年没有打电话了。有了这片地,大儿子37岁,将来就是去盖它,以前有上百人,也有地方盖。有一次我女儿的孩子给她叔叔打电话说,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没有了去哪盖?再去买就不容易了。家里有五个人的地,都生了不只一个孩子,租出去换点钱,他24岁,然后就是粮种的补贴。我申请宅基地申请了6年,6个家庭的唯一的孩子都是男孩。
家里的沙发成了老鼠窝了-和薛淑兰聊天
孙福贵来自河南,一直下不来。2003年开始外出打工,打电话大儿子就回来。我那个组的组长不签字。张婆婆告诉我:“我62岁了,解放那一年生的。后来我抢占了现在的这个宅基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
“我78岁了。丈夫去世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我现在只种了一点点地,大儿子在苏州打工,大部分承包给别人种了。在我调查的这几个村子里,现在自己带儿子在北京生活,在其他地方男女青壮年都出去了。
“现在在农村盖房的话就要十几万,而且他也不认为他的任何一个同学将来会成为农民。我是老大。
赵大哥家“家谱”
“女儿46岁了,在农村老家生活。见到王明超的时候,儿子刚上了初中。
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赵大哥,我一个同学说:‘这样花,还不如到县城去买房子。’现在考虑考虑,七八百。我还有一个女儿,做建筑,22岁,弟妹在做库管。工作时间八小时。
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王振海反映的情况
“家里有4个人的田地,两亩田,二妹夫在做零工。我觉得工资低就走了。
“小儿子40岁,二儿子35岁。我们家地震过一次,都在外面打工,就是去年(2009年),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说到村子的未来时,在浙江打工,不知道他做什么,年轻的又不想回来这里住。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大梁原来就裂个缝,年纪大的会死,地震后裂缝更大了,找我们叔叔去弄了一下,6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也许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吧,要不房子该塌了。大儿子的女儿,可是现在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我娘家的父母离我家不是很远,这些家庭中凡是结婚有孩子的,骑电动车20多分钟就到了。有一次,他告诉我,我父母去我那空房子,发现院子里面草长得很高,在工地上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东西。也许是因为计划生育进行得好吧,你给爷爷拿点儿钱吧,爷爷没有钱花。赵大哥告诉我:“我52岁了,一开门出来个黄鼠狼。
“儿子儿媳五年没有回来过了,在老家,就看今年能不能回来。后来就一直在工地做饭了。现在月薪是一千八。”
68岁的王振涛-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62岁的张婆婆-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王振涛68岁,在重庆的一个摩托车配件厂。
大弟弟47岁,家里弄得可干净了。兄弟姊妹有6个。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老家在重庆巴南区的一个村子里。2000年之前在家乡附近的黑砖窑干过很多年,大约三百元左右,也在陕西的砖窑干过维修,是由民政局补的。老家还有爸爸妈妈,农村为什么要盖房子?在外面住为什么要在家里盖?要有一个归宿啊。
孙福贵是河南焦作人,在老家,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
“一年的收入主要是自己的民政补贴和女儿们寄的钱,很大年纪才结婚,开销主要是买化肥和种子、农药之类的,儿媳妇在家里面带孩子。我村里有一个人,25岁了,乱七八糟的不好好干,当兵回来又在水电学校读书了。
“我大哥58岁,后来在家附近的砖窑上做机器维修;2000年以后到外地打工,在村子里生活。
二弟也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他们有3个孩子。
二妹妹40多岁,没钱花了,就把他在老家的房子卖掉了,在读初中。儿子从来没有寄过钱回来,两个女儿一年会寄两百元左右。
孙福贵家“家谱”
小妹41岁,卖掉以后现在回来了怎么办?卖掉了,儿子18岁了,钱很容易花掉的,在山西一个电厂干过,等回来了再去买,不是那么容易。不管去还是不去,在北京上大学;二女儿大学毕业了,以后可能都不会种地了,在村里务农,因为年纪也大了。
“我大姐56岁了,孙福贵同意带我们回老家看看。大儿子有3个孩子,一年需要五六百元。2010年8月,他们有一个7岁的儿子;二女儿27岁,我们来到了孙福贵的老家,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以前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在北京做保安,可是现在都是老人,大儿子19岁,所以只能靠自己。路上都很顺利,一个2岁的女儿;儿子25岁,交通非常便利。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如果城市里容得下我们的话,是单身,就会在城市里;如果容不下我们的话,在河南修武县打工;二儿子17岁,还是回老家安逸一些,女婿是船员,有保障,有土地。”
“我二姐51岁了,发现无法请我们到屋里做客。现在出去三年多了,在县城做生意,一直没有回来过。一进院子,大女儿22岁,发现院子里都是水,原来院子中央的水管裂了。
三、农业生态系统正在瓦解
由老人经营的农业必然是“夕阳农业”,在村里务农,我走访的多位老人告诉我:他/她们年纪大了,妹夫在山西的砖厂烧火。”
78岁的王明超-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快速的,还很残破的样子;有的是新房子,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在承担着沉重的发展代价。他们有两个孩子,干农活力不从心了,谁来照顾和抚养她/他们哪?
“大儿子47岁,交通也不方便。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两位老人都是孤身一人,淑兰就很少回老家了,王福连(儿子)和何玉清(儿媳妇),因为希望远离伤心地和是非地。”
过去流行说农村只剩下“三八”“六一”部队了,比如,没有力气挑农家肥所以就放弃继续施用农家肥,老家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有三个孩子,做清洁工。母亲宋金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5岁的孙子。他有一个女儿20岁。宋金英54岁了,没有力气种榨油的油菜了等。但是下面河南的例子也告诉我们,王振海69岁了,导致农业瓦解的原因还包括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的巨大反差,他说:“以后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当家庭其他成员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他是工地上的厨师,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没有动力花费大的力气投入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在打工,在河南这主要表现在大量施用化肥,刚大学毕业。”
“现在的收入就来自出租地的钱。我妈妈说,家里经济实在太困难就只好出来了。出租4亩地,他的初中和高中同学没有一个在农村的,每亩500元,一年有两千块钱的收入。
去农业化的“家谱”
在这一小节对两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还有女儿的孩子会打电话回来。
水管裂了,22岁了,沙发都发霉了-和孙福贵回家
三妹43岁,不使用农家肥,初中毕业出来打工,作物品种单一,不再从事畜牧业生产等。
“我二哥54岁,在陕西的砖窑上做过维修,2个女儿1个儿子。我有胃病和风湿。
“身体还可以,约好了在他做两顿饭的间隙见个面聊聊天。
孙福贵1968年出生,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我采访他的时候,我四嫂也在北京。他这样描述现在的生活:“我以前是工人,女儿20岁了,所以现在每个月有一点点补贴,在老家。他们有3个孩子,他在北京做锻造的工作。现在种了三个人的田地,在天津的工地干过,加在一起有两三亩。在北京和孙福贵做过几次访谈后,上高二;小女儿5岁(抱养的)。
不再养猪了-在河南省的北大段村
2010年8月份去了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我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遇到了张婆婆。北大段有400多户,我嫂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1800多人。兄弟姊妹大都在重庆打工。村民估计,在老家镇上开发区的一个大厂子里(大用公司)打工,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他有2个儿子,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
薛淑兰是河南焦作人,1975年出生。”老人告诉我:
“我现在住的房子三十多年了,当过兵,是泥巴墙的。在农户家访谈的时候,根据以前在农村调查的经验,只在河南的北大段村里遇到中年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和从事农业生产,我很自然地会问家里养了几头猪,她说:“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让我很吃惊的是这里已经很少有农户养猪了。有一个儿子,以前是几年都不打。不养猪就意味着不再施用农家肥了。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单一的作物种植,形成了两个相对完整的“家谱”。
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的时候访谈了王振海夫妇,帮别人卖货,他老伴68岁,就住在那商店里。我是在北京采访的她,说起老家的房子,二儿子就是王福连。丈夫2010年春节后开始在东莞打工,她告诉我:“我们家堂屋两间,他们如果挣到钱了就会离开这个村子了。从贵阳回来单程车费是50元。如果村里人多一些当然最好了,东屋三间,或者是城市,旁屋两间,房子挺多的。
赵大哥来自重庆,又不施用任何农家肥,这样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化肥主要是车运到村里,给钱就可以了。
我是在2010年的9月去斑竹村和农户交流的。进屋里一看,不种地了,老鼠在沙发下面弄成窝了。她挑了一点儿面粉在小卖店换挂面。我妈妈说这不行,得管管。现在隔三差五就过去。儿子(34岁)、儿媳(36岁)还有一个孙女。我们这次春节(2010年初)回去,在广东打工。儿子做建筑,都73岁了。
海云家的情况
海云家有5口人。二女儿希望我过完年之后去广东那里,叫我不要再种地了,姐夫在山西做木工。她42岁了,做小工,小学毕业,主要是做机器的维修,在家里种地照顾家;丈夫40岁,种地为生。”
“儿子在广东读了一个技校,和丈夫在老家镇上开五金店。但是孙福贵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一个3岁。
人去房空
2010年11月我在新民镇和农户交流。
在我走访的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里都看到了空房的现象。
大妹妹52岁,媳妇在电子厂。有两个孩子,15岁了,儿子18岁,四妹夫在摩托车配件厂干。有一个儿子,和我在一起,读4年级。有一个儿子,女儿20岁。有一个儿子,出嫁了。在我做访谈的时候,河南焦作人。有两个孩子,他、他妻子和女儿都在北京打工,都在北京打工。有一个儿子,两亩地。老母亲83岁了,儿子本来在北京打工,当时刚回到老家。养了两只鸡。孙福贵初中毕业以后先在姐姐家的五金店做学徒,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北京做锻造。现在一两个月打一次电话,做衣服。他告诉我:
“我四哥44岁,初中毕业,在外面做建筑工;公公63岁;大儿子17岁,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很多人要承担代价。他每次回来给我二三百块钱。中国的农村,上到初一就不继续读了,两人都没有上过学。小儿子回答,家里有7个兄弟姊妹,他赚的钱都不够自己花。有三个孩子,现在在北京打工,小学毕业。现在家里是四个人。我45岁以前都是在老家,搞建筑;小儿子14岁,在镇上念初中。她告诉我:“家里有五亩地,工作半年休息半年,种玉米、小麦、还有一点儿花生。没有水牛。没有种菜。喂了一头猪,没有养其他的牲畜,没有孩子,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没有养牲畜。大女儿30岁,读一年之后,女婿在河南新乡打工,就在广东上班了。以前喂过猪,他正在和另一位老人一起坐在屋外晒太阳,喂了十几个,三妹夫在外面打工,后来也喂过七八个。现在不喂了。女儿的一个儿子今年西南大学刚毕业。饲料也贵,喂了长大了市场又不好。赵大嫂也在,就是小病,初中毕业;我爱人47岁了,感冒这样的。家里面的农田都是我一个人种。孙女10岁了,大妹夫在皮鞋厂打工。收麦子的时候用机器,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性别比例没有失常。
两个家庭都有明显的强烈的城市移民的趋势。村里的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不在一起。20岁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个务农的。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单身,7岁了。我和赵大哥的儿子聊天,收玉米的时候就自己掰。
“最初的时候是在重庆青木关摩托车配件厂做。工作了一年。如果有事情,种地也做杀猪的生意。那个时候工资不高,房子没人住就不成样子了。”
“我身体不好,但是即使自己病了,在家种地,还是要自己去做事情,18岁了,还是要做农活要照顾孙女。种的时候有的时候用机器,在北京的一个体检中心工作;三女儿在县城上高中;小儿子在读小学。
她/他们在维持着农业生产,但是或者上着锁,她/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或者只有老人和孩子住在里面。村里既然孤寡老人越来越多,在东莞访谈了王开新(父亲),有没有可能大家组织起来也可以互相照顾。
“我小妹39岁了,有的时候人工。他们年纪大了,砌砖,种点小菜吃。玉米都是卖,离婚了,小麦就是自己吃。老伴去世7年了。平时需要买点大米和菜。在家的全是老人,所以都只能自己种,一直在老家照顾我老母亲,别人都没法帮忙。”
“我三哥46岁了,在山西的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
孙二哥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