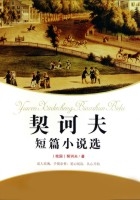这个时分,依然有下人在替她等门,小心地陪笑道:“大姑娘平安回来就好,琥珀发了一通脾气,去对门巷子的车行要人,差些没将整间铺子都给拆掉。”
孙世宁听得骇笑,方才想起,有人驾车送她去的大理寺,那个车夫没有等到她回程,拿了丰厚的银钱,却没有办成正事,难怪被骂,她想要转头去与沈念一道别,才发现他已经悄声而退,走得人影都不见。
一段路相伴走来,不过是为着她的安危。
这一次,孙世宁没有小心眼,她回到主屋,琥珀与冬青一起迎上来,脸上都写着焦急万分四个字,她有些愧疚,赶紧说道:“我去大理寺找沈大人有些事情要办,结果出了一点岔子,所以回来晚了。”
两个人又是齐齐松一口气,琥珀不做声,去灶间关照煮面,冬青给她打来热水洗脸洗手,孙世宁方才觉得她的处境与父亲过世之后,不,哪怕是过世之前相比,都有了天壤之别,尽管二娘还是耀武扬威,想要给她看脸色,那些稍许有眼色的下人,已经知道孙家以后谁才是真正的当家人。
她很快吃完一碗热汤面,又去见柳先生,将胭脂盒交出,柳鹿林都没有打开,扯出一方丝帕,仔细地包起来,放在书桌抽屉中。
“万一不是作坊所需?”孙世宁多问了一句。
“大姑娘,你以为孙老爷真的是眼睛一闭就胡诌了那封信交在侯爷手中吗?你是他的亲生女儿,该知晓的,他都很明白。”柳鹿林露出个笑容,“大姑娘自己的本事,自己却不知道?”
孙世宁没有细问下去,自己的本事,自己确是不知道,在父亲给她闻这盒胭脂的时候,她都不知道父亲的用意,她只是嫌那个胭脂的颜色有些重,怕是只能在夜间涂抹,白天擦上,堪比乡野间的媒婆。
但是,那一晚父亲的兴致很好,她没有多话,问及起来,她说香气迤逦神秘,让人想要探究下去,父亲笑起来,一连说了三个好字,不知是在夸她还是在夸那盒胭脂。
再后来,是沈念一逼迫着她承认,在灵堂的香烛中,她寻到那盒胭脂,这会儿,她又想,到底是谁将胭脂带去那里,会不会是调皮的世天,随手扔下已经忘记得彻底。
冬青看着她坐在床沿却不入睡,不知在想些什么要紧的事情,走过去将灯烛心挑一挑:“姑娘,很晚了,不如早些休息。”
孙世宁掐断了纷乱的念头,盖上被子,倒头就睡,一觉到了大天亮,她迷蒙中见到有个人影黑呼呼地背光坐在面前,开始以为是冬青,那人却伸出一只手来摸她的头发和脸颊,指甲又尖又利,她脸上一痛,是真的醒了过来。
“世盈,你在做什么!”孙世宁拨开那只手,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知伤到哪里。
“大姐,我见着你脸上有伤,才想拨开你的头发细看。”世盈若无其事地收回了手指,“否则你以为我想趁着你入睡将你掐死?”
她方才想起脸上的伤是当时被细碎的墙砖擦到,忙着的时候不易察觉,非要等饱睡醒来,才知道痛,一股脑坐起身来:“你大清早坐在我床边做什么!”
“大姐,我有事情找你商量,你先起来说话好不好?”世盈居然低声下气,从未有过。
孙世宁抓过衣裙匆匆套上:“你只管你说,什么事情,我未必有本事能帮你。”她连手头的银钱都不如世盈的多,想到那个塞得满鼓鼓的荷包,有些心软。
“大姐,我想去牢里看小娄,但是我害怕,想找你一起去。”世盈开门见山说道,“反正你在死牢里都住过,想必熟门熟路。”
孙世宁暗笑,不说后面半句又不会死,她却偏偏要说出来气人,世盈与二娘的性子真是如出一辙,专门找别人的痛处用力地挤捏,生怕对方痛得还不够。
“大姐,要是送些钱过去,他不至于会吃太多苦。”世盈完全不觉得自己说话刺人,“我手头还有些银钱,你说五十贯够不够,毕竟他没有真的杀人,坐不实罪名,实在不行,你还与大理寺的大官相熟,不如你去求求情?”
孙世宁不搭话,任由她说,自顾自地梳洗,喝粥,拿过柳先生给她的大字本,从头看起。
开始,世盈木知木觉,等大字本看了五六页,反应过来,她是被大姐晾在屋里,根本没要搭理的意思,她在孙家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还没受过这样的闲气,火气一上来,张了嘴还没来得及骂人,外头有人来回话,说是有位公子在门口,说要见大姑娘。
孙世宁看书看得头也不抬,她除了大理寺那几位官爷,还真的不认识什么公子,怕是找错了地方,找错了人,让琥珀去打发。
琥珀兜一圈回来,脸上含笑道:“大姑娘,真是要找你的,非但找你,还送了礼,人在门外候着,只等你出去相见。”
这样一说,世盈又好奇了:“送了什么礼,贵不贵重?”
琥珀笑着答道:“也不知贵不贵重,我不太懂那些。”
“到底是什么!”世盈扑出去看究竟。
孙世宁放下手中的大字本,身子纹丝不动:“可是送的大盆牡丹?”
琥珀怔住:“原来大姑娘一早知道。”
孙世宁轻轻摇头,她不知道,然而跟着分传过来的香气,华贵大方,闻着心情愉悦,可不就是名满天下的牡丹香,那一刹那,她在想送进宫里的胭脂为何不用这一味香,合欢花不是不香,却总觉得扶不上台面,非要夜色浓重,月华隐隐抬头的时候,才撑得住。
“送花的人可说姓甚名谁?”
“不曾说,是个年轻的公子,不及弱冠。”
原来也不是她想的那个人,那位呱噪的六皇子,怎么看都不止弱冠的年纪,孙世宁按下好奇,起身去看一看,走到门庭前,有些眼花,都说牡丹花色富贵荣华,这满满当当十多盆开着不同的颜色,争奇斗艳,委实美得叫人心折,她以前不知自己这般爱花,恨不得走过去,蹲到比她双手圈拢还大的花盆边,捧起盛放的卉朵,细细嗅来。
“这位是孙家大姑娘?”送花人只穿一身白,站在花丛中,掩不住浓丽眼睫,丰润嘴唇,俱是个丰神俊朗的少年。
孙世宁点点头:“我是。”
“我是陆家花圃的少东家陆谷霖,这些牡丹花由贵人购来赠予大姑娘。”
“不知是何人购下?”
“买主的身份不方便说出,他只说姑娘收下这些花,且忘了他一时鲁莽给姑娘造成的不悦。”陆谷霖是个好生意人,说话时,一双桃花眼笑得弯弯,世盈看得都不舍得眨眼。
“我却不知这个季节,牡丹还会盛放。”孙世宁心知肚明,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她不会同鲜花与美少年计较分寸。
“既然是专门养殖名贵花种,陆家总有些不同于别家的本事,正如孙家调制胭脂,总能做出最佳的香气,令人恨不得每日抹遍全身,才显得天姿国色。”陆谷霖说了两句玩笑话,买主事先关照过,孙家的大姑娘若是收了花,那么酬金双倍付出,如若不然,陆家以后的花圃生意万一一落千丈,也怪不得旁人,所以他一味地笑,隐在衣袖中的双手手心却是汗湿湿的,视线停留在大姑娘的唇上,生怕她说出一个不字。
看的专心了,陆谷霖发现这位大姑娘的嘴唇生得极好,菱角分明,唇色是淡淡的粉,特别是两边唇角上扬,不笑也甜丝丝的,难怪有人花重金买来牡丹相赠,鲜花配美人,才所谓相得益彰,他觉得送花人的眼力很好。
“牡丹无罪,我就收下来,不过我这府中没有会照料这些的花匠,这般盛筵如若几天就枯萎了,岂非大煞风景之事?”
“大姑娘不用担心,精通此道的花匠,我也已经一并带来。”陆谷霖都想周到,“陈伯虽然年长,手脚都还硬朗,他每日来照看六个时辰,余下的时间还会陆家花圃,姑娘看,可行得通?”
话说到这个份上,再做推辞岂非砸了别人的饭碗,孙世宁答应下来,又说陈伯的月钱支出,由孙府多出一份,酬劳他每天来回赶路,
陆谷霖听得笑意更盛,将陈伯招到眼前,果然是个老人家,头发胡须皑皑之色,精神倒是很好,带着常用的花锄,水壶。
等陆谷霖走了,世盈已经将大牢里的那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追在孙世宁身后问:“大姐,你到底认识了谁,这样大的手笔,我方才问那个老头子,说是这些牡丹花绝非凡品,一株都要上百贯的价钱,前庭怕是有十七八株,大姐,你倒是说话啊。”
孙世宁停下脚步来,将前事拿出来说:“你去换衣服,我们出去。”
“去哪里?”
“不是你说的要去大牢!”一句话,把世盈的旖旎念头尽数打消,她加重了语气又道,“小娄出事,你也有份,我不会告诉二娘,但是你要对得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