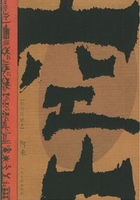每逢礼拜天,我有时候会听见钟声,林肯、阿克顿[451]、贝德福德[452]或者康科德的钟声;在微风的吹送之下,钟声隐约而悦耳,如同大自然的乐曲,真值得在旷野中侧耳倾听。若是传到距离足够远的森林上空,这声音就转换成某种颤动的低鸣,仿佛触目所及的松针都变成被它轻拂而过的琴弦。所有声音传到最远处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宛似宇宙七弦琴的颤音,正如我们眼前的空气会给远方的山脉染上黛青色,让其变得赏心悦目那样。我听到的钟声不啻是空气调和过的乐曲,森林里所有的树叶和松针都曾与其唱和,大自然参与和改造了这声音,并让其在一个又一个溪谷中回荡。这种回声其实多少也算是原声,并且自有其神奇与迷人之处。它重复的不仅仅是那值得重复的钟声,还包括了部分森林的声响;森林女神所吟唱的,也无非就是这种依稀可闻的歌词和曲调。
傍晚时分,远方有些奶牛的哞哞声传入了森林,听上去既美妙又悦耳,起初我还以为是某些流浪歌手在唱歌,那些人常常在高山与低谷间游荡,我曾欣赏过他们的表演;但我很快发现那原来是廉价而自然的奶牛之音,我有点失望,却并没有感到不快。我说那些年轻人的歌声像奶牛的音乐,倒不是意在讽刺,而是想要表达我对他们的欣赏,毕竟这两种声音归根到底都是大自然的曲调。
在夏季的某段时间,每到七点半,夜班的火车已经驶过,夜鹰往往会栖息在我门前的树桩或者屋脊上,吟唱半个小时的夜曲。它们开始歌唱的时间总是在每天日落前后五分钟以内,简直准时得跟钟表差不多。我因而有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去了解它们的习性。有时候我听见四五只夜鹰同时在树林里不同的地方啁啾,听着很像是整齐的大合唱;由于离得特别近,我非但能听清每个音符后面的舌音,往往还能听到那种特殊的嗡嗡声,就像苍蝇掉进蜘蛛网发出来那种,只不过更为响亮。有时候夜鹰会在树林里绕着我兜圈飞,离我只有几英尺,仿佛是被绳子拴住了,大概是因为我离它所下的蛋太近了吧。它们彻夜断断续续地歌唱,在黎明即将来临时,会再次奏响动听的乐曲。
当其他飞鸟安静下来时,鸣角鸮[453]接续了歌声,像家里死了人的妇女般,发出了亘古的“呜噜噜”的啼叫。它们的悲鸣真是本·琼森式[454]的。这些聪明的午夜女巫!它听起来完全不像诗人形容的那种“突喂、突呼”的叫声[455],而是——不开玩笑地说——最沉重的墓园之歌,是自杀的恋人在冥界森林回忆起生前相爱的种种苦痛与欢愉时的相互安慰。然而我爱听它们哀怨的鸣叫和凄恻的回应,这在树林间回荡的声音有时候会让我想起音乐和鸣禽;我总觉得这听起来像是阴郁而催人泪下的音乐,是充满悔恨与叹息的悲歌。它们是情绪低落、心境忧郁的孤魂野鬼,前生也曾是人类,可惜在夜里横行无忌,做过许多坏事,如今只能在当初为非作歹的场地上唱着哀怨的歌曲,以此来进行赎罪。它们让我对大自然——也就是我们共同的寄居地——的多变和广袤有了新的认识。“悔只悔当初、初、初!”有只鸣角鸮在湖这边叹息着,旋即在无尽的绝望中飞起,最终栖息在灰色橡树的枝桠上。然后,湖那边另外一只鸣角鸮极其真诚地呼应着:“悔只悔当初、初、初!”而远处林肯镇的森林传来了微弱的回声。
我也有幸聆听过雕鸮[456]的呼号。如果从近处听,你会觉得它是大自然里最忧伤的声音,自然女神似乎想要把这种声音作为人类垂死呻吟的模板,并让其永久地保留在她的合唱团里。这些雕鸮仿佛绝望的游魂,正要走进阴曹地府,像野兽般吼叫着,而又混杂着人类的抽泣声,那“咯咯”怪叫竟似有幸灾乐祸的意味,听起来更加让人觉得恐怖——我发现写到“咯咯”时,我自己居然情不自禁地模仿起雕鸮的叫声。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说明它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黏稠发霉的状态,所有健康和勇敢的想法都已被消灭干净。它让我想起了食尸鬼、白痴和疯子的嚎叫。但现在,有只雕鸮的呼应声从森林远处传来,距离的遥远让它变得真的很悦耳,“嚯……嚯……嚯……呼嚯……嚯……”,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声音只会让人产生愉快的联想,无论你听到的时间是白天还是黑夜,夏季或者冬日。
有雕鸮我是很高兴的。就让它们替人类发出愚蠢与疯狂的嚎叫吧。这些声音与日光照耀不到的沼泽和阴暗森林极其相称,揭示了自然界还有大片人类尚未认识的、未经开发的地方。它们象征着绝对的阴晦和每个人都有的得不到满足的想法。白天时,太阳照耀着某处荒凉沼泽的表面,伫立其间的黑云杉[457]挂满了须松萝[458],几只个头很小的苍鹰在上空翱翔,山雀[459]在常绿的树木上婉转啼唤,榛鸡和野兔则在地上漫步;但如今一段更为忧伤和与之相称的时光来临了,一些迥然有别的动物甦醒过来,开始表达大自然在那个地方的意义。
夜深时分,我听见远处传来车辆过桥的轰隆声(这几乎是夜里听到最遥远的声音)和狗的吠声,偶尔还能再次听见某只不安分的奶牛在远方的院子里发出的哞哞声。与此同时,岸边响起了牛蛙的号角,这些古代酒徒与歌者的阴魂,依然毫无悔改之意,来到这个斯提克斯式的湖泊[460],还想要高歌一曲(但愿瓦尔登湖的仙女原谅我这么比喻,因为这里虽然没有芦苇,却有许多青蛙),它们很乐意继续遵守古代宴席那些喧闹的礼节,只不过嗓音已经变得沙哑而沉重,与欢乐格格不入,原来的美酒也已经失去香气,变成了只会让它们的腹部鼓胀的劣酒,酩酊的醉意非但淹没不了往日的记忆,反倒让它们感到肚子里装满了苦水。领头的青蛙体态最为臃肿,它的下巴压着一片荇菜[461]的心形叶子,那叶子像餐巾般托住它垂涎欲滴的嘴巴;它在瓦尔登湖的北岸猛然喝了一口从前嫌弃的水,再把酒杯传出去,同时说着“干杯啊,干杯啊!”远处某处浅湾随即传来了这句口令的回声,原来是有只官阶较高的胖青蛙听从前者的吩咐喝了一大口;酒令巡湖一圈之后,主持这次宴席的青蛙满意地说:“干杯啊!”于是所有的青蛙依次都喝了,就连身形最瘦小、肚子最干瘪、职位最低微的青蛙也不例外;然后它们一轮又一轮地喝着,直到太阳驱散了晨雾,只剩下最老那只青蛙还没潜到水底,有气无力地反复喊着“干杯啊”,喊完了还要停下来等待回应。
我想不起来在我住的地方是否曾经听到过鸡啼,我觉得养只小公鸡,就当它是鸣禽,听听它的音乐,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公鸡就是原来的印第安野鸡,它们的音符肯定比其他任何鸟类都要独特;假如它们虽然遭到蓄养,却没有被圈在院子里,那么它们的啼叫很快就会变成森林里最著名的声音,超过大雁的叫唤和猫头鹰的哀嚎;就算公鸡休息了,还有母鸡会咯咯叫个不停呢!怪不得人们要将这种鸟驯养为家禽——何况它们还能向人提供鸡蛋和鸡腿!若是在冬日的早晨走进树林,看到许多家鸡在它们的故乡漫步,听见野公鸡在树上啼唤,那声音清越而嘹亮,几英里之外都清晰可闻,完全盖住了其他飞鸟孱弱的啁啾——想想就觉得很美妙!这声音能让许多国家警醒。要是终其一生都能及早起床,人们怎么可能不变得难以言喻地健康、富裕和聪明呢?[462]全世界的诗人在赞扬了本国鸣禽的曲调之余,也都称颂这种外来鸟类的音符。雄鸡能够适应各地的气候。它的适应性甚至胜过许多本地的飞鸟。它的身体总是很结实,它的肺总是很健康,它的精神从不沮丧。就连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手也被它的啼唤弄醒,但在木屋生活时,我从未在它尖厉的声音中起床。我不养狗、猫、牛和猪,不养母鸡,所以你可以说我这里缺乏居家的声音;我这里也没有搅拌奶油的声音、纺车的声音,甚至没有锅碗瓢盆的叮当声,没有水烧开的嘶嘶声,就连孩子的哭喊声也没有。老派的人会认为这种生活没有意义,或者觉得无聊到死。墙里也没有老鼠,因为它们被饿走了,又或者压根就未曾钻进去。我这里只有屋顶上或者地板下的松树,屋脊上的夜鹰,在窗下欢唱的冠蓝鸦[463],木屋底下的野兔或者土拨鼠,屋后的鸣角鸮或者雕鸮,湖里的一群大雁或者一只欢笑的潜鸟,还有在夜间叫唤的狐狸。像百灵和黄鹂这些常在种植园出没的温驯鸟类,从来不曾出现在我的林地。院子里没有公鸡打鸣或者母鸡乱叫。甚至连院子都没有!只有未曾被篱笆隔开的大自然爬上你的每个窗台。几株幼苗在你的窗下成长,漆树和黑莓的藤蔓钻入你的地窖,粗壮的刚松[464]紧紧挤着小木屋,想要争取更多的生长空间,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入木屋下的泥土。如果要烧火,你不用费心去拿煤斗或者那块被大风吹掉的窗板,只要到屋后折断松枝,或者干脆将其连根拔起即可。纷飞的大雪不会盖住通往前院大门的小径,因为根本就没有大门,没有前院,也没有通往文明世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