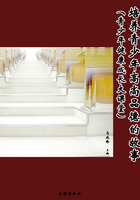1976年的初春,“农业学大寨”见了效。我们大队把一条河齐腰拦了,用炸药、雷管、鸡公车、背篼、黄土垒了一条大堰,修成了一条水电站。冬天水干,用电高峰,就见电灯红初初的,像猴子的屁股,照得人眼睛麻酥酥的。
队长说:“毛主席他就是英明,他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就是纸老虎了,不费吹灰之力美帝国主义被我们赶了出去。”队长说话的时候已是黄昏,我们社员正坐在大队院坝里算工分。
南河大队看见我们大队修电站,他们就办了一个红心石材加工厂。我在山脚脚下,就能目睹到他们热火朝天的场面。半山腰开山采石,轰隆隆的开山炮声,腾起的阵阵浓烟,垮塌的岩石,顺着岩槽滚下山脚的石场。石场上一派繁忙。
山脚下通往山外的公路上,满载着大理石的拖拉机、板板车把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挤得水泄不通。
我骟割仔猪的这户人家,就在南河红心石材厂山脚下的公路边上。九头仔猪,五公四母,按我精湛娴熟的骟割技巧,应该是要不了半小时就完成了,但这次却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五头公仔猪中遇到了一头“阴阳猪”,这种仔猪的比例大约是千分之一,平时是很难碰上的。也就是睾丸没长在阴囊内,而是长在腹腔里。要摘除这种仔猪的睾丸很费事,得剖腹寻找那一对隐藏在腹腔中的睾丸,摘除也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会大出血造成仔猪死亡。还好,虽然我额头出了汗,这头仔猪在被骟割到最后缝合都没出血。我的耳边一直响着堂兄那高亢激昂的牛角声。我一点没有紧张。
这家主人见我骟割他的这头“阴阳猪”费神吃力了,等我停当时便立即递上烟茶来。然后他说,等到这窝猪仔卖了后,还请你把这头老母猪给骟了。
我不明白地问他,骟了它干啥?它给你下猪仔,就是在给你下票子啊!
主人说,卖猪仔那些钱,怎么能跟别人比啊。别人得的是金砖,我这只能称为雪花银。我也打算上山开山卖石材,那才是大把大把的金子。
南河大队山上山下一片嘈杂,已没有了从前的那份宁静,那如诗如画般的宁静山村已经远去。
我正爬上半山腰时,就遇见南河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书记阳长春和大队长阳吉木在其他几位社员的帮忙下,拖着三棵连根的松树往山下滑。
原来,这是生长在山头上距古刹宝莲寺约2000米处的石人山旁的三棵美人松。在这崇山峻岭中,这三棵美人松,特别出众,亭亭玉立,宛如三位玉女在崖畔迎风守候。我还知道这三棵美人松的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南河大队的半山上一户人家有两位如花的姐妹,同时爱上了一位如意郎君,两姐妹不愿意互相伤害,但又无法割舍爱情,便分投石人山旁的悬崖殉情而去。姐妹同时爱上的那名男子,得知姐妹因他而殉情的事后,他也在姐妹二人投崖的地方舍身而去。后来,在他们三人殉情的地方便长出了这三棵美人松。
我回到东河大队,左邻右舍的乡亲都闹起来了,说东河大队山脚下的殷世全患了一种怪病,不得了,要死人了。起初感觉阴茎麻木、疼痛,继而感觉阴茎变小并渐渐内缩,肚子里好像有一股冷气在乱窜。听老人们说这叫走阳,得的是一种叫“缩阴症”的怪病。病人发气短促,直冒冷汗,且浑身发抖。病魔来势凶猛,像真的是要殷世全的命。
夜里,我梦见在一片草长莺飞的山坡上骟割一头凶猛的黄牛。黄牛被一位我似曾熟识的美丽的少妇牵着,这次没像平时那样将黄牛捆绑倒地,而是让黄牛站着,我就在牛屁股后面开始骟割摘除两只硕大的睾丸了。
少妇在那里牵着牛鼻绳嬉笑,她的笑容明显地让我感觉到有浓重的羞涩和挑逗。我身体的敏感部位有些鼓胀和涌动,像春天里顶破土层直往上蹿的竹笋。
被我骟割的黄牛睾丸更是让我根本无法收拾,刚刚摘除一对热乎乎的睾丸时,立马又长出一对睾丸来。我不断地摘除,睾丸不断地迅速生长出来。
黄牛没有丁点的痛苦,它的那种舒坦和从容,反而让我痛苦起来。
这时候,少妇干脆丢掉了牛绳,来到了我的身旁。她挑逗的目光钻进我的身体,我左手握住刚生长出的一对睾丸,右手中的青铜弯月刀像绸缎般柔软无力,更像绸缎般的是少妇的一对乳房在我的后背肌肤上滑来滑去,我浑身血液涌动,敏感的部位再次像要顶破土层的春笋聚力勃发。
我不顾一切地丢掉堂兄传给我的青铜弯月刀,转身与少妇相拥时,黄牛奔跑了,渐渐地,没有了黄牛的身影,在我模糊的视线里,前方只有一对硕大的睾丸在奔跑。
白天,我一直被夜里的这个梦困扰着。
我心里老想不再干这骟匠的活儿了。
看着山背后南河大队山山水水被人糟蹋得不成模样了,老中医说南河大队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心里总不是滋味,南河毁林砍树,开山采石,破坏山水大地,老医生阳生云说过的话,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自然界是神奇的,哪里该生长多少棵树,该生长什么样的树,哪里该生长多少矿,该生长什么样的矿,都是有道理的。如果破坏了它,自然界就会报复的。”
那么,我骟割摘除了牲畜身体上繁殖后代的部件,不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破坏吗?想到这里时,那些曾经被我骟割的猪、牛、马、羊、鸡、狗、免们的仇视目光像利剑般射向我,我顿时被万箭穿心。我在想,如果我这样骟割下去,会不会遭到报复呢?
在“过三两关”的特殊时候,母亲为了救我的命,曾多次冒着被革命的风险。一次,集体劳动种洋芋,一个洋芋种子被切成三块或四块丢在泥土中,然后浇上大粪。母亲就偷偷地从浇上大粪的土坑里,捡起一块洋芋揣进怀里的布兜里,拿回家救我们兄弟的命。可就在母亲要把洋芋揣进怀里的时候,她被人发现了。在大队的院坝里,母亲站在大坝的台子上,台子下面是黑麻麻一片群众。有人揭发说母亲偷了生产队浇了大粪的洋芋种块,这是破坏集体生产,是破坏社会主义,是存心不让社会主义的地里长出社会主义的苗来……
母亲无言以对。我正从大队小学放学回到坝子里,就看见母亲紧咬牙关,人群中的吼叫掀起一股股凛冽的寒风,寒风中是飘摇的母亲,母亲站在台子上像风中一盏飘摇的油灯。
更有恶作剧。一个人抓了一把青草要母亲含在嘴里。那人一边往母亲嘴里塞,一边说,你不说话,你不开腔,你就吃草吧!
开始我的心一阵阵地疼,后来我记起了老师的一句话,你把母亲比着牛就比着牛吧!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呢!牛是伟大的,母亲更是伟大的!我在心里狠狠地说。
许多年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人人尊敬和爱戴的骟匠。每当我去给曾经往我母亲嘴里塞青草的那家人骟割猪、牛时,我觉得割掉的似乎不是牲畜的生殖器,而是人的生殖器,我用力之狠,牙齿咬得格巴巴响,心里在说,你断子绝孙,你断子绝孙!
一次,我给那家人骟一匹公马,那匹公马不但成天追赶着母马,还追赶母羊母牛和母驴寻欢作乐,让所有畜生们不得安宁。我心底涌动着一种无名的仇恨,青铜弯月刀割开绳索捆绑的公马皮囊,公马疼痛地颤抖,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愉悦和舒坦。
公马的主人拿出钱来,我直截了当地说,钱我不要,银钱如粪土,仁义才值千金。作个人情吧,你如果有旧时的瓷盆、瓷盘、瓶瓶罐罐什么的,我们倒可以做个交易,你们都知道我喜欢上了古玩。
公马的主人倒很真诚,他说,殷师傅,我家的确没有盆啦盘的,说实话,你给我骟割了公马,给我们消除了祸害,只要有的我都会毫不吝啬地拿给你。说实话,前辈只给我们留下了七枚银圆,你喜欢的话,就全部送给你。
我心里日思夜想的本来是而今早已失散的另一个乾隆锦地开光描金山水人物盆,但瓷盆没在他家,有银圆我也会收下。我说,拿出来我看看,是真是假还不好说。
公马的主人说,千真万确,是解放前家传下来的,不会有假。
我说,你懂个啥,并不是解放前传下来的都是真品,银圆这东西在当时流通时就有很多造假,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地的军阀都私造银圆,因而大量的假银圆在银圆流通时就混入市面而被传下来了。
公马的主人拿出了陈封的七枚银圆,我一一过目后,认定其中的一枚三鸟帆船、一枚大尾龙大清银币、一枚四川银币和一枚“袁大头”实属真品,再听声音和看颜色、包浆等,都与我目测相符,最后用秤测重量,这四枚都是26.8克,其余三枚均在24克以下,且声音颜色都属赝品。
公马的主人问我,都是真的吗?
都是真品,七枚全是真品。我说。
那你都收下吧!公马的主人对我说。
我将四枚真品收下,装进了我的棉布褡裢里,然后对公马的主人说,是你的家传,我怎么好意思全拿,拿四枚已算我心狠了,这三枚你留下吧,继续家传,好有个维系。
我执意不肯全部拿走,公马的主人只好依了我,看得出他还是一脸的诚意。
我回想着南河村的往昔和今时的瓜葛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