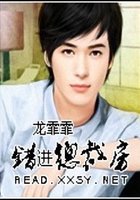子矜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昏昏沉沉的看着安王离开,然后又是怎样脚步虚浮的回到房间,忐忑不安的度过了一天,到了夜幕降临时,子矜看着窗外缓缓升起的皎月,又想起了母亲在人前卖笑的脸。
她是母亲活在世上的唯一支柱,若是她有个三长两短,母亲该怎么办呢?
子矜拔下髻上那支银簪放在手中看着它呆了许久,蓦然抬头看向镜中乌发散落的女子,看到的是苍白的脸颊和慌乱的眼神。
她不能告诉他月美人的事,有道是捉奸在床,她空口无凭的说出来,再加上她并不知道那男子是谁,这样便是明显的栽赃。
若是月美人再趁机告上她一状,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出府的那一天。
影子中的面容更加苍白,子矜动了动唇,呐呐的发不出声音。
尖尖的簪尖,戳破了吹弹可破的肌肤,鲜红血滴慢慢渗出来,在那白皙肌肤上分外妖娆妩媚。
她用手抚上光洁如玉的脸颊,看着镜中,叹了口气,实在万不得已,就拿着簪子毁了它,一个已经毁了容的女子,想必他不会再难为她吧,又或许他会好心的放她出府呢。
吸了口气,起身梳了发髻,将那簪子插进发中,换了侍寝穿的衣服,静静地坐在房中等着王总管领着人来接她。
她吹了灯,屋内一片昏暗。
她不由想起小时候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时候她还很小,记得事情并不多,她只记得她们母女二人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屋子里,有时候那个擦着满脸粉脂的老鸨就会来找母亲,母亲总是把她关在屋子里,然后将门带上,外面母亲和老鸨的声音低低的听不清,可是她知道,每次出去前母亲就会在她的首饰匣子里拿件东西,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
开始的时候,她会抬起小脸天真地问,母亲你拿那个做什么。
母亲会温柔的笑着对她说,它能让我们安静的生活一会子。
等她长大一点,知道什么是接客,什么事妓女,什么是青楼的时候,她便不再问了,她依然看着母亲在首饰匣子里拿东西,直到那里面变得空空如也。
她一直知道的,老鸨总是来劝母亲接客,母亲拿她手头的积蓄换来了几年的平静日子,再多的积蓄也会有尽头,当看到匣子空了的时候,母亲抱着假装睡着的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门外传来脚步声,缓慢的小步子,一声声击在心口上,跳得厉害,子矜不免有些忐忑,紧紧地抓住身下的床单,几乎将那床单撕裂。
门开了,看到的是王管家熟悉的老脸。
“丫头。”他笑起来。
子矜怔怔的起身,缓缓地朝门口走去,一脚刚跨出门槛就被王总管拦住,不由诧异的看他。
“丫头,今天王爷有事进了宫,说是不用侍寝了。”王总管笑吟吟的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瓷瓶,炫耀的在她面前晃了晃:“王爷听说你脚腕上受了伤特意赐给你上好的金疮药,听说还是大内特制的,一般的人还用不到……哎,丫头你怎么了……”
王总管絮絮叨叨的说着,却见子矜的身体失了力气般瘫倒下来,急忙扶住她……
当日,子矜发起了高烧,大病一场,安王忙着处理政务忙得焦头烂额,却也把子矜的事隔在了后头,时间久了倒忘得一干二净,王总管向安王禀报的时候,安王也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总管给她请了大夫看了病,又劝着月美人给她安排了个小丫头照顾,只是子矜怎么也不肯让那大夫看她身上的伤,只让他开了治风寒的方子,自己偷偷敷了安王赐的药,这病才断断续续的好了。
这件事总算过去,安王也没再叫她侍寝,月美人忙着准备中秋的节目也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整她,子矜难得的平静了一阵子。
月美人派给她的小丫头不过十三四岁,长着一双大眼睛,柳叶眉弯弯,很是可爱,只不过太过懦弱,看谁也是怯怯的,子矜自己就不是主子,也没有拿她当丫头的想法,伤好了以后两人一起做些零碎活,相处得也算融洽。
那丫头叫小梅,别看她胆小,平常知道的事情倒是多,有时候说些乱七八糟的趣闻,把子矜逗的直笑。
“子矜姐姐,你不知道,自从那天你从戏园遇到王爷,第二天府里的侍妾们都偷偷摸摸的去了,听说还有几个丫鬟也去了呢!结果有几个还真碰上王爷了,都以为她们晚上能得宠幸,结果被王爷狠狠的教训了一番,有一个还被王爷赶出了府,当天,那院子就被封了,为这事,王总管还挨了训。”小梅在她耳旁小声说着,还时不时看看周围,一副怕别人听到的样子。
闻言子矜微微皱了皱眉,迟疑开口:“赶出了府?”将头上散落下来的几缕发丝别在耳后,淡淡开口:“为什么?”
“听说是惹王爷不高兴了,发了火。”小梅歪了歪头,认真地说着。
子矜不由怔住,惹怒他?这个方法管用么?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好像都不怎么高兴吧,耳畔似乎又响起他“不惜毁掉”那番言论来,那算是生气么,可是他为什么没把她赶出府呢?
难道是气他不够?
子矜暗暗想着,眉头蹙成了一团。没有留意小梅看她的眼神从神秘兮兮变成了怯怯的。
“怎么了?”子矜不由纳闷看她。
小梅没有说话,小心翼翼的瞄了一眼她的身后,害怕得低下了头。
子矜一愣,急忙回身看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