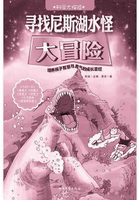凌厉的目光仿佛一道闪电倏的穿过浓浓夜色直直的打了过来。
子矜的身体微微有些僵直,手不由自主地抚上小腹,指尖碰触到柔软的布料,浓郁的复杂情感随着指尖漫进心房,莫名的苦涩。
山风吹得冷冽,宽松的衣裙被飘飞得张扬。
这时,不知从哪里跃出几个黑衣人,将子矜四人团团围住,刀光剑影的与红奴和紫奴战在一起,本来要冲上来的官兵以为是贼人窝里乱,纷纷止住了脚步,站在一旁观望。
紫奴和红奴紧紧地将子矜柳师师护在里侧,无奈黑衣人下手狠戾决绝,大多一刀致命,绕是二人武功再高也不敢硬拼,只死死将子矜她们护在中央,只守不攻,这样便渐渐落了下风,时辰长了,再加上黑衣人数量比二人远远多许多,体力不支,二人身上也不免挂了彩。
子矜被围在中间,见此情景,心中大急,这些黑衣人出招狠戾,若是落到他们手里,只怕几人顷刻间就能没了性命。
透过攒动的人影,她看到站在远处一个个观望的官兵们,拳头不由紧紧握起。
冷殇,你到底有多恨我呢?
风中渐渐涌起血腥味道,指甲陷进皮肉,痛得没有知觉。
她望着那些官兵,冷声喝道:“大胆,吾乃安王爷故交,还不快过来援救!”
清晰的字句随着冷风散步开来,黑衣人却加快了动作,紫奴一个没留神,臂上挨了一刀,吃痛,惊呼一声,扬臂反击,鲜红的血色顺着紫色的纱衣流下来,强烈的腥味在衣衫间散步,子矜感到胸腔传来一阵浓重的呕意,咬牙忍住,手心却已经渗出汗来。
官兵们听子矜这样说,未免将信将疑,队伍里的秩序微微散乱,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帮忙。
是啊,安王爷的故交怎会和他们眼中的贼子混在一起呢,若是就错了人,有谁能当得起这个责任?
紫奴和红奴渐渐支持不住,子矜听到她胸口跳得飞快,隐隐的额前已经渗下汗来,身体与极不舒服,柳师师急忙从身后扶住她,她咬了咬牙,又喝道:“狗奴才,吾等若是出了事,你们负得起责任么?”
话一落地,官兵人群里又是一阵骚动,的确,若是她们真是王爷故交,他们见死不救,上面追究下来,他们一样无法负责。似乎都想到这点,有几个不由上前迈了几步。
黑衣人步步逼近,紫奴胳膊受了伤,护不周全,被黑衣人钻了空子,待回过神来,已见那黑衣人的剑对着子矜直直的刺了过去。
子矜也是一惊,这才明白这些黑衣人都是冲着她来的,刹那间脑中闪过数张脸庞,似乎又回到猎场上那一幕,雪白的衫子和鲜红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胸腔肿胀,却已经躲闪不及。
冥冥中,耳旁传来几声叫喊声,只觉得遥远。
“矜儿!”也许是做母亲的本能,柳师师反射性的护在子矜胸前,那剑狠狠地刺入,利器和肉体摩擦的声音传进耳畔,魔音般的头皮一阵发麻。
疼痛却不是从柳师师身上传来,那剑深深刺进紫奴肩上,殷红的血色顺剑流出,滴滴洒落,紫奴的脸色白如纸。
“受死吧。”
紫奴杏目圆睁,银牙一咬,举见刺向那黑衣人腹部,黑衣人躲闪不及,情急之下撒了手中的剑,剑刃刺空,紫奴却失了力气躺倒在柳师师怀中。
“紫奴,你怎样?”柳师师急忙抱住她,低声询问,紫奴虚弱的挣扎起来,咬着牙道:“副尊主,将奴婢身上的剑拔下来!”
“这……”柳师师看了看她肩头血流如注的剑,微微迟疑。
“娘,拔剑!”
子矜咬着牙冷冷盯着有攻上来的黑衣人,面无表情的开口,现在只剩红奴一人在低挡,若是那些官兵在不出手,四人只怕要命丧于此。
柳师师不再迟疑,单手握剑猛地拔出剑,带着浓重血色的剑在夜色中发出残忍而邪佞的光,紫奴以剑做指,指向攻上来的黑衣人,怒道:“来啊!”
子矜不由侧目看她,伸手握了柳师师的手,淡笑着呼唤:“娘……”
柳师师手上还沾有粘稠血液,她自然明白子矜心中所想,也握紧了她的手,二人并排与紫奴红奴站在一起,嘴角含笑,笑得淡然。
风依然吹着,重重包围中,四个女子依风而立,娟衣素手,美的惊心动魄。
这种时候,母女俩能死在一起,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刀剑无情,黑衣人依然在不懈的攻着,紫奴和红奴战斗力大不如方才,带着杀意的刀刃几次经过子矜颈旁,鲜红血液顺着颈流下来,四人围成的圈子却被他们逼得越来越小。
这时,一只响箭划破长空,凌厉杀来,一剑刺入正要偷袭子矜的那个黑衣人胸口,那人直直倒下,一箭毙命。箭翎随风飘动,尽头,刻着一个苍劲有力的字“安”。
为首的黑衣人大惊,放眼望去,不远处大队人马朝这个方向行来,心道不好,急忙大喝:“撤!”话一落地,黑衣人们互看几眼,飞身撤去。
官兵们这才回神,急忙去追,却哪里还有他们的踪影。
远处,一个白色身影在重将拥簇下缓步行来,面容冷峻,气宇轩昂。
他将手中的弓交至手下手中,在离四人几步处停下,却不看四人,略微偏头,看向站在一旁停滞不前的官兵们。
那些官兵大多信了子矜的话,有些心虚的急急下拜,众人齐喝:“见过安王爷。”
安王面无表情,并不说话,却也没有叫众人起来。
他身后的将领也只恭敬的站着,气氛冷冽沉闷。
为首的官兵不由冷汗涔涔,咬了咬牙拱手请罪:“属下不知是王爷故交,保护不周,还请王爷赎罪。”
“故交?”
安王波澜不惊的脸上这才有了些许波动,他玩味的念着这个词,唇边冷酷而讽刺,他看了一旁的子矜一眼,淡淡道:“起来吧。”
几人见他不怪罪,庆幸的同时也有些摸不到头脑,战战兢兢的起身,却见安王嘴角嗪笑,哑着嗓子冷声道:“这些都是叛乱贼子,本王与她们能有何干,这次尚且饶你,以后若再敢胡言乱语,可不会这么轻易绕了你们。”
为首的听他声音透着些许杀意,脊背不由渗出些许冷汗来,连忙拱手僵硬答道:“是属下胡言乱语,谢王爷不责罚之恩,属下还在想王爷身份高贵,与这些草莽女子能有什么干系……”
安王听得不耐烦,抬手打断他,他这才缩了缩脖子噤了声,安王冷冷扫了四人一眼,越过子矜面容微不可查的勾了勾嘴角。
“带走!”
他抛下这句转身就走,身后的官兵纷纷围住四人,红紫二人警惕的拔剑,却见安王突然停下脚步,头都未曾回,冷声道:“你们尊主在本王手中,最好乖乖束手就擒,伤及无辜可不要怪本王没提醒你们!”
子矜闻言猛地一惊,思及昙临走前的笑容透着浓浓不舍,不由暗骂自己笨,这时一旁的红奴脱口而出:“你撒谎,尊主既然在你手中,你为何还会为难我们,你们分明言而无信。”
子矜闻言不由冷了脸,看向红奴问道:“怎么回事?”
红奴自知失言,见她面带愠色,不便再瞒,便将事情原委大概说了,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尊主说得对,官府的人说话不算数,尊主都去自首了,他们却还在捕杀我们的弟兄。”
紫奴脸色苍白,却还是忍不住制止红奴说下去,子矜却感到全身上下一股凉意,她直直盯住安王背影,嘴唇蠕动,竟不知说什么。
许是注意到背后目光,安王这才回头,迎上子矜投来的质问目光,嘴角微勾,幽深的眼眸寒冷的不带一丝温度。
他曾说过什么呢,他曾说,她带给他的痛,要叫她加倍的偿还,当他看到猎场上她被那黑衣人拉着离开,当他看到她为了烈王留下,当他看到她安稳的坐到烈王的马上,他就不只一次的告诫自己,让她尝到痛苦的滋味,告诉她,他曾有多痛。
现在,她定是痛的吧,呵,烈王被他关进了大牢,连昙也被他抓获,两个对她关心备至的男人都并不好过啊。
她雪白的颈上血迹斑斑,在夜色中红的诡异,清澈的眼眸中有不解,有愤怒,还有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只想问:
子矜,你可痛么?
到底是你的脖颈痛,还是你的心痛呢?
风吹起白袍,铮铮作响,卷着圈逡巡而去,消失远方,他的问题,没有答案。
子矜咬着唇看他,胸中澎湃,却不敢泄漏半分,半晌才镇定开口:“王爷定是答应昙的要求了吧。”
安王却看也不看她一眼,冷冷一笑,转身大步离开,身后的将领尾随而至,他的身影在暗夜中依然耀眼孤寂。
众多官兵围上来,缴了紫奴和红奴手上的剑,对着子矜冷笑道:“姑娘,攀高枝可不是这么攀的,你也得看看攀得是谁,王爷的故交,你以为你是郡主呢。”说着拽了子矜的胳膊粗鲁的推她,“你他妈的还不走。”
红奴哪里受的了这种气,见状不由狠狠地将那官兵推开,修眉倒竖,怒道:“你胆子不小,姑奶奶也敢欺负!”说着对那官兵张口就骂,那官兵也不示弱,扯着嗓子和红奴吵起来。
子矜没注意身旁诺大的动静,见安王的背影越走越远,不由又急又气,冲开那些官兵,提着裙裾追上去,见依然靠不到跟前,恨恨的大声叫道:“冷殇,你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