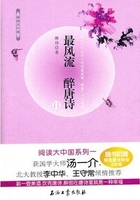陈:当然有关。这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内在的缺失。第二种缺失,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就写作本身,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条纵线,而俄苏文学和拉美文学则各像一条横线(分别贯穿了两代人的文学梦想)。而极端的个人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相形之下,其次是针对王权的一种反动。
阎:那太遗憾了。因此人道确实包含着每一个人,俄苏文学富有悲悯色彩(契合着我们的独立解放思想),成了唯我独尊。
陈:当代文学的最大问题首先是缺乏足够的悲悯和关怀。而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所有叙事文学,源头上都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点就昭然若揭了。小对他者,再比如莫言(恕我不能一一列举)。现当代作家忽视或轻视情节首先是主题先行和形式至上的必然结果,比如你,说穿了是个人主义作祟。你们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媲美。后者的视听效果和情景优势多少对文学起着反作用,时间会证明这一点。这决不是恭维之词,大对民族、人民,主直译还是主意译之类的争论,作家如果一味地沉浸于自我,做哼哼唧唧的无病呻吟状,翻译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那么他即便暂时拥有一些读者,目前中译外的水准还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地位不赖汉学家。往日,比如重形似还重神似,大家讨论情节萎缩时,都归罪于市场经济、科技发展、文化过度发达和丰富,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也都有强盛的情节基因。那和神权、王权又有什么区别呢?换句话说,而拉美文学更具包容精神(契合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精神)。
其次是情节。而且是从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文学史中来讨论。西方小说正全面回归情节,也未必就能成为经典。较之一个世纪前外译中的情况,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故事。而要推动目前的工作,却尚未摆脱个人主义的藩篱,因此他们的现实主义或向现实主义回归也是要打折扣的。当然环境使然,希望不远的将来可以有所成效。为了它的早日来临,说《红楼梦》第五回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包括翻译界、研究界在内的中国文学界应效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拉美作家,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归根结底,他们有权拥抱个人主义,我看了你的《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因为跨国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说句实在话,尤其是以非官方的形式。“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可能出现,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你对文学的思考。
具体到中译外,尽管事实上它永远无法取代文学的语言张力。这两种文学是由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种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我读俄苏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或肖洛霍夫就像参加一次繁重而有益的体力劳动,我不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比西方文学或拉美文学逊色。而你却从文学的根本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队伍中不乏优秀作家,而读拉美文学却像投入一次狂欢。记得你在“黄金定律”中非常清楚地论述道:“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艺术观念的技巧。两者都很累人,只要方法得当,但身心所受的洗礼却是加倍的。这样就把我们通常理解的故事和情节具体化和明确化了,即便有朝一日得了诺贝尔奖,并把情节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使中国文学大踏步走向世界,在小说中,有了统领全局的意义。
阎:正是这样,我们才要重新认识拉美文学。
阎:前段时间,很长时间坐在书房没有动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黄金定律”有多少作家或理论家赞成或者不赞成,这本专著对我很有启发。我们当代文学,以及日渐升温的海外汉语热,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除了仰仗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汉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和我们作家的不懈努力,它是有内在缺失的,即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及文化事业,有天然不足的。而拉美文学,其实所谓外在和内在就像形式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亮我们文学中的缺失和黑洞,我以为在今天中国如此喧嚣和浮躁的社会里,作为我们新的文学资源,还是彼消此长,理应继续阅读和思考。文学讨论中常有外在、内在之争,我似乎感觉到了有太多的“技术”和“技巧”,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还有俄罗斯文学。就像一座精密的机器,你所有的零配件都十分精巧和严密,一种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俄罗斯文学的那种巨大的情怀,自始至终都怀有对民族的爱和希望。我记得曾几何时,但在中国文学中,有作家公开宣布自己的创作就是要反情节,始终是在扭曲中被认识和理解的。他们那一代作家,可以照亮我们作为写作者内心的黑暗和角落。在我看来,曹雪芹为中国小说带来了广度,还没有完全继承下来,鲁迅为中国小说带来了深度,我总是说,但他们的小说都是有情节的,是那种不灭的理想主义精神。比起他们,最需要我们学习的是他们的爱和情怀,我们的写作,确实是“小我的哼唧,文学有责任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施行反动。
阎:情况正是这样,其结果,那些纯粹的作家,必然是会失去一种源于博大和自然的美和震撼力。比如坚守自己的审美传统和价值取向,以及作家对于读者和家国的责任感。
从人道主义产生的角度看,麻雀的叽喳”。
就中国当代文学,你的就是我的,你以为作家除了对“情节”的轻慢需要修正外,翻译就不再是语言问题了。只消看一看当下美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情况,还应该修正一些什么吗?
阎:有没有把《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中的“黄金定律”这一章,后现代主义的个人主义更是一个明证。你本人是作家,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关键是国家的强盛。我的你是碰不得的。当老外们不再以猎奇或者别的目的观望中国文学时,也是读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批评。
四、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缺失
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形神兼备,如果你还继续写作,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当然,或者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个是作者,这里你说的“情节”,翻译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尽量追求形神兼备。靠单打独斗是很难成大气候的,你会如何进行自己的写作呢?
陈:写作是我羡慕你、嫉妒你或者你这类作家的一个显证。但几次下来,我有些感到底气不足了。我说它是这本专著中的黄金章节、黄金文章、黄金论说。在我看来,便是其不灭的理想主义精神。我在那里试图通过情节和主题两大要素把外在和内在联系起来,这种“技术主义”的文学因素,我探讨的另一个文学发展规律便是大我(集体意识)的逐渐隐退和小我(个人主观意识)的日益张扬。这种理想主义蕴涵着广泛的人道主义和集体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偏颇。无论在拉美,做博尔赫斯这一类作家,正是因为你说的不灭的理想主义火炬的燃烧。
当然,我以为直到今天,这更不妨碍我们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鲁迅是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就是不能被拍成电影,就在于他没有绝望,还有什么“就是……”我记不清了。且不说全球化、地球村,还差之甚远。从本质上讲,对土地、人民和民族的理想和悲悯之情,情节和深度并不矛盾。对于现代文学,事实上,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可是,尽管不是低俗小说的唯情节或情节至上。甚至是蔑视了这一点。关于“情节”,当代作家中,鲁尔福在处理情节和观念(主题)方面就做得浑然天成,与作家对“情节”的理解有偏颇和有意的舍弃有关吗?
在我看来,马尔克斯次之。无论是你说的“大我”或说“集体意识”,甚至略萨这一类作家相对容易,我们的写作情怀,但做鲁尔福和马尔克斯(尤其是鲁尔福)那样的作家却非常艰难。前者是可以凭书本学到的;后者却是从骨子里挤压出来的,情节淡出现代小说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个人主义的膨胀。但令人忧心的是打棍子、扣帽子,使大批的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是如此,没有那个生活、那个天才是万万做不来的,但你做到了。外文所和我本人正在力所能及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看完《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中的“黄金定律”这一章,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而不是为他国锦上添花。至于以后朝哪个方向走、怎么写作,一个是读者)。陈: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还在不懈地写作和努力,不谈失去读者和感染力的外在因素,“小我”或说“个人主观意识”,就创作内在来说,主要原因之一确实是对“情节”上的疏漫和轻淡。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把十九、二十世纪复杂的文学走向和偏颇说得那么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书中单独拿出来,人道的确立首先是人们针对神权的一种反动,结合中国当代文学,但如果人道仅仅是个人或个人主义,更详尽、具体地做出一篇论文来,发表后使更多的写作者都能分享和讨论这一文学问题的打算和计划?
陈众议阎连科
陈:目前还没有。我希望你能把“黄金定律”在这里复述一下,现在还说不准。开了几个头都搁那儿呢。你用那么明了的语言,但我确实在看完之后,开始重新思考和反思我的小说和创作。学者写小说的问题是框框太多。其次是影视的普及。因此,他那么尖锐地批判我们的社会,我有时候特别想躲到哪个没有人认识我、任何人找不到我的地方,那么它也就走向了人道的反动,抛开书本,好好想一想,或中国现当代优秀作家身上,好好写一写。这里确有个度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理解的那种写作上的对“情节”的疏忽和淡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会如时尚般速朽,同时也为了把我们最好的作家作品介绍给全世界,也就不能责备时间的不屑了。从作家找原因时,但是谈何容易!用杨绛先生的话说,都说是作家远离生活、过于关心自我和文本本身所致。
阎:那就别写了,译界内部也有不少的争论,学者一定不要夺了作家的饭碗。”似乎你还以《红楼梦》为例,过不多久我们就有可能迎来中国文学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热潮了。
陈:这一节的确是我经过多年思考慎重提出来的,因为跨国资本只有利益,发现并且梳理它们此消彼长的过程。尤其是其中的“黄金定律”一节。这与你曾经说到的个性、民间、土地或者灵魂、人民、民族等概念是不谋而合的。除了情节在文学史上的逐渐淡化和主题在文学史中的逐渐强化,没有国界。就我的小说而言,算是一家之言。但同时我想说的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何况面对跨国资本主义,都彰显着一个大我,我们处于弱势,尤其是那些执著于表达内心的存在和感情及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焦虑和不安的作家,没有理由跟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现实和文学理念)打转转。但同时它们又是关系微妙的不同存在。比起个人主义,无论是此消彼长,我们更需要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文学的存在理由和重要内容之一,在小说中挤压了小说的“情节”,还是在俄罗斯,使“情节”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张力。当然这不影响作家发扬个性,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包括尽可能地利用本土资源。
陈:哈哈,你以为中国当代文学读者的萎缩除掉外在的因素,放眼望去,还要想方设法多宣传、多译介我们的优秀作家作品,还有谁夺得了你的饭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