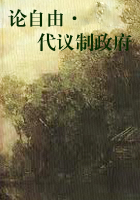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0524。
在晚清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颇有点意味深长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都曾经把备受侵凌欺压、面临亡国灭种险境的风雨飘摇的中国比作一栋千疮百孔、即将倾塌的“千岁老屋”。但对于这栋老房子,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应对方略。
最早作这样比喻的大概要算是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在接见即将赴四川臬司任的张集馨时,勉励张要认真整顿吏治,说:“汝此去,诸事整顿,我亦说不了许多。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道咸宦海见闻录》,89页)道光帝讲这段话时,鸦片战争才过去几年,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已经日益显露。他关于国家像一所“年深月久”的“大房子”的比喻,反映了他思想上有了可贵的危机意识,但他只是要求“随时粘补修理”,却提不出任何根本解决的办法。
清代官德丛谈“老屋子”的比喻洋务派的领军人物,曾经一度手握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权的李鸿章,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使用过类似的比喻:“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10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李鸿章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讲这段话的。由于他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这段话的主旨在于强调客观,诉说苦衷,为自己开脱。所以在这段话之前,他还特别强调说:“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同上书,107页)他所说的“环境所迫”的“环境”,就是指清王朝已经像“一间破屋”,他这个“裱糊匠”只能“勉强涂饰”,“支吾对付”,却不料日本侵略者竟来“爽手扯破”,结果“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了。因此,他这个“裱糊匠”是不能“负其责”的。
我们且不论李鸿章的这种辩解是否有道理,他的这段自白,对我们正确了解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却是大有帮助的。有人把洋务运动看做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认为如果按洋务运动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个看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曾经充分肯定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方面的“荜路开山”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严肃地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所谓“根本不净”,是指这个运动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一切举措以不触动封建统治秩序为最高准则。但这个时候,封建统治已十分窳败,极端腐朽,早已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洋务运动尽管“经划屡年”,最终只能“一无所成”。维新派毫不含糊地指出,洋务运动是一场并未能使国家民族臻于独立富强的失败了的历史活动。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评判,在李鸿章自己的讲话中得到了印证。李鸿章等人办工厂、筑铁路、建海军等等,无非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对“破屋子”“东补西贴”地裱糊一番。当然,修葺裱糊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要靠这种办法使“破屋子”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显然是缘木求鱼。看来,不论是旁观的梁启超还是当事的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比今天的有些研究者似乎还要客观和实事求是一些。
梁启超写文章“笔端常带感情”,是一位充满激情、善于鼓动的宣传家。他也有一段关于“老屋子”的议论,至今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他在《变法通议》中写道:“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无不亡,由后之说无不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关于“老屋子”的比喻,从道光帝那里,我们看到了忧虑和忐忑;从李鸿章那里,我们看到了敷衍和无奈;从梁启超那里,我们则看到了激愤和奋进。梁启超批评的第三种人,实际上指的就是洋务派,在他看来,尽管洋务派在三种人里属于“又其上者”,但由于他们只是“补苴罅漏”,“苟安时日”,所以“漂摇一至”,仍然难免“同归死亡”的命运。梁启超认为,对于这栋“老屋子”,应该“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也就是要实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几乎与此同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和《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也将中国比喻为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厦,并大声疾呼地号召志士仁人“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当时孙中山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稍后的革命派的报刊上,还是利用“老屋子”的比喻进行了革命的鼓吹和宣传。如汪东以寄生的笔名发表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一文,就这样写道:“且亦知中国之削弱,所以至于此者,其故何也?则以陈陈相因,积弊不扫,而曾无一度之廓清也。日本户水宽人尝评吾国曰:清人之治国,如居室然,不于其未雨而绸缪之,及其敝坏已达极点,又不毁屋而重构,而维弥补漏,跼蹐以处,疾风骤雨之来,则漂矣。噫嘻!他人言之固如此其亲切而有味也哉!夫今日之中国,其敝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而重构,轮换一新,未尝无及焉,则革命之谓也;弥缝补漏,跼蹐以处,立宪之谓也。今世各国其号称立宪而未尽泯乎专制之性质者有之,自今以往,世界之程度愈高,则其政体之于民必愈便,百年千载,终不尽易立宪为共和不止。”(《民报》第2期)批评洋务派“补苴罅漏”、“苟安时日”的梁启超,转身之间又被革命派批评为“弥缝补漏,跼蹐以处”,批评别人和被别人批评的词句几乎是一样的,但内容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革命派批评立宪派只是“补苴罅漏”,是因为革命派深信,对清王朝这栋“老屋子”,仅仅实行一点“去其废坏”的改革是不行的,必须“毁屋而重构”,也就是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才能为新世界的到来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