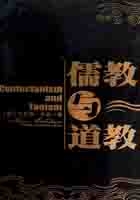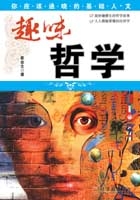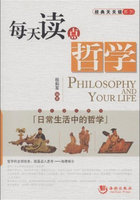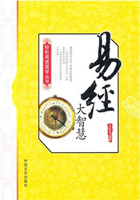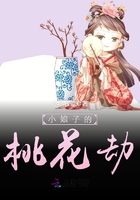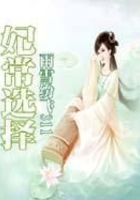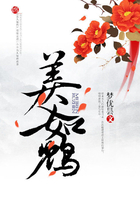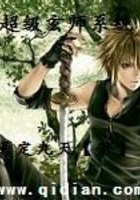首先,贺麟提出两种知行合一说:“自然的知行合一”和“价值的知行合一”。自然的知行合一所谓知,指一切意识活动;行指一切生理活动。知是精神性的,行是物质性的。知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任何活动都是意识活动和物理活动的结合。不过知和行的显现程度是有等差的。有的活动主要是意识的活动,如读书。有的活动主要是生理的活动,如运动。前者是显知隐行,后者是显行隐知,但二者都是知(意识)与行(物理)
两个方面的同一。贺麟所谓知行合一,有知行同时发动,知行平行、知行为同一的物理—心理活动的二面诸义。他把这种知行合一叫做“自然的知行合一”,因为“只要人有意识活动(知),身体的跟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取消的。凡有意识之伦,举莫不有知行合一的事实”(《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36页)
。“价值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是,知行合一是应该如此的理想,须加以人为的努力才能达到,不是现成的事实。价值的知行合一所理解的知和行,与宋明理学所谓“知”“行”意义略同。价值的知行合一是先据常识将知行分为两事,再用种种努力求其合一。贺麟认为,无论是自然的知行合一还是价值的知行合一,若加以思辨地分析,皆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因为人类的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受知的指导而不是凭本能行动。人的活动失去知的意义,就是纯物理的活动。所以知是体,行是用,“行为者表现或传达知识之工具也,知识者指导行为之主宰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41页)。
第二,知主行从,知永远决定行,行永远为知所决定。错误的行为为错误的知识所决定,正确的行为为正确的知识所决定,概莫能外。
第三,知是目的,行是工具。行为永远是知识的手段和功能。贺麟的第一和第三个结论,是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绝对精神决定着自身的一切外化,人类文化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都是为了完成绝对精神的目的。第二个结论吸收了斯宾诺莎关于行为永远被思想所决定、正确的知识表现为自由的行为、知天理是行天理的前提条件的思想。贺麟并且批评了“副象论”,这种理论认为身心永远平行,但精神活动只是身体活动的影子,因此“身主行从”。他认为副象论是同王阳明的学说正相反对的。贺麟还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补偏救弊的知行合一,一个是本来的知行合一或知行的本来体段。所谓补偏救弊是说,为了补救知而不行、揣摸影响和行而不知、冥行妄作两种弊病,将本来合一的知行分作两事说。这样的知行合一是理想,须努力去求方可达到。本来的知行合一是说,知行自然如此,本来如此,欲知行不合一而不可得。贺麟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虽近于“自然的知行合一”,但仍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实际上强调的是价值的知行合一。价值的知行合一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朱熹主之,因为他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用敬为二事,二者的合一是人追求的理想。一派是率真的价值的知行合一(知行的本来体段),王阳明主之。而由朱熹的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到王阳明的直觉的率真的知行合一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贺麟这个观点,与他认为中国当代哲学是陆王之学的盛大发扬,从朱熹到王阳明,从理学到心学、理学合一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的看法相一致。
新心学的知行合一说受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学说的影响,借鉴了当代西方行为心理学派对知行问题的见解和分析方法。他的目的是:
第一,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打破独断论的伦理学,为正确行为找出知识基础。这是他对比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特点后对中国伦理学缺乏知识论提出的一种改进。第二,他欲强调知的决定性、首要性,引导人们主要在知上用功,从而破除“知易行难”的旧说,以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相配合,为孙中山改造国民偷惰、畏难苟安的积习,进行“心理建设”的大计进行理论上的证明。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是阳明学说在现代中国的一点余响,也是贺麟古为今用的一点尝试。
四致良知
1.致良知的提出“致良知”是阳明在平定宸濠之后总结以前不同时期的讲学宗旨,特别是几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体悟而提出的学术总旨。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龙场之悟,阳明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结论。“吾性自足”,即良知本具;不求理于事物而求之于心,即致知。不过此时的“致良知”,只是规定了王阳明自内之外的功夫路向,许多具体内容,要待此后因实践范围的扩大、体悟的深入而逐渐展开。平定宸濠及其后的处忠泰之变,对阳明来说是一次意志、智慧的大考验。中间许多性命交关、生死搏斗的曲折,引发阳明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来一番彻底的省视。阳明及其弟子曾多次谈到这次事变对阳明学术进步的意义,《年谱》说:
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阳明自己也说:
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又说: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
弟子钱德洪也说:
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盖先生再罹宁藩之变、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
在险恶的政治、军事环境中,身处群小汹汹、谗陷日构的氛围,王阳明通权达变,沉着应付,终于出离困境,转危为安。在这种“濒死者十九”的环境中,良知所蕴涵的意志、理智、情感诸方面得到了极大锻炼,对人生的真谛、人世的本质有了更加通透的理解。以前种种假面、种种牵缠、种种回护,到此一起斩断;所谓真我、良知越加精粹,越加澄彻。阳明曾自述这种改变说:
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下)
行不掩言,信得良知真是真非是“诚”,“平澜浅濑,无不如意”是明,阳明此时真正达到了明则诚,诚则明,诚明两进的阶段。
王阳明的高度的处世智慧和应变能力,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在某一次事变中忽然得到的,而是从他的学说和实践的长期锻炼、陶养中得来的。他的良知学说中最主要的是意志和理智两个方面。按阳明的理解,朱子学的功夫进路最多只能给人以智识,但不能给人以意志。而在艰苦的环境中(如龙场),在复杂险恶的局面下(如张许之难),意志比智慧更能发生效用,意志在整个人格结构中,是最重要的。他终生提倡一条以道德为首务,以道德带动知识,以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为归宿的路径。他平时教导弟子更多地注意在道德理性上、在意志上用功,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人在事变中锻炼意志:
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与王纯甫》,《王阳明全集》第154页)
阳明常要弟子寻得力处,这个得力处就是切实身心体验,不可漫漫口耳讲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理、致良知诸说,皆是自己亲切体验的产物。他的“致良知”宗旨是他半生军事、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讲学宗旨的概括和提炼。他以高度的融释能力,把《大学》的三纲八目,《中庸》的慎独、诚、性、道、教,《尚书》的惟精惟一等儒家哲学范畴糅进“致良知”中,使得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广。他甚至把良知等同于易:
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这种涵盖面至大至广的“良知”,引起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它表示王阳明的学问臻于化境,有极大的包容能力。他可以用致良知三字解释差不多一切有关的学术问题,“累千百言,不出此三字为转注”。这是阳明学“简易直接”之所在。由于这种简易和变通,使得阳明学说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迅速在广大地域流传,蔚成当时的显学。另一方面,这种简易和变通使后学对良知的理解出现了多方面的分歧,离开了阳明立说的原意。黄宗羲尝说:“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掺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黄宗羲这个评断有不确切的地方。阳明良知之旨其义甚明。学术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使阳明弟子偏离师旨是真,但绝非“未与学者深究其旨”。从五十岁揭致良知之教到五十七岁逝世,阳明对致良知作了大量阐说,特别是因父丧居越期间,阳明的讲学活动达到高潮,致良知是与弟子反复论述的问题。晚年概括其一生学问宗旨的《大学问》,以致良知贯穿《大学》诸义,“致良知”可以说发挥无余蕴。
2.良知诸义(1)天理之昭明灵觉良知概念源于《孟子》。孟子曾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人具有一种不学不虑便天然具有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最初的表现便是爱亲敬长。所以称为“良知”,一是因为这种道德意识是善的,二是因为它是先验地具有的。道德修养就在于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由“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培养至“溥博渊泉”地位。孟子的全部修养方法,如集义、养气等皆以此为出发点。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这一思想,他说:
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欲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传习录》上)
这段完整的阐述,有本体,有功夫,将王阳明致良知的意思明确道出。对比孟子关于良知的定义,可以说,阳明更加突出了良知自动地呈现于心并为主体所觉知的品格。如果说,在孟子那里,良知还主要是一种朦胧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四端之情)的话,在阳明这里,良知就主要是一种明显呈露于知觉层面的“意识”。阳明给了这种意识以更多的“知”的色彩。其次,这段话把孟子以后儒家的修养功夫,特别是为程颐、朱熹反复强调的“胜私复理”的内容加了进来,使致良知功夫的两面——正面的保任良知充塞流行和负面的胜私复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和《大学》的致知诚意结合起来。这段话是徐爱所记,表明阳明把孟子的良知和《大学》的格物、诚意融合在一起,在他早期思想里就有了。虽然阳明对孟子的思想有了增广,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这里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孟子的,比起他晚年赋予良知的许多复杂精微的思想来说,仍是简单、平实和最基本的。在代表晚年成熟思想的《大学问》中,阳明也以此为全部功夫的出发点:
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也,而其一体之心犹能不昧。……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在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性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王阳明全集》第968页)
在阳明看来,“人是天地的心”,人最多最完美地体现了宇宙根本法则,从这个方面说,人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宇宙。而人心又是人之知觉灵明所在,所以,“人心是天地发窍处”。宇宙根本法则通过人心这个孔窍表现出来。人心是宇宙的全部精蕴所在,良知是天理的表现。阳明说: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传习录》上)
又说: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
这是阳明“良知即天理”的最明确的解释。阳明的“良知即天理”在表达心与道德理性的关系上比陆九渊的“心即理”更为精粹:“心即理”的心没有明确区分形而上的性理和形而下的情欲,而只笼统言心,故攻此者甚众。但“良知即天理”因为有“良”、“天理”作限定,保证了良知内容的纯洁性。并且在阳明哲学中,天理在心中的表现是主动的,只要不被私欲障蔽,心自然就表现为天理。良知就是天理在心中的自觉。关于这一点,刘宗周说得十分清楚:“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明儒学案·师说》)良知最基本的内容,一是性,一是觉。“所性之觉”就是天理自然显露而为主体所知。因为良知是性理在人心的显现,所以人与天理是相通的,人与宇宙万物处在一个大系统中,天、理、性、心、气等等,不过是对这个大系统的不同方面的描述:“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传习录》中)又说:“性一而已”、“心一而已”等。阳明屡屡说要破除内外之分,他的着眼点在宇宙这个大系统,他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从天人合一、良知是天地万物的发窍处出发的。
(2)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王阳明良知内涵的又一重要方面。王阳明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是非之心,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是是非非”,即因其是而好之,因其非而恶之,亦即好善恶恶。这里引的阳明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意为,良知有天赋的好善恶恶的趋势。一是“知是知非”,即良知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阳明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它是,非的还它非,是非只依着它,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