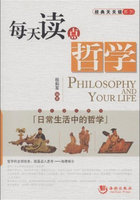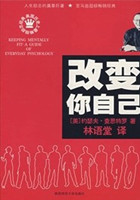如何評價錢謙益降清的行為?筆者個人認為只有殉義而死者、堅持抗清者、終生拒不仕清者纔真正有資格批評他。當時有許多人對錢謙益冷嘲熱諷,但他們自己也並非真的能在生死關頭堅持心中的原則而毫不動搖。他們生活於清軍鐵蹄之下而不敢反抗,甚至最終為了生計扭扭捏捏地應試赴選,和錢謙益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坐而論道易,躬行實踐難。錢謙益也曾慷慨陳詞,但真到國家需要的時候,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種種私心雜念一霎那間都浮上心頭,而終於失節。沒有大勇氣、大智慧、高尚情操的人是很難克服這些誘惑的。死,永遠比生更沉重。一個人的生命有多重意義,就個人而言,包含個體生命的存續、個性的張揚、身心的解放與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就社會而言,則要維護自己所處群體的利益,保證群體意志得到實現。自我價值溝通了自我與社會的聯繫,如果以社會為中心,則自我的實現應在社會中完成;而如果以個體為中心,則自我價值的判斷更多在於己身。錢謙益受王學影響,但同時儒家倫理準則又與之糾纏,因此在投降與自殺之間徘徊。但經過多年的坎坷磨難,他逐漸拋棄道德理想主義,走向政治實用主義,在明末特別是南明不惜屈氣節而求實利,因此他的降清仕清又不是偶然的失足,這也正宣告東林黨後期借政治實用主義實現道德理想主義策略的破產,它最終必然蛻變為掩蓋個人利益追逐的漂亮招牌。
無疑錢謙益的降清是有種種理由的,如重生惡死、修史的心願尚未完成等等,但不管怎樣,他背叛了自己曾經賴以自傲的氣節與時人對他的尊敬,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感情[36],這與他所享有的威望極不相稱,也對不起抗清而死的恩師孫承宗。面對危局,他確實無能為力,但他最終放棄了一切人格、尊嚴、名譽而屈膝投敵,這是封建社會中士人品格的最大侮辱。比起殉節者、抗清者、遁隱者,他不夠堅強,不夠勇敢,未能經受住誘惑與考驗。他曾在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作的《重修維揚書院記》中批評當時“朝著無槃水加劍之大臣,疆場多扣頭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並說:“夫立乎人之本朝,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37]真是鏗鏘激昂,擲地有聲,可是言猶在耳,他卻變節事清,兩者的反差如此強烈,不啻對他自己的尖刻嘲諷。
“時窮節乃現”,在生與死之間,人格高大與卑微的差別便完全暴露出來。自清軍南下,義不受辱,拒絕降服,乃至奮起抵抗,兵敗被殺者極眾,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勇氣與堅定,對於道德理想與民族氣節的堅持讓我們肅然起敬。“金陵破,秦淮河丐者碎碗畫壁上曰:三百年來盛治朝,兩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髠,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迂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啓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升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官,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吏部考功司員外郞青浦夏允彝絕命詞: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愧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願言從子,握手九原。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38]……壯烈殉國者很多都是錢謙益的老友、相識,如祁彪佳、陳子龍、侯峒曾、金聲等,錢謙益的氣節、精神自然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
當然,同死心塌地效忠清朝的降者相比,錢謙益心中的良知從來也沒有泯滅,他降清並不等於說他就沒有民族感情,氣節蕩然無存,只不過是對死的恐懼壓倒了這一切罷了,所以他雖然懾服於清軍的武力之下,但對明朝依然有深深的眷戀。他曾對清朝抱有幻想,但薙髮之令下後,清朝消滅漢族衣冠文化與民族意識的企圖得到暴露,江南士民奮起反抗,遭到清軍的血腥鎮壓。清朝決心借殺戮以立威,推行民族征服與民族壓迫,這無疑令錢謙益大為反感,對與清朝和平相處、互相利用的幻想也破滅了。他此時痛悔降清、仕清,並努力為自己開解,試圖平息內心的不安,但輿論的壓力與自己的悔恨讓他生命中的最後十餘年充滿了艱辛與苦澀。
注釋:
[1]《明季南略》卷四“马士英奔浙”、“赵监生立太子”、“十二日癸巳”条。李清与夏允彝认为张捷、杨维垣是死节,笔者以为不然:十一日马士英出走,留下几十名黔兵全部被百姓击杀。十二日,获马士英中军八人,也全被赵之龙斩杀。马士英的党羽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清军尚未来,京城秩序大乱,民众殴打王铎,抢掠马、阮、杨、陈诸家,说明他们在宣泄对弘光朝的不满情绪。当时有谣谚曰:“马刘张杨,国势速亡”(《明季南略》卷三),张捷、杨维垣应该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故而极度恐惧而自杀。
[2]《明季南略》卷四。
[3]《明季南略》卷四。
[4]《三垣笔记》附识下。
[5]据《国榷》卷一百四,在其他记载中则有不同,如《明季南略》卷四“十四日乙未”条云:“报清豫王兵到都城,忻城伯赵之龙率礼部尚书管绍宁、总宪李乔,各遣二官缒城出迎,跪道旁高声报名。”阮大铖似乎当时也已逃走,不在南京。
[6]《明季南略》卷四。
[7]汪龙麟《钱谦益诗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民国时期的各种文学史及有关论文,在阐释钱谦益失节事时多采此说。”而据笔者目前所查阅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十餘种文学史(如胡云翼、林之棠、曾毅各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其中论到钱谦益多是略为介绍其经历,认为他人品低劣,文学成就高,分析其投降原因者极少,“富贵逼人”说也仅见于《中国文学史讲话》。
[8]《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4期。
[9]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10]汪龙麟《钱谦益诗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称:“金谱之成书与钱文选之翻印的时代,正是日寇大举侵华之时。金、钱于民族危亡之际为钱谦益降清所做的如上辩护,不独证据不足,且难免有取媚汉奸之嫌了。”要说明的是:钱文选翻印金谱可能有取媚汉奸的嫌疑,这点在来新夏的《近三百人物年谱知见录》中也有提及。但金鹤冲作《钱牧斋先生年谱》始于1911年,成于民国戊辰,即1928年(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跋),曾于1934年印行,而日寇大举侵华是在1937年。此书立论确有失偏颇,但金鹤冲在书中强调钱谦益的反清行动与心志,洋溢着民族气节。金鹤冲本意可能是为家乡先贤讳饰,与为汉奸辩护无关。
[11]《有学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北方论丛》1992年第4期。
[13]《柳如是别传》第五章。
[14]《柳如是事考》,台北:作者自印本,1978年版。
[15]发表于《复旦学报》1989年第一期。
[16]《吴中学刊》1996年第2期。
[17]《有学集》卷四十九《题邵得鲁迷途集》。
[18]史惇《恸餘杂记》“钱牧斋”条,转引自《柳如是别传》。
[19]参见《有学集》卷四十六《李忠毅公遗笔跋》。
[20]《明季南略》卷四。
[21]《明季南略》卷四。
[22]《明季南略》卷四。
[23]《明季南略》卷四。
[24]《明季南略》卷四。
[25]《明季南略》卷四。
[26]《虞阳说苑乙编》第三册。
[27]《祁忠敏公日记》第六册《乙酉日曆》六月初五日。
[28]《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条。
[29]《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30]《牧斋外集》卷二十二《与邑中乡绅书》。
[31]《多铎奏疏》,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32]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33]据《明季南略》卷四与《小腆纪年》卷十。
[34]《牧斋遗事》。
[35]引自钱谦益《与常熟知县曹元芳书》,《虞阳说苑乙编》第三册。
[36]在《初学集》卷二十七《书武林禳夷事》中钱谦益对满洲攻杀明军表示强烈的义愤,并极端仇视所谓“建州夷”。
[37]《初学集》卷四十四。
[38]《枣林杂俎》仁集“群忠备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