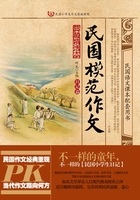吕品丝毫不被他激怒,仍平静无波地回答:“我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这几年我一个人,都活得很好。”
杨焕热切燃烧的眼神慢慢清明下来,他抿上唇不再说话。
她背水一战,甚至连孤独终老的准备都已做好,她不是在赌气,而是在最冷静的情况下作出的最终决定。
吕品又退开两步,室外的月光透过窗帘洒在地上,窄窄的一道幽白光带,像隔开他们的银河。
他在这头,她在那头。
他身上还裹着她给他搭上的毯子,毯子的里面裹着的,却已是一片破碎虚空。
早上杨焕走的时候,吕品在他身后叮嘱:“你熬了一晚上,别开车了,打的回去吧。”
杨焕脚步在门口停住,尔后回身冷冷道:“别关心我成不成?我心里碜得慌!”
他一赌气,还真就开着车回去,心里甚至有股悲壮的想法,疲劳驾驶又怎么地?死了好,死了好,死了让你做小寡妇,让你后悔去!
可惜天不遂人愿,一路都在堵车,连出点事故的机会都没有,只得慢慢地挪回家。刚打开大门,一只拖鞋就飞了过来,夏致远正躺地毯上朝他伸开双臂:“老杨,你简直是为改变这个世界而存在的!”
杨焕哼了一声,没有如他所愿的扑上去,而是钥匙一丢,脱掉外套,踩上客厅里的跑步机。
速度不断调高,从最慢的3.6KM/H一路调到7.2KM/H,然后是10.8KM/H。跑步机均衡而稳定的噪音,好像就在他耳边嗡鸣,那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像涨潮时拍岸的浪头,一波未去,一波又来,拍至灭顶。
跑步机的皮带,仿佛变成一条时光的穿梭带,一串一串的记忆,都在这里倒带。
是公司team-building去张家界玩,天桥上挂着错错落落的金锁片,片片都刻着恋人的名字和俗气的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的愿望,他心中悲苦,不敢刻下二人的名字。
是那个冬天的圣诞节,从温暖如春的加州到冰封雪飘的麻省,大巴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带着渴切的希望;又从冰封雪飘的麻省到温暖如春的加州,大巴仍开得飞快,把他的心留在极北的严寒里。
是不知哪年的春节,他威逼利诱公司没买到票的小美工跟他回家过年,到吕品面前去耀武扬威,她只是局促地笑。她不知道,她笑得比哭还难看。
是无数个交作业前的课间,他下笔如飞地抄她的作业,她在一旁可怜巴巴地说:“你以后还是自己写吧,有不会的我给你讲都成,不然期末考试你怎么办呐?”
是青春期的绮梦,从充斥着她发丝撩拨的温柔乡中醒来,再在自习时不经意的一转身,明白什么叫想入非非。
醒过来的时候他四仰八叉地躺在跑步机带上,夏致远大概是私报公仇,左一耳光右一耳光地抽他,还夸张地高叫:“老杨,你醒醒啊,你不在了我们可怎么办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杨焕面如死灰,迷迷糊糊地骂:“你丫号丧么?”
夏致远见杨焕能说话,马上眉开眼笑:“招魂啊!效果挺好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看杨焕一脸颓败,夏致远也能猜到,八成又是和那个“灭绝师太”有关。难得夏致远今天有良心,居然没“宜将剩勇追穷寇”,反而安慰道:“又受打击啦?有什么大不了的呀,再难,再难能比罗家英向汪明荃求婚还难?”
杨焕从兜里摸出那张存折,手虚弱得提不起劲:“她要去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在那边分了房子,这是另外的安家费。”
夏致远看看存折面额,咝了一声:“这得卖多少年啊?”他瞅瞅杨焕,极无奈地摇头,“师太的觉悟也太高尚了吧!”
杨焕从指头缝里瞟夏致远一眼:“阿夏,我要是把股票从B级转向A级,你怎么看?”
夏致远倏地跳起来,毫不留情地在杨焕腿上踹了两脚:“你不如找根绳子打个圈让我吊死算了!”他抽起挂在跑步机上的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朝杨焕叫道,“有种你试试,我死给你们看!这店是我一个人开的吗?我容易么我,你们这些娘希匹,动不动就撤资退股!”
杨焕无力地从指缝里白夏致远一眼,外面人常说自己做事路子野,谁会知道这个在外沉稳持重的八哥才是个疯子?
原本也只是试探而已,夏致远的反对在意料之中。
Memory网虽尚未上市,但内部股权却早划分成A级和B级。A级为普通投资股票,公司部分老员工和接受的外界投资均属此类;B级股票则拥有超级投票权,在公司重大决策中的投票权重远超A级股票。这样的划分是左静江在创业之初便决定的,目的是保有高层团队对公司的绝对控制,防止融资过程中外部资金过多左右公司走向。这固然对后期融资造成阻碍,却又不得不说是团队对自身信心的一种体现。
股票从B级向A级的转化是不可逆的,其真正的意义便是,退出管理层。
公司成立五年以来,作出这样决定的人不在少数。早期创业时许多人都还是学生,荷包并不宽裕,遇到经济困难,只能退股来兑现。
Memory几乎是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当然报纸上只会赞颂他们从咖啡屋里创业的“浪漫神话”。
其实没什么浪漫的,在咖啡屋干活无非是因为当初没钱租办公室。那时三五万块钱就能逼死英雄好汉们,如今看到那些投入都有百倍的回报,但当初,谁知道呢?
即使Memory如今身处融资困境,外面仍有不少虎视眈眈的眼睛,至不济卖盘,收益也必然可观,现在退股纯经济损失也是六位数往上走,那无疑是最不智的行为。
用夏致远往年劝阻他人退股时的话说就是:“那可都是血汗钱呐!”
玩完一哭二闹三上吊后,夏致远又恶狠狠道:“娘希匹,新社会啦是吧,妇女都解放啦,现在流行妇唱夫随啦!”
“我就这么一说……”杨焕在跑步机上翻了个身,阖着眼又问,“那个……罗家英求婚求了几十年,成功了没?”
夏致远又死踹他两脚,发泄完毕后高唱着“Only You Can Save Memory”飘进卧室。
Memory绝地翻身,却因为这样不走寻常路的改版,引发网络上对CE二期预研计划中的间谍案的再度关注。
尽管从各研究机构到Memory自身都努力规避CE二期预研项目间谍案,然而潮水般的论战仍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有人快递了剪刀和绳子到严律师的事务所,留言是“你们这种为了钱就替卖国贼辩护的律师,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严律师从事律师行业前的种种背景也被人肉出来,说他本来就是靠克扣民工的黑心钱起家的,说他小白脸靠女人上位,说他谋杀发妻获取高额保险……甚至于连他走路时不注意踩到一只蚂蚁,也能作为他虐待动物的证据拿出来大肆批判。
所有牵扯进来的人里,杨焕无疑又是最面向公众的,于是Memory网上每天都有无数人要他出来澄清,否则就是不配做中国人云云。
偶尔也有人站出来,说大家要冷静客观地等待结果,也立刻淹没在口水唾沫的汪洋大海中,且一定被斥责为“将来日本人打过来,最先投降的一定是你们这种走狗!”
势头汹汹,持续了大半个月才消停下来,杨焕的改版计划在这个月内为网站流量贡献巨大。做网站的除了技术实力,另一样至关重要的便是要吸引眼球。改版要求技术并不高,绝多数网站都能做到,只是Memory珠玉在前,再有人效仿,也不过是给Memory增添知名度而已。
这样好消息与坏消息交织澎湃的时期,杨焕终于克制住自己,没有再去酒店找吕品。因为找了也于事无补,碰面他就忍不住要开火,开火后看着她难受,然后自己更内伤——何苦来哉?
也许是该到冷静冷静的时候了。
间谍案的判决也下来了,纵然严律师多方论证袁圆的行为在实质上构成的伤害有限,且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整个案件的涉案人员绝大部分最终都受到从严的判决。
袁圆并不是最严重的,判了十四年。
判决结果杨焕是在网上看到的,看到十四年这几个字眼的时候,他心头升起一种难以言述的复杂情绪。
不知道该恨她,还是该可怜她。
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袁圆身上,吕品大概也不会如此决绝地以为,他们再没有丝毫可能;如果不是袁圆出卖图纸,吕品也许不会如此坚定地签下合同去一线……
然而袁圆偏偏是吕品唯一的朋友。
杨焕竟不敢去想象,此刻吕品究竟有多难过。
更没有想到的是,吕品会主动联系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他心里不可遏止地升起某种希望,某种潜藏的甚至有些卑劣的希望——也许失去袁圆,会让吕品感觉加倍脆弱?会让她更觉孤单无依?会让她渴望他的怀抱?会让她稍稍妥协,需要他的安慰?
他抑制住这种在短暂的几秒内呈级数倍数增长的欣喜,用尽量平淡的声音问:“什么事?”
吕品的声音有些诚惶诚恐:“你周末有没有空?周六——周日也行,不用一整天,半天也可以……”
“有。”
“要是忙的话……”
“有,”像是生怕她继续撤退,杨焕抢先截断她的话,“我有空。”
他想说我今天就有空,现在,立刻,马上,有空,随时,为你。
终究还是没有出口。
吕品找他是为周末去给袁圆探监,她吞吞吐吐地没说要他去的原因,杨焕也就没问。进去的路上遇到钱海宁,他是往外走的,垂着头,没了魂似的。吕品想开口安慰他,又不知从何说起,钱海宁闷闷苦笑:“她不见我。”
声音有如世界尽头般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