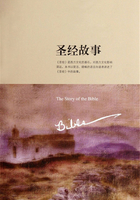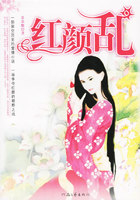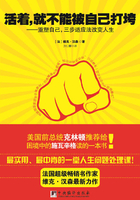信不能穷理达本,而是达到悟的一种手段,达到了顿悟,闻解就“谢”而不起作用了,犹如果子成熟后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不过,悟解并不能自然产生,必须依靠佛教知识的不断增加,依靠不断地渐修。要用佛教信仰和修持去克制个人思想和行为上的迷乱,以去掉系缚,灭绝烦恼,最后顿悟获得解脱。这就说明竺道生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从闻见得来的佛教知识,认为顿悟也是需要依靠渐修的。但是闻解是由信仰与修持得来的,并不是自我的彻悟,见解是真正的自我证悟;闻解只是渐修的过程,见解是成佛时的顿悟,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在竺道生看来,修行成佛是渐修顿悟的过程,一旦在宗教实践上有了所谓自悟,过去仅从闻见得来的信仰就不再起作用了。
佛典上所讲的修行十种次第等都是佛用来使众生易于理解、接受,使信仰者自强不息、努力精进的,并不是把开悟的境界分成若干层次。渐修的阶次与成佛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竺道生对见解与闻解、悟与信、顿悟与渐修进行区分,是建立在般若学的理不可分和涅槃学的直指心性的学说基础上的。由理不可分而肯定顿悟,强调冥符真理不能渐悟,不是渐悟;由直指心性,佛性在我,理本在我竺道生认为佛性就是理。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6章;方立天:《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见《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2。,也即见解之事在我,不假外求,重视主体的内在见解——真理的自然顿发,进而肯定悟与信不同,悟不是信。
四、能至与一极竺道生的顿悟说得到大诗人谢灵运(385—433)的大力支持。谢一生笃好佛理,揄扬佛旨,与南朝佛法关系甚深,在南京时曾和竺道生有过交往。他专门辩论顿渐问题的《与诸道人辨宗论》(《广弘明集》卷十八),不仅基本上与现存的竺道生关于顿渐问题的说法相契合,而且还发挥了竺道生的顿悟义。
谢灵运的顿悟说主要阐发竺道生的理不可分义,并且具有自觉地折中儒佛两家的特色。《与诸道人辨宗论》说:
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不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
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
“颜”,颜回。“一极”,指宗极,宇宙实相。“新论道士”、“道家”,皆指竺道生。这段话的意思是,佛教主张,得道成佛的前景虽然遥远,但是只要坚持不断地学习是能够达到的,人生的烦恼断尽(“累尽”),就会产生明确的认识进而悟道(“鉴生”)。儒家认为圣道很玄妙,就是孔丘的高足颜回也只能达到庶几乎圣人的贤者,要努力全面地体认虚无的本体,观照周全,从而得到宇宙的最究竟的道理(“一极”)。竺道生高唱新论,宣传观照(“鉴”)湛然常静的境界(“寂”),是极其微妙、不容有任何阶次(“阶级”)的,要悟就悟,不悟就不悟。通过无限的积学过程,是可以达到成佛境界的,不应自暴自弃。去掉佛教的“渐悟”,取其“能至”;去掉儒家的“殆庶”,取其“一极”,这样有取有舍,就和儒佛不完全相同了。儒佛都是依随方便拯救万物的言教,竺道生兼取两家之说,调和儒佛,也就和佛教的旧说不同了。
谢灵运所谓的儒家体无的说法,实际上是魏晋玄学家王弼等人说的儒家圣人孔子的体无的观点,而不是孔子本人的主张。谢灵运把佛教讲的理和玄学家讲的本体等同起来,把佛教的成佛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体认宇宙本体统一起来,主张以体认不可分的本体为佛,顿悟成佛,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来说,这是把认识论和本体论牢固地结合起来,是在当时玄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折中儒道佛三家的观点。
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是一种快速成佛法,他是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首先宣传快速成佛法的第一位佛教学者。竺道生和谢灵运的顿悟说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论观念,如真理的整体性与片面性的关系、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关系、日常学习与顿然觉悟的关系、认识过程中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的关系等,都是值得人们总结和反思的。竺道生的顿悟说,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悟与理的观念为后来一些宗派所继承,成为稳定的思维定向。
慧能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的顿悟,与竺道生的顿悟说有所区别,但其思路是相通的,所受道生学说的启发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节四重二谛与般若无得
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典籍,经鸠摩罗什译出后,师徒相传,影响很大。至隋代吉藏(549—623)更继承中观学派的思想,著书立说,阐发《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的理论,创立三论宗。吉藏在创宗过程中,在理论上着重发挥二谛、中道和般若无所得等问题,发展了中观学派的真理论和方法论。
一、于谛和教谛真俗二谛作为相对的两种真实的认识,是大乘中观学派组织佛教学说、阐释宇宙万有的实相的基本论纲。吉藏著《二谛义》一书,针对南北朝时众多学派对于二谛的各种异说,提出了于谛和教谛的新说。
自从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以来,二谛说就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视。迄至隋代,三论宗以外的佛教各宗、各派,大都认为二谛是理、是境,也就是说二谛讲的是道理、真理、境界,如说“真谛之理”、“俗谛之理”以及对理的观解所现起的境界。这样就等于说有两种相对的真实存在了。在吉藏看来,佛所说的真实,即真实的理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只有佛用来说法的形式即教法可以多种多样,如八万四千法门,乃至无量法门。吉藏强调二谛是“教”不是“理”,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说教上成立的。他说:“非真非俗为二谛体,真俗为用,亦名理教,亦名中假。……不二为体,二为用。”(《二谛义》卷下)体是一,用是二,理是一,教是二,二谛是教,不二是理。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吉藏又把真俗二谛归结为于谛和教谛。
于谛的“于”是所依的意思。所谓于谛,是说世间一切现象,本来是非空非有的,是不二的,但是“于”(对于)世俗人来说是有,世俗人认为是实有,所以叫做“世谛”、“俗谛”;“于”(对于)出世的圣人(菩萨、佛)来说是空,圣人认为是真空,所以叫做“圣谛”、“真谛”。
凡人与圣人对于非空非有的宇宙万有实相,有着有空或真俗二谛的分别,这所依的真俗二谛就是“于二谛”或“二于谛”,也就是“于谛”。于谛就是“于”万有实相上的凡圣二种不同认识,世俗是“于”凡为实,真谛是“于”圣为实,凡人心中本来并不知真谛,圣人心中原来也没有俗谛,所以,于谛既不是在境、理上讲的谛,也不是圣人为了化度众生而设的“教谛”。
于谛不是教谛,但是用于谛去解释佛法,就成为教谛。教谛是说真俗二谛是佛为众生说法的手段,是化度众生以转迷为悟的工具,是一种言教,并不是说依据客观的境而立有二谛的二理。在吉藏看来,宇宙万有实相本来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认识的,是不可言说的,只有直观证悟才能把握,但为了启发、教导众生,只好强名强说。所以佛所说的二谛只是言教而不是所证的理。据吉藏《十二门论疏》卷上的说法,“教”的意义和作用有三:一是“破除迷倒,谓遮闭众非”,即破除众生的生灭、常断、有无、来去等颠倒妄见;二是“显于正理,则开通无滞”,真俗二谛本身不是理境,但作为言教也可以起显示宇宙万物实相的理的作用;三是“发生观解”,使众生体会二谛的教义,进而产生对宇宙万有实相的真实观解。由此可知,强调言忘虑绝、非真非俗的万有实相之理是不属于言教二谛的,对言教二谛是不能执著的,这是吉藏提出于谛和教谛的说法的目的。
三论宗人还宣扬,和依“情”而立的于谛不同,教谛是依“智”而立的,是佛依实智与权智两种智慧而立的。佛的实智重在真谛方面,佛的权智重在俗谛方面,二者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般若”和“方便”。佛依这两种智慧设二谛之教,使凡人由俗谛有而知真谛空,最后既不执有也不执空,达到无所得的境界。
二、四重二谛为了进一步说明真理只有一个,是不二的,宣传依不二之理而立二谛,以不二之理观二谛不二的道理,批判其他各种异说,三论宗人又把二谛发展为多重化,特立二谛三重、四重的次第之说。吉藏的老师兴皇法朗(也作道朗)立三重二谛说,吉藏在三重二谛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一重,立四重二谛说。吉藏说:
他(师)但以有为世谛,空为真谛。今明:若有若空,皆是世谛;非空非有,始名真谛;三者,空有为二,非空有为不二,二与不二,皆是世谛,非二非不二,名为真谛;四者,此三种二谛皆是教门,说此三门,为令悟不三,无所依得始名为理(真谛)。(《大乘玄论》卷一)第一重二谛是以有为世谛,空为真谛;第二重二谛是讲空、讲有,互相对立,都是俗谛,非空非有才是真谛;第三重是讲前一重把二(空、有)和不二(非空非有)对立起来,还有二边,不是中道,是俗谛,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第四重是讲前三重,包括“非二非不二”的说法,都是一种教法,不能执著,应当舍去,达到无所得境界,才是真谛。
吉藏四重二谛说的特点,首先是每一重的真谛是对俗谛的否定,前一重的真谛就是后一重的俗谛。其次,是连续性的否定,即第二重真谛是对第一重二谛的否定,第三重真谛是对第二重二谛的否定,第四重真谛是对第三重二谛的否定。凡是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都同时加以否定。从方法论来说,这是一种“双遣双非”法的系统运用。再次,在这种系列否定中也表现了正反合的模式,第一重二谛的真谛是对俗谛的否定,俗谛是“正”,真谛是“反”。第二重的真谛是对第一重真谛的否定,第一重真谛原是“反”,第二重真谛是“反的反”,即是“合”。
第三重的真谛又是对第二重真谛的否定。后者是新的更高一级的“正”,前者是新的更高一级的“反”。第四重的真谛是对第三重的真谛的否定,是新的更高一级的“反的反”,即新的更高一级的“合”。这种正反合的思维模式是以否定性为特征的,其理论目的是通过否定性的“合”以破除各种有所依、有所得的看法。最后,是对语言和思维的最终否定,对直观思维的最终肯定。吉藏强调二谛是一种言教,是佛根据不同对象立说的,不能执著为真实。也就是说,对“立”和“破”都不能执著。吉藏认为,前三重二谛都是语言概念表述的,都没有超出有所得的范围,还是俗谛,只有“忘言绝虑为真”,真谛是无法用语言和思维表述的,也就是说,佛教的绝对真理不是一般的思虑和概念所能把握的。这一些也就是三论宗人观察事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直观思维方式和信仰主义真理观。
四重二谛说以“忘言绝虑为真”,这就涉及了认识领域是否“绝名”的问题。“名”,名言,概念,语言文字。“绝名”,离绝名言,不可言说的意思。名与实、名与理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佛教通常认为表述万物的各种名是假名,但是,无名又难以把万物区别开来,所以又主张对俗谛来说,名不可绝。另外,表述真谛的空、实相、真如、般若,表述佛果的涅槃、常乐我净、寂灭等也都是名,真谛、佛果虽是超名、无名的,但也要先有此类的名,才能去想象、理解、追求、证悟,这样对于真谛、佛果来说,名似可绝又不可绝。这些理论上的困惑、矛盾,一直吸引着佛教学者的强烈关注,他们殚精竭虑,大力探索。吉藏时,佛教界一般认为,就世谛来说,都以为有名可说;就真谛、佛果来说,是绝名,不可说的,有的虽有名说,也是借俗名真,实际上是无名的。但是这种说法又带来了逻辑上的矛盾:如认为是借用世间俗名,那么,名的意义只是世间的,而不是出世间的,也就只是俗谛而非真谛,这是一种矛盾;如果说真谛、佛果所用的名是表示出世间的意义,那么,虽然不是假借,但是不是不可名而是有名了,这又和真谛、佛果的无名说相冲突。吉藏针对当时关于二谛的绝名与否的种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真俗二谛都是不绝名的,也都是绝名的。
他在《二谛义》卷下等文中提出绝有四句——“四绝句”,即“俱绝、俱不绝、真绝世不绝、世绝真不绝”。这是关于二谛言说不言说的四个层次:“俱绝”,世谛不说无生灭,真谛不说有生灭,二谛俱不说;“俱不绝”,世谛说有生有灭,真谛说不生不灭,二谛俱说;“真绝世不绝”,生灭和不生灭,世谛说,真谛不说;“世绝真不绝”,世谛说生灭不生灭,实无所说,真谛无所说而无所不说。这是在有名言中绝名言,由无所不说而悟一切不说。如此不说即说,说即不说,从而获得在二谛的绝名与否问题上的自圆其说。吉藏认为,二谛的绝是不同的,世谛的绝是绝实,绝实有的生灭、是非,真谛的绝是绝假,绝假有的生灭、是非。绝实,绝假,都是为了教人体悟言外之意。吉藏说:“若言二谛俱绝者,真谛绝四句、离百非,世谛亦绝四句、离百非。然此义从来所无,唯今家有也。”(《大乘玄论》卷一)真俗二谛都是绝四句、离百非的,都有绝名与不绝名的两个方面,这确是三论宗的独创性新解。从思维形式的角度来说,真俗二谛的绝四句、离百非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宗教的直观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联系与区别。
三、五句与三中三论宗人讲的教谛是真俗二谛并重的,既不偏于俗谛,也不偏于圣(真)谛,二者合起来讲以合乎中道,洞照宇宙万物的实相。这样合乎中道的观门就是中观。三论宗人把中观学派的著名的“三是偈”中的缘起与性空都看成是假名,缘起的有和性空的无都是假名上说的,由此合成为中道。吉藏还在所著《中观论疏》和《大乘玄论》等书中以二谛和“八不”相结合来阐明中道的新内容,提出了“五句”和“三中”,构成了中观的新形式。
三论宗认为,从“八不”即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的八个方面去体证一切缘起事物的实际,并能在修持中加以正确的运用,就可以达到清净境界。吉藏把“八不”归结为“五句”,如以“八不”中的不生不灭为例,五句是:实生实灭、不生不灭、假生假灭、假不生假不灭、非生灭非不生灭。这五句与二谛相配合,第一句持实有生灭的看法是单纯的俗谛(“单俗”)。第二句持真实的不生不灭的看法是单纯的真谛(“单真”)。
第三句从道理上推论无实生实灭,只有假生假灭,这种看法是以世俗为主显示中道,称为“俗谛中道”。第四句,若认为不生是实不生,不灭是实不灭,这如同实生实灭一样,都是偏见,同样应当否定,所以此句认为生灭既假,不生不灭亦假,这是以真谛为主显示中道,名为“真谛中道”。最后第五句,综合和超越以上二句,认为俗谛中道的假说生灭,应是非生灭,真谛中道的假说不生灭,应是非不生灭,两者相即不离,非生灭而非不生灭,宇宙万有实相就是非生灭非不生灭,这样综合俗谛中道和真谛中道来看,称为“二谛合明中道”。第一、二句是单俗、单真,都是偏见,都不能名为中道,后三句的俗谛中道、真谛中道和二谛合明中道,合称为“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