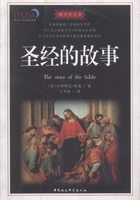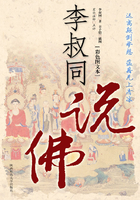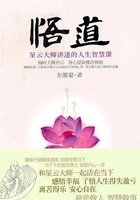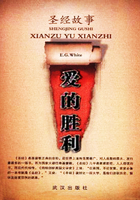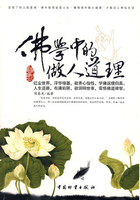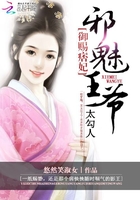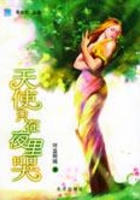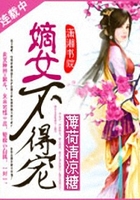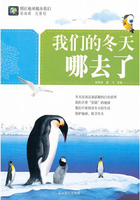小乘佛教为了追求人生的道德圆满和最终解脱,着重应用因果律分析人的构成因素,提出五蕴说。认为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因素构成的,一方面包括了肉体的物质因素,一方面包括了感情、意志、思维、认识即精神的因素。这些因素各有善与恶、染与净的不同道德内容,并按照因果法则不断地流动。人们应当了解这些因素活动的情况,认识到人并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实体,以便控制、减少和停止活动,达到寂静状态,进入涅槃境界。小乘佛教还从五蕴说进一步扩展为十二处、十八界的学说,体现了以人的认识为基点而展开的对人与其他事物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涉及人的认识与人体官能以及外界事物的关系,成为极富认识论色彩的学说。由认识器官攀缘、接触外境而产生认识,即“依根缘境生识”说,是小乘佛教典型的认识论内容。
一、认识的成立小乘佛教认为,人们一般认识的产生在于客观境象对感官的刺激。《中阿含经》卷七《象迹喻经》说:
若内眼处坏者,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眼识不得生。……若内眼处不坏者,外色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识得生。
没有正常的感官和感官感觉的对象,就不能产生认识。佛教的宇宙观是缘起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人的认识也是缘起的,由几种因素形成关系而成立,没有形成关系,或关系离散,认识就不能生起。认识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感官(根)、客观的境象(境)和主观的认识(识)。
如前所述小乘佛教把认识分别为六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这六种识是分别依不同的根缘不同的境而后产生的,由此又有六根和六境,合称为“十二处”,十二处和六识又合称为“十八界”。“处”是生长的意思,生长即指生长识而言。十二处是认识力的十二个根据。《杂阿含经》卷八:“二有因缘生识。何等为二?谓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
虽然小乘佛教对意根和六境的解说有其特殊的含义,但是它强调由根、境二因缘而产生识,是和朴素唯物主义认识发生论原则相吻合的。
后来大乘佛教唯识学者进一步提出,和出世间认识不同,世间认识由三个因素构成,即能认识的“分别”、所分别的“相”以及对所认识的相加之以诠表的“名”。其具体含义是:
“分别”,区别,辨别,指能认识的心。能认识的心之所以称为“分别”,是因为心就是种种认识,而认识不过是种种分别。分别是能认识的心,心有分别认识的作用而无实体,也就是没有永恒不变、常存不灭的心灵实体。
“相”,形相,相状,指所认识的境。为什么把所认识的境称为“相”?佛教认为,我们的认识活动直接接触的只是事物的各种相,如见日月星辰、花草树木,只是见这些事物的形色相状,和这些事物的本体并没有接触,更不能见到。也就是说,事物没有永恒不变、常存不灭的物质实体,只有形相。
“名”,也称“名想”、“名言”,是对相的称谓,即概念、观念。名是分别借以用来表示相的工具,人们对外部事物的形相有了分别,就要对相是什么有所表示、有所称呼,佛教也称之为“诠表”。唯识学者认为,名和相同是心的所变境,而名是相的能诠,相是名的所诠。名在认识中的作用,既在于便于记忆把握,也在于便于与人交流思想,但名不同于所名的物,把名和所名的物等同起来是不对的。
大乘佛教的世间认识三因素说,是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基础上立说的,是为了强调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没有不变不灭的实体。再者,与小乘佛教以根、境、识为认识三条件相比较,“境”称为“相”,又提出“名”,相与名合称为“所变境”,又以了别为“能变心”,原来“根”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降低了。虽然唯识学者阐发“名”即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是有意义的,但是忽视感觉器官的作用,把名和相都看作心的所变境,却是一种理论上的逆转。
二、五根与意根小乘佛教对五根和意根有着独特的分析和认识,对五根和意根的关系也作了细密的剖析和揭示。
小乘佛教讲的五根,相当于五种感觉器官,但严格地讲是指感官中极精妙而不可以肉眼见的细微物质,即分别散布在五官上面的具有某种特性的因素,如眼根不是指眼球,而是指散布在眼球各处具有视功能的因素,相当于视神经,鼻根也不是指鼻子,而是指散布在鼻孔里面具有嗅功能的因素,相当于嗅神经,其他三种感觉器官也是这样。佛教又把根分为正根和助根,称真正具有见、闻、嗅、尝(味)、触五种功能的内在的五官为正根,称外面的五官(如肉眼等)为助根。佛教还把五根分为两类,即以眼和耳为一类,鼻、舌和身为另一类,认为前一类能远取各种外境,后一类则只能摄受与其直接接触的外境,也有的认为前一类能摄受外境无量的细微质点,后一类则只能摄受外境一定量的细微质点。佛教讲的五境是可以感觉的事物,每一个事物都由若干质点、因素所构成,这些质点、因素的性质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影响、作用于五官,如作用于眼的不作用于耳,作用于鼻的不作用于舌,同样,眼根只能看事物的某些质点、因素而不能看别的质点、因素,鼻根也只能嗅事物的某些质点、因素而不能嗅其他的质点、因素,其他感官也都如此。佛教认为,五官所感觉经验的并不是外部的物体和内含的各种性质,而是客观事物的某类因素,如看见黄色的事物,是因为有众多的分立的黄因素刺激眼根的结果,这种黄因素存在于黄色的事物之中,然而又是相对独立于黄色的事物的,人们看到黄色是主观综合黄因素的结果。虽然佛教看到事物的因素如颜色与事物的区别,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它把事物的因素看作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这为导向唯心论埋下了契机。
意根,前面已提到,小乘佛教上座部指肉心,即心脏,小乘佛教其他部派则以前念意识为意根,按照这种说法,意根是精神性的、心理性的,五根是物质性的、生理性的。
关于五根与意根的关系,《中阿含经》卷五十八《大拘罗经》说:“意为彼依。”“彼”,指五根。
意根为五根的依止,五根须依赖意根的执持,才能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物质的生理器官要依心理活动而起作用,如果心理活动停止,五官也就失去取境生识的作用。同时,小乘佛教又认为,没有五根,也就没有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感觉,也就不能显示出意根的存在。
虽然,五根与五境不相接触,没有形成五识时,意根也能生起意识的作用,但是,如果五根变坏腐烂,意根也就不能发生作用。所以,意根也不能离开五根而活动,意根和五根是相依而存在的。此外,意根还和五根不同,具有广泛的摄受作用,“五根异行异境界,各各受自境界,意为彼尽受境界”《大正藏》,第1卷,791页。
。五根分别受取各自的境界,意根则既以“法处”为境界,又以五根所取境界为境界,意根不仅和五根相感交通,而且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意根不仅产生意识,而且还能产生前五识,当五根和五境相接触时,内在的意根就发生作用,引发为五识,产生认识。也就是说,不仅第六识要依止于意根,而且五识也要依止于意根,这样才能产生明确的认识。小乘佛教强调了意根在整个认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视它为一切认识作用的源泉,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三、前五识与意识小乘佛教认为,六识中的前五识各有自身固定的活动区域,即前五种感官只能了知直接在自身面前的与自身相应的对象,并不能涉及其他识的地盘,即只有分摄受性。第六识却不同,它能一概了知全部六种认识的对象,即具有总摄受性。也就是说,前五根因器官不同,所生的识也就只有专属的作用,仅能作用于自己的相应范围之内,其认识的范围是固定的,而意识则没有有形的器官的限定,认识范围很广,不仅对前五根的范围能起作用,即使是超出五根的范围,如过去、未来的事,也都能认识。小乘佛教又把认识分为三种:一是外界对象呈现于面前时的感性认识;二是由现时感性认识而联想过去形成的相同或不相同的感性认识;三是基于感性认识的构思和推理。前五种识只有第一种认识功能和结果,第六识则具有全部三种认识功能和结果。
意识依止意根而产生,前五识也要依止意根才能产生明确的认识,由意根产生的意识也能认识前五识,这样就有一个前五识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两者究竟是本质的不同,还是作用的不同?
也就是识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在部派佛教时代有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种是从认识活动的复合性出发立论,认为由于所依根和所缘境的不同,识有多种。如眼只能对色,不能对声,耳只能对声,不能对色,六根各自认识不同对象的自相,彼此认识的功能作用是不同的,这是多识的主张。
一种是从心识的统摄作用出发立论,认为六识是一心(第六识)向多方面的开展,如眼识是心识住于眼根而发生的认识色的作用,耳识是心识住于耳根而发生的听声音的作用,鼻识、舌识和身识也都是心识住于相关的根而发生的作用,这是主张一识的观点。
前五识各有不同的根,但又依于意根而生起,意识也依于意根而生起,也就是说,六识都依于意根而生起,那么,各个识的生起是同时的,还是有先后的?这又是一个引起分歧的争论问题,主要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俱时起说,认为各种认识只要条件具备,就会产生认识,没有先后次第之分,不必等待一种认识产生之后,另一种认识才产生。认识的产生,不但二识可以同时,三识、四识、五识乃至六识都可以同时产生。如人在同一时间里,既能看画,又听音乐,还闻花香,口含甜糖,摇扇凉身,思索画意乐曲,并没有先后之别。
一种是异时起说,认为认识是次第产生的,只有前一念的认识过去,后一念的认识才能产生,虽然前念后念相隔时间是极为短暂的。
后来大乘佛教又认为既有俱时起又有异时起,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说:
若于尔时一眼识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识同所行转;若于尔时二、三、四、五诸识身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识身同所行转。
这是强调前五识中某一识或各种识的生起,必定有第六意识与之俱起,而第六识生起时,不一定有前五识与之同时生起。
从上述小乘佛教对于人的认识形成的根源、过程、类别等学说来看,是作出了有益的理论贡献的,其中包含了若干合理因素。现代心理学认为,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主动进行加工的产物,在感性认识阶段存在着理性因素的作用,如主体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都对感性认识发生不同的作用。佛教关于第六识对前五识的关系的学说,关于前念意识在思维活动中作用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至于佛教忽视乃至无视思维器官的作用,笼统地把前念意识说成是意根,并由此引出各种唯心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
§§§第四节般若中观论
随着大乘佛教的产生,般若学越来越成为佛教的主导思想。般若,被认为能断惑证真,度化众生,而称为“佛母”,是佛教所谓的高级智慧——一种指导观察一切事物的根本观点,判别是非善恶的基本方法,也是佛教所证悟的最高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和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般若是一种特殊的体证方法和体验境界。
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奠基人龙树,是般若思想的发掘者和弘扬者。他依据般若思想,进一步超越单纯的空观,主张离去“空观”和“实有”二边,以合乎中道,把握一切事物的实相,这就是“中道正观”,即“中观”。大乘中观学派认为,中观是观察一切事物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为了论证中观学说,龙树还提出“二谛”说,作出了真理论的论证。又为彻底贯彻二谛说,还着重破除各种“偏见”,以否定世俗的认识,提倡“现观”即神秘的直观,作为悟解人生宇宙的实相和证入涅槃的方法。
一、般若大乘佛教继承小乘佛教禅观的运思路数,同时又针对小乘佛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主张佛说的法都有自性的观点,强调法无自性,对佛所说法不可执著,由此出现了般若类经典。此类经典影响深远,后来的《宝积经》、《华严经》、《法华经》和《维摩经》等,都是依据《般若经》的般若思想撰成的。可以说,般若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大乘经典的中心思想,般若是大乘佛教的新思维。
般若是梵文Praj的音译,也译作“波若”、“钵罗若”等,意译为智慧。这种智慧不是指普通经验的知识,也不是世俗人所能具有的一般智慧,它是包含各种神通的超越能力在内的、超越知识、超越经验的灵智,是洞照性空,超情启知,达到成佛境界的宗教智慧,是一种宗教的神秘直观,一种成佛的特殊认识、手段。般若,汉语意译作智慧,并不完全符合般若的原意,有的佛教学者用“圣智”来表示般若,而唐玄奘则主张保持梵文音译“般若”。用我们的话来说,般若实质上就是体悟万物性空的直观、直觉。
般若,作为一种特殊的智慧,一方面,只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获得,是排斥世俗认识的。另一方面,般若智慧如果不采用世俗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手段,又无法宣传、影响群众,为群众所接受。因此,为了方便,又承认运用世俗认识的形式、方法作为通达般若智慧的工具、桥梁。这样,通常般若又分为三种:一是“实相般若”,指般若的理体、实性,即是离开虚妄分别相的空性,是体证的境界;二是“观照般若”,指观照实相(性空)的真实智慧;三是“文字般若”,即般若经论表述般若思想的言教,是一种言传的方便。这就是说,般若是以特殊智慧为内核的包含了实性、功能和形式的内容丰富的概念。
从宗教思想方面来看,般若思想的中心内容是阐发一切现象“性空幻有”或“真空妙有”的道理。依据缘起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也就是没有自性的,是空的,是性空、真空;虽然一切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没有自性,但是假有的现象是存在的,幻有、妙有是有的。由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是幻有,但不是无,不是虚无。空不是假空,而是真空;有不是真有,而是假有。般若思想要求对一切现象同时看到性空和幻有两个方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同时般若学还认为,佛经上所说的般若言教也是佛为了教化众生的需要而作的假设、方便:“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波罗蜜”,是到达彼岸的意思,也就是指到达彼岸的途径、方法。这是说佛说的般若也是概念的假设,是“文字般若”,佛说法也是幻有。般若思想就是要求在认识和行为上不滞于现象,排斥对于现象的执著,也就是超越“偏空”和“偏有”的偏见,以把握现象的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