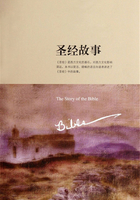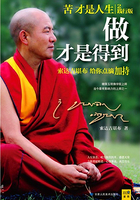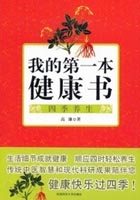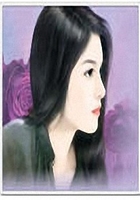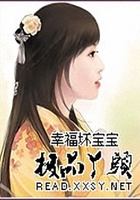§§§第一节真如缘起论
真如缘起论,也称如来藏缘起论,系佛典《大乘起信论》提出的缘起理论。它认为世界万有是宇宙的心(称一如真心,也称心真如)的生起和显现,宣扬三界唯心的观点。这是佛教史上一种颇具新异色彩的缘起理论。
《大乘起信论》题为真谛译,然有人疑为中国人所作。本节论述的若干观点,参照吕澂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见《中国哲学史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不另一一具体注明出处。
《大乘起信论》的内容,是在融合地论师和摄论师的不同说法的基础上,讲论止观的教程。它的理论已接触到佛学的根本原理“心净尘染”,但由于受魏译《楞伽经》误解的影响,却构成了“真心本觉”说。它认为众生的心原是离开妄念而有其体的,可谓“真心”。真心是大智慧光明的、遍照世界的、真实识知的,甚至是具足了超过恒河沙数的不可思议功德的。这个真心就是宇宙的心。《大乘起信论》如此夸张描绘真心的性质和作用,给当时佛教各派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修为方面,当时一些派别都循着它的途径去把握真心,把真心作为总源头,将修为方法看作是可以取之于己,不待外求的,即走上了返本还源的道路。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和印度传统佛教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印度传统佛教认为,众生的心原本就没有清净过,如何由不净改变为清净,这要经过持久的修持,逐渐地改变,才能达到解脱目的。自《大乘起信论》以来,中国佛教学者还将宇宙发生的原理,笼统地联系到真心上面,而有如来藏缘起之说,宣扬如来藏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从而更加深了中国佛教的唯心主义的色彩。
一、一心二门《大乘起信论》的总纲是一心二门说。一心的心是本,是天地之本。一心就是宇宙之心。它是世间和出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的一切现象的本质,也是众生本来具有的成佛的主体和依据。一心既是世界的本原,又是包括一切境界的世界的整体。这样,对一心就可以从实体和缘起、静和动两个方面观察、分析,即分为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
所谓“心真如门”,是说心是宇宙一切现象的本体,具有无量的本有的功德,能产生世间和出世间的善因果。它是“绝相”的,也就是非生非灭,非染非净,无差别相,不动不转,真实如常的。要之,是绝对的本体。所谓“心生灭门”,与心真如门不同,具有体(体性)、相(相状)、用(作用)“三大”。心生灭门包括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是真如本体的相和用。一心之中,为什么具有正反相对的两个方面呢?《大乘起信论》提出真如不变随缘的重要论点来说明,它说,虽然真如是非生非灭、断绝言象的,但是因“无明”之风忽起,使心现出生、住、异、灭四相,随任因缘而生灭,生起内外、染净的森罗万象。心真如门显示心的本体、绝对、无差别的一面,心生灭门则是显示心变现生灭现象、相对、有差别的一面。虽然一切现象随任染净的因缘条件而生起,但是真如本体仍然恒静不动。反过来说,虽然真如湛然不动,但是一切现象仍然生灭不已。生灭不碍真如,真如不碍生灭。没有真如就没有现象,现象不离真如。真如虽显现为现象,但仍保持自身的不变性。真如显现现象,并不是直接生起现象,现象是由外在的无明所生的。
二、真如与无明“真如”,梵文意译,其意义是真正如实的、常住不变的存在,一切事物的真实性质、真实相状。佛教各派一般用以指无生灭、无变化的永恒真理、最高原理、世界本体。《大乘起信论》把所谓先天具有全部佛教功德而又永恒不变的真心当作真如,认为是宇宙一切现象的本原、本体,也是众生得以成佛的主体、依据。宇宙一切属于真如,真如统摄一切。
《大乘起信论》分真如为“离言真如”和“依言真如”两种。所谓“离言真如”,是说远离妄念,没有各种相状,没有一切差别,无言可说,无名可附,即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的。离言真如是真如的本来面目、本来状态。所谓“依言真如”,是说真如虽不可说、不可念,但为了向人们解释真如究竟是什么,使人们产生信解,勉强用名言来诠显其性质,称为“依言真如”。依言真如又有两种意义:一是“如实空”。这是指真如的空性——清净本然的空,也就是真实的真如自体。真如没有虚妄分别的心念,因此也没有虚妄的境界。一切妄念、妄境都空无,从而显示出真如自体的真实。二是“如实不空”,真如自体清净本然,具足无量无边清净本然的功德,所以说如实不空。真如如实不空,就是含藏清净功德,由此又称“如来藏”。如来藏,“藏”是胎藏的意思,有如矿中的金,是矿中的原有的真实含藏。众生具有无量功德,众生本来具有清净的如来法身,为如来藏。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佛性,即成佛的根据。《大乘起信论》对真如的自体即如来藏作了如下的描绘:
从本已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故,自性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名为如来藏。
这是说,真如的根本特征是“自性满足一切功德”,即不由修行而有一切善德。真如的具体特性共有六条,即真如所具有的一切善德展现为六个方面:(1)具有伟大的智慧之德和伟大的光明之相;(2)普遍地广照一切地方;(3)没有妄知,也没有分别识,而有智慧的真实识知;(4)脱离一切染污,没有无明,没有烦恼,自性清净;(5)具有常、乐、我、净四德,即永恒常在,充满欢乐,身具一切佛法,断除一切烦恼;(6)没有妄惑的热恼,没有果报的生灭,清凉不变,圆满自在。由此看来,《大乘起信论》所讲的真如是完满具有佛教一切功德的实体,是一种极高的境界。真如作为佛教道德、智慧的集中体现,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真如不是神灵,不是造物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切众生普遍具有的道德与智慧相结合的精神性实体,是独具特色的神秘实体。
前面讲到,真如湛然不变同时又随各种因缘条件而生起一切现象。随缘也有两种意义:一是“违自顺他”,即隐藏真如自体,显现出种种虚妄现象;二是“违他顺自”,和违自顺他的意义相反,对治虚妄现象,显现真如自身的一切功德。《大乘起信论》强调,违自顺他,生起一切染污现象,就是无明的作用。无明就是妄念,是于不生不灭平等无差别的真如,起生灭差别的妄见,成为不变真如生起现象的缘,即生起一切现象尤其是染污现象的根源。一切现象无非是妄念、妄见的产物。
三、阿赖耶识《大乘起信论》依据魏译《楞伽经》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不生灭的真如和生灭的无明妄念和合叫做阿赖耶识,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阿黎耶识。”如来藏即真如。阿黎耶识即阿赖耶识的异译。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无明是有生有灭的,两者和合成阿赖耶识。由于如来藏为无明妄念所刺激、影响,举体起动,成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是如来藏和无明的混血儿。如来藏是净,是不生不灭,无明是染,是有生有灭。生灭之心,从不生不灭之心起;不生不灭之心,举体起动,不离有生有灭的现象。不生不灭的真如,举体起动为有生有灭的现象。由此可以说,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之外没有生灭变化的现象,又可以说生灭变化的现象之外也没有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就是生灭变化的现象;生灭变化的现象就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两者不异。同时,如来藏虽起动为生灭的现象,但其真性不变,所以,不生不灭的真如与有生有灭的现象,划然有别,两者不一。总之,如来藏和现象是不一不异的关系。由不生不灭常住真心与有生有灭妄心和合而成的阿赖耶识,是为展示一切现象的源泉。这里形成了如来藏和阿赖耶识的交涉,这也正是《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中心所在。
为什么阿赖耶识能够统摄、生起一切现象呢?《大乘起信论》进一步展开说:“此识(阿赖耶识)有二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觉义,二者不觉义。”阿赖耶识因为具有不生不灭的如来藏(真如)和有生有灭的妄心两种属性,从而有觉和不觉两种意义。所谓“觉”,是觉照、觉明,也就是能照见万事万物的真理,觉悟了解真如自体的智慧。所谓“不觉”,是迷妄,是不觉悟了解真如自体的无明。不觉即无明,它由细转粗,千变万化,现出一切妄染的境界。反之,脱离不觉无明,彻底悟证真如自体,就能显现清净的境界。这样,迷和悟,染和净,无一不是阿赖耶识所具有。阿赖耶识是一切现象缘起的总体,宇宙万物的根源。阿赖耶识能统摄一切现象、生起一切现象。
觉又分本觉和始觉两种。所谓“本觉”,是指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觉照、觉明的性德,固有的自性清净心,也就是心体。本觉是就烦恼来说,就心生灭门来说的,如就断除烦恼来说,又称为“法身”,如就心真如门来说,又称为“真如”。所谓“始觉”,是说众生本觉的心源,由于无明的刺激、影响而有不觉,处于迷妄状态,后来由于本觉从里面影响妄心,佛法从外面教化妄心,因而逐渐开始有所觉悟,直至完全契合本觉的心源,融为一体,称为“始觉”。
不觉也分根本不觉和枝末不觉两种。所谓“根本不觉”是指无明的体,是对真如迷惑的无明。所谓“枝末不觉”是指无明的相,是执著虚妄现象的无明。《大乘起信论》还把枝末无明分为九相,以说明真如一心随缘起动的形相,也即由阿赖耶识现出的一切世间妄染境界。真如一心随缘起动生成九相,其中有前后、细粗的区别,分为三细、六粗两类。起初无明为因,生三细。因微细难知,故名为“细”。三细后以境界相为缘,生六粗。因粗显易知,故名为“粗”。三细,第一位是业相,也称“无明业相”。业相是指真如初依不觉无明而动作的相状,开始形成生灭,但主客未分,状极微细。又因是真如依不觉无明起动的最初一念,也叫做“业识”。第二位是能见相,也称“见相”,又名“转相”。“见”,见照;“转”,转起。这是说,依前第一位业识的起动,转成能见之相。妄心既起,转而生成了主观的见照分别一切现象的作用,也称“转识”。第三位是境界相,也称“现相”。“现”是能现一切境界的意思。既然有了主观的见照分别作用,那就能映现出种种与之相应的客观境界。因依前转识之见,起此能现之功,又称“现识”。三细相属阿赖耶识。六粗,第一位是智相吕澂在《〈大乘起信论〉考证》中指出,“智相”的“智”,《楞伽经》原本作“自”,魏译本误写为“智”字,《大乘起信论》据以立“智相”、“智识”说。,也称“智识”。“智”,分别。主观对于现识所现的客观境界,不明了是自识所妄现的幻影,误以为是心识以外的实有境界,不生起智慧,对境界作染净、善恶、是非、爱憎等种种分别。第二位是相续相,也称“相续识”。
这是说,依第一位智相所作的种种分别,于喜爱的境界产生快乐的感觉,于不喜爱的境界产生痛苦的感觉,数数起念,相续于前。第三位是执取相,是说依第二相续相,对于所感受的痛苦快乐的境界,不明了是虚妄不实的,深起取著。第四位是计名字相,是说由于顽固执取苦乐,更在所执取的相上,虚妄计度,立怨亲、美丑、是非、美恶等种种假名。第五位是起业相,是说依前计名字相,寻怨亲、爱憎、苦乐、是非等名,执著更深,从而生起贪、瞋等烦恼,并有言说行动,造种种业。第六位是业系苦相,是说既已造种种相,必招来生的苦果,从而在六道中轮回,生死长缚。这六相属前六识。六相中,前四相是惑因,第五相是业缘,第六相是苦果。
上述三细、六粗,即九相,涵盖一切妄染的境界。《大乘起信论》认为,这一切妄染境界的本原,就是根本无明,根本不觉。一切妄染境界都是根本无明次第生起的差别相。前面说过,阿赖耶识生起一切现象,这里说根本无明生起一切妄染境界,那么,阿赖耶识和根本无明是什么关系呢?两者在生起一切妄染境界方面各起什么作用呢?《大乘起信论》说,阿赖耶识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随缘真如是因,根本无明是缘,两者和合转成阿赖耶识。同时,根本无明作为一切妄染境界的根本,又是生灭的因,色、声、香、味、触等妄染境界诱发起种种妄念,是生灭的缘,因缘和合,生起一切现象。由此看来,根本无明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方面,两者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一切现象的生起,根源于阿赖耶识,而更直接的根源是阿赖耶识中的根本无明。这两个根源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一切现象都是心识的产物,所以《大乘起信论》又说:“三界虚伪,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又说:“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
由此《大乘起信论》又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使本来具有的真如去熏习、影响无明,即以“本觉熏不觉”,从而根除妄念烦恼,灭绝无明,不起妄心,也不起妄境。妄境是无明生起一切现象的缘。无明已灭,妄境缘也灭,这样主客观也都空;同时,由生灭还归不生灭,“从染入净”,也就返归真如,显现真如的本来面目,证得涅槃。
心外的一切现象,一切境界,由妄心(无明)而起,又由净心(真如)而灭,这其间细密而烦琐的论证,体现出极富思辨的佛教唯心主义的特征。
四、真如缘起论的重大影响《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如来藏缘起论)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很大,其中又以将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分为两截的观点影响最大。这个观点与印度佛教不同,是根据魏译《楞伽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