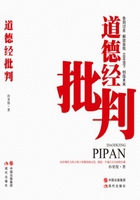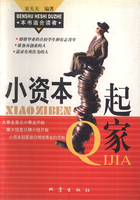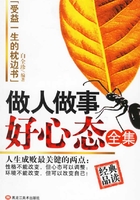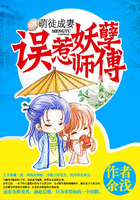咸丘蒙是以《诗》之言来衡量舜之事而提出疑问的。他引《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言,提出舜做了天子,他的父亲瞽瞍为什么不是王臣的疑问。这种提问或者否定《诗》之言不显示义理,或者质疑舜之事不合义理。这种提问方式显示了咸丘蒙观念意识中言、事、理之间的差异与区分,也使得作为文化传统遗留物的《诗》世界呈现出言、事、理等不同层次。
咸丘蒙这种引诗提问的方式与《韩非子》文本相同。在“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的立场上,韩非《韩非子·忠孝》显示出对《诗》的怀疑。
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
在其“仁”、“义”、“明”所表示的义理法则上,《韩非子》此处否定了《诗》之言所能显示的事实与事理。对“普天”之《诗》,“信若《诗》之言也”出现不合忠孝情理之事。舜做了天子,连尧、尧的女儿及舜自己的父母,都当是舜的臣仆侍婢了。被儒家认作经典的《诗》,在韩非心目中其内容正确性是根本靠不住的;被先哲视为贤圣的舜,在韩非看来是“乱后世之教也。……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在这种观念之中,《诗》之言、事、理在《诗》的世界中呈现分离。《韩非子·说林上》文本中还有温人之周引“普天”之《诗》。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温人之周是在言的观念立场上使用《诗》,省略了《诗》之事实、事理的意义空间。从《诗》之言引申出主客之理,这个故事中引用《诗》之言作为一种修辞、巧辩甚至是强辩。在此引《诗》论理,理不在《诗》言之中。这个在《韩非子》故事与《战国策卷一·东周策》文本中相同,成为《战国策》总计四处引《诗》之一。记录春秋之后245年间历史的《战国策》,不但引《诗》数量少,而且其使用《诗》文本的怀疑与修辞立场显示了战国时期《诗》学主流观念。荀子引“普天”之《诗》来说明天子的至尊至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告至备也。天子也者,执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在这里,“普天”之《诗》是作为荀子所论观点的语言材料,所引突出就是修辞用《诗》。以言用《诗》并非不讲义理,而是义理不在《诗》之言中。在《荀子·君子》篇论说中,荀子多用“《诗》曰”、“书云”、“传曰”来总结其论点。因此,理不是《诗》中,《诗》不等于理。“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对于经典权威性的强调,其所关注点并不在经典文本的字面意义上,而是经典的精神及其实践意义。《荀子·大略篇》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所强调的就是对其本质性的把握。他在《荀子·儒效篇》提出:“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其意即在强调礼义的实践意义,而让《诗》、《书》从属于礼义。在“隆礼义而杀《诗》、《书》”立场上的荀子提出:“《诗》、《书》故而不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
引用“普天”之《诗》使用《诗》之事,《吕氏春秋·慎人》篇提出舜自为诗之说:
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
《吕氏春秋》所论显示在事的观念上用《诗》,“普天”的《诗》之言显示的是历史事实,记载了舜为天子之得意之情。而此处的理是论者认识历史事件而提出来的“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义理不在《诗》言之中。《吕氏春秋》在事的观念上提出“舜自为诗”,后世也以新的事实认同来评价这种认识。
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
以上使用中的“普天”之《诗》,或用之言、或用之事、或用之理,但没有一个在言、事、理的统一立场中看待“普天”之《诗》。这种在言、事、理的不同观念立场中看待“普天”之《诗》的方式,不同于《左传·昭公七年》引“普天”之《诗》的观念视野。在《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有:
楚子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之阍入焉。无宇执之,有司弗与,曰:“执人于王宫,其罪大矣。”执而谒诸王。王将饮酒,无宇辞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执人于王宫?’将焉执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宠,未可得也。”遂赦之。
《左传·昭公七年》显示了言、事、理统一的观念立场中凸现出的“普天”之《诗》的意义空间。在无宇这种引《诗》观念中,“普天”之《诗》言记载着“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之《诗》事,显示着“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之《诗》理。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古之制、古之事与古之言相统一的“普天”之《诗》,在《左传》世界中是神圣有效的处理事务、解决争端的法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表示的是神圣有效的经典法则,还是故而不切的历史记载?或是琅琅上口的语言修辞?先秦使用与解说“普天”之《诗》者,现存《左传·昭公七年》、《孟子·万章上》、《战国策·东周策》、《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韩非子·说林上》、《吕氏春秋·慎人》等处。这种论者对其诗句的不同理解,显示不同语境中《诗》的观念以及用《诗》立场与方法的差异。这几处用《诗》呈现了言、事、理的审视“普天”之《诗》不同立场,并表现出从言、事、理相统一到言、事、理相分离的转变趋势。从历史背景来看,这种转变发生在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进程中。
在春秋时代,《诗》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在百家争鸣中,《诗》的存在意义被怀疑了。最为要命的是,百家中除以坚持经典体系、传承周孔之道为己任的儒家学者外,几乎其他各家对《诗》都不怎么感兴趣,甚至出现了反《诗》学的强音。当时活跃于文化、社会舞台的有儒、墨、法、道、名、农、兵、阴阳、纵横等多种流派,但大多著作或已不存,或真伪杂糅,或根本不涉及《诗》的问题,难以细作考究。有籍可案的只有儒、墨、法、道四家,这也是影响最大的几家。而在四家中,就有三家是反《诗》学或基本否定《诗》学的。
用《诗》的变化源自用《诗》文化背景的不同。春秋时期政教统一的文化建构转向战国时期则出现政教分离的文化解构,这种文化转变使得“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诗》由社会制度的操作层面,下落为一种古代知识系统;由春秋前的官方意识形态组成,下野而降为民间思想。
春秋以降,礼坏乐崩,原来王官之学散播民间,出来了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私学和独立的知识阶层。面对当时深重的社会灾难与人民的不幸,这一知识阶层以崭新的独立姿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救世治国方案。《诗》对于他们已不限于酬酢应对的交际工具,而是他们创说立言的文化资源。并在创说立言的同时,也以自己的道德或政治理念对《诗》进行重新诠释或价值重估。
孟子所面对的正是以言、事、理立场的分化用《诗》与多元用《诗》的历史语境。因此,不同立场的人们能对《诗》本身提出问题,能在言、事、理的不同层面上使用《诗》。《诗》的这种历史命运在孟子的视野中呈现出独特面目,《孟子》中“迹熄《诗》亡”命题显示了他对《诗》价值转换的应对立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迹熄《诗》亡”命题显示了《诗》在孟子的知识谱系与思想主题中占居重要位置。历代论者对“迹熄《诗》亡”命题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各种不同的理解显示了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对《诗》的不同认识来印证孟子命题所指的历史事实。不同理解呈现了认定“王”、《诗》、《春秋》关联性关系的共同观念。这种观念在现代被质疑:“即从今天的学科分类角度看,《诗经》是诗歌总集,内容以抒情为主;《春秋》乃史书之属,只是记事。二者亦如风马牛,难以凑泊一处。”
孟子提出“迹熄《诗》亡”命题所涉及历史事实的考证还需推进,但孟子提出命题所建构的意义本身、所显示的孟子观念本身的历史存在也是不容忽略的。孟子把“王”、《诗》、《春秋》绾结在一起,“迹熄《诗》亡”命题展现了《诗》的价值转换历史在孟子视野中呈现出的价值失落面貌以及王道伦理重建的价值选择。“迹熄诗亡”命题一方面反映了孟子以《诗》为制为训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面临着迹熄《诗》亡的历史变化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孟子的观念中,既要坚持“王”、《诗》、《春秋》的意义关联,但又要面对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的历史变化。
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就是王道重建的价值选择与迹熄《诗》亡历史变化的现实应对。这种选择与应对就是在文、事、义的结构中建构了《春秋》的意义空间。所以,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强调“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表述,体现了孟子观念中《诗》与《春秋》共同承载历史的文化功能与褒善贬恶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孟子主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里以文、辞、志的结构建构的《诗》意义空间,在孟子视野中就是等同于“孔子作《春秋》”在文、事、义的结构中建构意义空间。
可以说,在孟子观念中,《诗》与《春秋》同构,孔子作《春秋》与孟子说《诗》同质。以意逆志命题与“迹熄《诗》亡”命题显示建构《诗》之志、《春秋》之义的应对方案。这种方案是在文、事、理分离的观念背景中形成的。
比较《左传》、《孟子》、《韩非子》文本中对“普天”之《诗》的诠释。孟子从普天句中得到的是“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王道之志。这种诠释既不同于《左传》之言事理的统一,也不同于咸丘蒙提问、《韩非子》质疑显示的言事理分离,而是在言事理分离观念前提下,建构志的形而上中心地位,以文、辞、志的等级结构确立《诗》的内在意义空间。
《诗》的文、辞、志与《春秋》的文、事、义等术语,显示了孟子在文、事、理分离的观念上建构《诗》与《春秋》的意义统一与志、义的形而上中心。孟子训导咸丘蒙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的前提就是“是诗也,非是之谓也”。以诗本身为关注对象,确立其自身内在意义,所以在后世视野中被视为先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谓:“是诗也,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以温人之词考之。昔人学于诗书而不能知者固众矣。不然孔孟何以为先觉乎。
因此,可以说《孟子》对“普天”句的独特诠释以及由此提出以意逆志命题,显示了解决其时代《诗》学现实问题的方案。其以志为说《诗》目标,是对现实语境中《诗》价值转换的回应,也是在时代知识观念基础上的应对。
二、交友古人:读其《书》、颂其《诗》,知其人、论其世
面对《诗》的价值转换,孟子确定志的说《诗》目标,建构《诗》的内在意义。但在孟子语境中,《诗》的价值实现需要克服时空隔绝问题。“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显示的文化时空转变,使得《诗》由社会制度操作层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儒者思想观念中的一种古代知识价值系统。“古人所留者,唯有诗书可见”,《诗》呈现在孟子面前是脱离现实政治力量,以文本为载体的知识体系。
咸丘蒙、万章的提问以及孟子与其讨论显示了言、事、理分离的时代观念,在这种分离中也出现了把握言、事、理的不同方式。以言、事、理的不同立场看待《诗》也关系着把握《诗》的不同方式。从使用“普天”之《诗》看,对于《诗》的世界呈现出两种基本把握方式:作为信仰目标式的用而不疑的推行实践,作为客观对象式的论而存疑的知识考察。
“普天”之《诗》作为外交语境中的共同伦理载体,《左传》显示的是推行实践方式,力图用它来解决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普天”之《诗》作为事理论说语境中的历史事件记录,《孟子》中咸丘蒙式提问、《韩非子》质疑显示的是知识考察方式,力求让它经受多种怀疑与拷问。现实语境使孟子失去《左传》用《诗》用而不疑的推行实践的机会,遭遇了咸丘蒙式问《诗》论而存疑的客观考察的危机。孟子以重建《诗》的经典意义为目标,怎样把历史遗留物的《诗》转变为现实经典,把握《诗》的方式成为关键。
把握《诗》的方式,在孟子的语境中称为“为《诗》”、“颂《诗》”、“说《诗》”等。把握方式的多样,在孟子的视野中呈现出“信言”、“固事”与“以意逆志”的不同。孟子提出的“为《诗》”、“颂《诗》”、“说《诗》”这些方式,虽然从现代视野中可以分为创作、使用与阐释不同的方式,但在孟子还没有独立成熟《诗》学观念的背景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到其处理《诗》方式所呈现的整体特征,关注其所显示的为学方式及其人生实践的整体特色。
首先,在孟子观念中处理《诗》的意义重大,“为《诗》”在孟子的视野中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