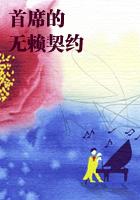“杨叔,你怎么今天来接我了?”莫醒醒背着手包,看到前面向他招手的男人,小跑着上前靠近。
“这不,你妈走了,我就来替她接你咯!”杨树伸手挠了挠莫醒醒过耳的头发,撩起一戳:“小子,该剪头发啦!”
莫醒醒轻拍了拍杨树的宽阔的手掌,撅起了小嘴:“杨叔,看你,都弄乱了我的发型!”嘴上有些不满的说着,嘴角却带着一抹是有若无的笑。
“饿了吧,走,今天杨叔带你吃好吃的去!”杨树说完,将莫醒醒瘦弱柔软的手攥在掌心里。看着这张充满朝气的脸,优良的基因,传承着欧阳锦身上的那股拧劲,只不过,没有她身上的那股强势,不似她那样的冰冷,还好,生了一个让人觉得温暖的孩子。
记得,在医院的病房里,从护士小姐的手中接过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的时候,那一刻,突然地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小锦那样坚持要生下他来!
很可爱的孩子,粉嬾粉嫩的皮肤,有点皱巴巴的,不是很俊俏,但精致的五观,让人看了一眼,就心生出欢喜。
从他呀呀学语……一转眼,都长这么高了,岁月真是不饶人了。前些日子,梳头发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额前的发丝里有着一根晶莹的白发,看着都快长过肩的莫醒醒,杨树的脸上荡起一抹会心的笑意。
莫醒醒微微扬起头,偷瞄到杨树脸上的那抹不明意的欢笑,耸了耸肩,大人的世界,他真的不太懂,妈妈也是一样,不明白她为什么那样拼命的工作,自读书以后,妈妈在他的眼里,就好比一个陀螺,每天都在不停地动转,没有中心,却一直在转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转的,到现在,他都快11岁了,还没有停过,从最初的,常带她到公司,一忙便是一整天,时常他都会饿得直哭,只有在这个时候,妈妈才是温暖的;后来,他长大了一些,家里面配了保姆,而她总是每每带着一身的酒气晚归,很长一段时间里,闻着从她书房里飘散出来的咖啡的味道,他有种冲动想去问问她。
可是,他知道,自己不会,也不能。
空气里弥散着泥土粘稠的味道,欧阳锦独自一人走在去故园的路上,那是阿婆唯一留给她的回忆,当初,母亲改嫁,远走他乡,只剩下她和阿婆两个相依偎着生活。阿婆的年岁大了,而她还刚刚懂事,生活全靠阿婆一个人在外面摆摊,那段时间里,每到看到路灯下,阿婆婆娑的身影,欧阳锦便常常会泪流满面。
那样光景有多久了,记不清了,只知道,后来有一天,街道居委会的大妈突然跑来告诉她,阿婆被送到医院了,等她跑着医院的时候,看见的只是阿婆端祥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欧阳锦不明白,早上还给她盛着稀饭,用她地瘦骨嶙峋的手掌抚摸着她脑袋的阿婆,现在却这样的安静,躺在那里,不会再对她笑,不会再用那如柴般粗糙的指尖擦掉她眼角的泪珠,如果说,妈妈离开了,只是暂时的,那么阿婆呢?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洋洋洒洒地下起了细雨,昨天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里,蔚蓝的云朵,是那样的美,今早一醒来,拉开窗帘,天空灰蒙蒙的一片,J城的天气,总是让人琢磨不定,就像米蔚然一样,虽然是一个弄堂里长大的发小,相伴十多年,甚至于共枕眠,可是,她却仍然看不透他。
每年,欧阳锦都会回一趟J城,去墓陵看阿婆,然后在槐花胡同的那棵老槐树底下,闻闻槐花香,坐一会,这样的每年一趟的奔波,好像已然成了一种习惯,刻进了生命的年轮里,每年圣诞节前夕的那几天,她都会不安,情绪焦虑,失魂落魄的,总想着回J城看一看,呼吸一下那座伤城里宜人的空气,在槐花胡同的绿荫小道上,漫步,好像回味了一番后,工作,生活里的重心又找到了。
娟子曾笑话过她,这是思乡的情愫。
“然子,等等,难道回来一趟,怎么就要走!”慕西追跑着出来,看着米蔚然有些愤然地拉开车门,一溜眼的驶出小区。
烦燥的抽出一根烟,不知道米部长从那里得到的消息,听说欧阳锦回了J城,硬是让母亲打电话催他回家,一回到家,就给他脸色看,嚷嚷着如果不将欧阳锦带回来,就要动用职权,撤他的职。
一想到欧阳锦这三个字,米蔚然便没来得更加烦燥,将车子停在胡同外的小道上,望着那颗槐花树,几个人才能合抱满的树干,小时候,他是胡同里的孩子王,一到夏天的时候,便带着胡同里的那帮发小,爬到树上去抓知了,每当他站在树枝上俯视的时候,总会看见那个闪躲在角落里的身影。
表面一副孱弱可怜的样子,却没有想到,骨子里却是那样的阴险。一转眼,都10多年了,不懂母亲跟米部长是怎么想的,虽然当初他一意孤行,与欧阳锦离婚了,象征性的给了她一笔钱,打发她离开了J城。虽然事后,米部长大发雷霆。
他们之间,一报还一报,互不相欠,只是,如果小雪还陪在他身边的话,那么欧阳锦这三个字,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生命里化作一个不起点的小点,不会再记起。
可是,却没有想到,命运的年轮,跟他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难道非得要他记得欧阳锦这个人吗?
隔着挡风玻璃看到那布入眼帘的身影,米蔚然的瞳孔一缩,将手中的眼蒂弹出窗外,以一个优美的抛物线无误地落入旁边的垃圾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