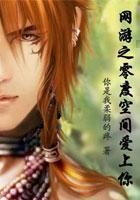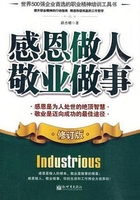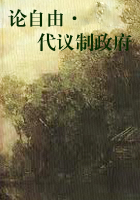山子心里一直想有一支枪,或一把刀。
这是在看过电影《昆仑铁骑》后产生的想法,对电影里的解放军叔叔骑着高头战马,手举马刀,在高原上飞奔急驰,山子非常羡慕,非常向往。
他曾自己用木头做了一把刀,但那刀轻飘飘的,因为又是木头的,太不提情绪了。
还在上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时,也就是初夏五月里的一天,山子去爸爸的邮电所玩。他在山坡上转来转去,看到公社院子里堆了一堆废钢铁。起先,山子从那里走时,并没有太在意。那一堆废钢铁,无非就是破锅、破鏊子、烂镢头、烂犁铧,还有一些生了锈的水车铁链子。
山子走过去玩了一阵子,正要走回来时,废铁堆中有一件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那好像是一把露着半截的长刀。那刀有山子的三指宽,已经掉了木柄,只有一根细细的铁把儿。山子怀着极大的好奇,伸过手去,抓住了那个细把儿,往外抽了一下,但没抽动。刀上面压了不少废钢铁,山子双手握住那个细把儿,使劲儿往外抽了一下。这回,抽出来了一截。啊,真是一把刀!而且,是一把战刀!山子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担心公社的秘书苏叔叔他们出来看见,不让自己拿这把刀。急忙四下里看看,院子里没有一个人。他一双小手握住那锈迹斑斑的刀把儿,哧哧几下,竟抽了出来。哈哈!刀有半米多长呢!山子简直高兴坏了,他把刀竖着抱在怀里,用身子挡着,跑到南瓜地里,摘下几片南瓜叶,把刀包住,绕过废铁堆,出了公社的大门,跑下一个斜坡,然后,撒开双腿,飞快地往村西边的家跑去。
回到家,山子找了块砖头,把刀放在一块长条石头上,浇上些水,就用砖头打磨上边褐色的铁锈。
娘看见了,问:“从哪里拿的?”
山子说:“捡的!”
娘又问:“从哪里捡的?”
山子说:“公社的废铁堆里。反正,被他们拉到钢铁厂,也是炼了铁水。”
娘也没再多问,娘知道儿子爱玩刀玩枪,但儿子在外边从来不惹事。山子是个兔子胆儿,让他去惹事,他也不敢。打架,又打不过人家。
娘只叮嘱了一句:“好生玩,小心手啊!”
山子很脆生地“哎”了一声。
“哧——哧——”,山子磨得很是带劲儿。不大一会儿,一边的铁锈磨掉了,露出青色的刀身来。再把刀翻过来,磨另一面。不一会儿,又磨出了青色的刀身。
山子脑门上的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磨去了铁锈,山子又在磨石上磨刀刃。
现在,山子终于有了一把刀,而且是真正的军刀,真正的战刀。它可能是小鬼子留下的,他们战败了,投降的时候,把刀缴给了八路军游击队。这把刀,是战利品。山子是这样推测的。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山子一边磨刀,一边唱。
刀磨出了刃,山子想试试刀快不快,他找了根手指头粗的树枝,放在地上,用布包住刀把,举起来往下一砍。“嚓——”树枝竟齐嚓嚓地断成了两截。
啊,这刀这么快啊!山子把两截断了的树枝并在一起,又举起刀,往下一砍,“咔!”树枝齐刷刷地断成了四截。
“噢!太棒了!”山子把刀扔在地下,拍着手,跳了起来。
爸爸下班回来,看到儿子摆弄那刀,也问了刀从哪里来的。山子如实讲了。爸爸说:“好生着点儿,别割破了手!”
山子把刀拿给爸爸看。爸爸拿在手上,端详了一番,说:“这是鬼子的一种小佩刀,还不是那种东洋刀。那种刀,有一米多长。只那个把,就有一扎多长。”又长长地叹了口气,“日本鬼子,才不是些东西呢。”
娘也说:“在老家的工夫,有一天我领着闺女去她叔家。那年,闺女才5岁。走到半路上,就听不远处一个劲儿地打枪。是鬼子在那里打靶。可把我吓坏了,领着闺女赶紧往前走。要是那回鬼子拿俺娘儿俩当靶子打,早就没命了。”
爸爸对山子正色道:“玩归玩,但不准拿出去,也不准冲小伙伴们耍。这刀挺快的,听见了吗?”
“听见了!”
刀把太细,没法握,山子就在上边绑了两块木片,勉强能握住。山子还用娘打袼褙(音
,用旧布和碎布加衬纸贴成的厚片,多用来做布鞋)的浆子糊了个纸刀鞘,又在刀鞘上糊上了锡箔纸,把刀装起来,又用根绳子拴住,挂在腰带上。他虽没拿到街上去跟小伙伴们玩,但还是忍不住在胡同里转了几圈。
一天,住在后院的杨七大爷看到了山子腰上挂的刀。杨七大爷很喜欢山子,他拿过那刀看了看,说:“来,小子,我给你做上个刀把吧!”
山子一听,简直太高兴了。回家跟娘说了一声,就跟着拎了马扎子的杨七大爷去了后院,来到了他的屋门口。
杨七大爷独身一人,没有老伴,无儿无女。高高的个子,腰背挺得很直。头发花白,下巴上有一些半长的花白胡子。杨大爷虽是一个人,却过得挺快活,他很会拉呱,也就是讲故事,他的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大伙都很爱听。每到夏季晚上乘凉,大门外就坐了十几个老汉、老太太和孩子,听杨七大爷津津有味地讲故事。有的人叫他故事大王,有的人叫他故事篓子。
杨七大爷住在一间长条石屋里,门口摆了个用泥做的烧柴禾的炉子,上边放了一只铁锅。杨七大爷的手很巧,那炉子做得像个元宝似的,很好看。杨七大爷进屋拿出来一块白铁皮,几块细木板,又问:“小子,你家有铁丝吗?”
山子说:“有。”就飞快地跑回家拿来一团旧铁丝。
杨七大爷先用一把剪刀把铁皮剪成了个刀把的护腕形,用锉刀把毛边锉掉,以防划手。又在中间凿了个长形的孔,把边往里卷了卷,套在刀把上。再把两块木条锯得一样长,用铁丝缠在刀柄芯上,使钳子拧紧。还把铁丝头别到木板缝里去,以防扎手。他握住刀把端详了一番,说:“唔,有个刀样了!”就递给了山子。
山子高兴地接过刀来,果然握着得劲儿多了。忙说:“谢谢大爷!”
杨七大爷也挺乐呵地说:“回去再找点儿布,把刀把缠一缠,省得木板子硌手,也不好看。”
“哎!”
虽然,它比不上《昆仑铁骑》中解放军战士高举的马刀,也比不上电影《战火中的青春》里那个雷排长的战刀,但总是像个战刀样儿了。
山子挎着刀得意地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冲几个男孩女孩显摆了一番。
这天,山子趁娘不在家,拿了刀来到西边赵三哥家,找到院子中的那块大磨石,又哧哧地磨了起来。
赵三哥瘦瘦高高的个子。他比山子大三四岁,是山子家搬到村里后认识的。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赵三哥只上了三年学就下了学,每天背个条筐去山上洼里割草,每次都用镰把儿背回来沉甸甸的一大筐青草,交到生产队的饲养棚喂牛。一大筐草,也就记一分工,顶多一分半工。赵三哥往筐里装草的技术很棒,一只浅浅的条筐,他能装进去三四十斤青草。那些草往外扎煞着,煞是好看。山子常跟他去西大洼割草。山子割的草,可以晒干了给娘烧火摊煎饼用。夏天的青草割回来,晒干了就剩不下多少了。娘说烧饭用它不顶事,没烟火,但山子还是跟三哥去割草,主要是想跟他出去玩玩。割草时,还捕一些蚂蚱,大的让娘给炒炒吃,或自己在炉子边上烧着吃,小的就喂了鸡。有一回,山子在一条绿草丰茂的沟里捕了足有一百多只蚂蚱,拿回来喂鸡,母鸡公鸡们一口一只,吃得可香了。一只母鸡抢吃了一只,另一只母鸡没抢到,就狠狠地啄了人家一下。山子心里不平,过去用手掌打了那只啄人的母鸡的背一下:“叫你叨人家!”打得那只鸡惊叫着跳了起来。
三哥也乐意山子跟着他,正好有个伴儿,在一块儿说说话。由此,山子跟三哥学会了磨镰刀,学会了往筐里装草,学会了给草打捆。认识了许多的草叫什么名字,也认识了许多野菜叫什么名字。还知道了好些农户家的情况。漫漫西大洼里,青纱帐里,时常就他们一大一小两个半大的男孩子。三哥因整天在外边割草,晒得脸、脖子、手、胳膊都黑黑的。山子常跟着他出去,很快也晒得黑黑的,看上去跟山村孩子没什么区别了。
三哥虽上学不多,但很知礼节,很懂事,把山子当自己兄弟。每当有男孩子挖苦山子,他就出来护着。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又说山子是“吃国库粮的寄生虫”“小地主崽子”。三哥把眼一瞪:“你小子吃饱了撑的吗?狗咬吕洞宾吗?人家吃国库粮的,碍着你什么事了?你有本事也去吃呀!”
堵得那个孩子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一个男孩说山子:“你大大凭什么拿那么多工资?每天光扒拉扒拉算盘子儿,卖几张邮票,就拿五十多块钱吗?”山子不敢反驳,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的确,爸爸的工资不但在公社里最高,在全县邮电职工里,也排在前头。
三哥却不乐意了:“哎,野孩子!咱别‘崩没根儿’(瞎说)!你让你大大也去扒拉扒拉那个算盘试试!他会珠算的加减乘除吗?他会发电报吗?他会英语吗?光眼红人家有什么用?就你这个熊样儿,在班里老坐‘红椅子’(得2分)。有本事,也跟俺山子兄弟一样,拿个第一回来!”
山子心里实在感激三哥,越发和三哥亲了!
磨了一阵子,山子用大拇指试了试刀刃,嗬,有的地方,比镰刀还要快呢。
三哥过来,接过刀,也用手指试了试刀刃:“是挺快!这钢挺好啊!”又说,“兄弟,千万别冲着人玩,听见了吗?”
山子点点头。
山子在家里墙上楔了个钉子,给刀套上刀鞘,挂了上去。平时,刀就挂在那里。没事时瞅瞅,心里就美得不行。
然而,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把刀,让山子闯了大祸。
秋收的季节到了。
爸爸开的荒地,南瓜早已收完了。玉米的棒子都掰下来,送回家了。娘挑了一些嫩的煮了。那鲜嫩的棒子煮熟了,好吃得很。见有一些玉米秆竖在那里,山子就想起自己的战刀来。星期六下午,他把刀带到了山上的邮电所,在营业室门口对爸爸说:“爸爸,我把那些棒子秸砍了吧?”
爸正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忙着工作,没顾得上跟儿子说话,连头也没抬,就说:“行啊!”
山子进了玉米地,从纸壳的鞘中抽出了那把战刀,像电影上的骑兵一样,把刀抡圆了,冲一棵直立的玉米秆“嗖”地一下挥过去,“嚓!”玉米秆断了,然后,慢慢地倒在了地上。嘿!太痛快了!太过瘾了!
山子边砍边大声唱起歌来。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它山高水又深……
一连砍了十几棵之后,山子发现有的玉米秆还比较绿,就拿起一棵,咬了咬砍开的新茬。有的挺甜,就多咬几口,咂咂里边的甜水;有的咬咬,干巴巴的,没滋没味儿,就扔在了一边;还有的,虽有水,但寡淡无味,就“噗”地吐了,再把秆子扔在地下,上去一刀,砍成两截。再下去两刀,成了四截。
这时,山子看到身后七八米远处,有一个小女孩,也就五六岁。大大的圆圆的脑袋上扎了一对翘翘着的朝天辫儿。又白又嫩的圆脸,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很是可爱。她是公社社长的女儿。山子家搬走之后,山子只见过她两次。半年多没见,小丫头长高了不少。今天,可能是她爸带她到公社来的。公社的不少人在一间屋子里,好像是在开会。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山子不知道。她家里兄妹几个,山子也不知道。小女孩好像知道玉米秆儿味道不错,捡起山子砍下来的一棵玉米秆,用雪白的小牙去咬。
山子热心地说:“哎,那棵不好吃!牛才吃那样的呢!”就把刀往地下一插,找到刚才尝过的一棵甜的玉米秆,把自己咬的那一截掰了去,递过去。小女孩接过去,咬了一口。山子问:“甜吗?”
小女孩望望他,不说话,却直点头。
山子说:“那你吃吧!”又说,“哎,你就在这儿吃,别过来!”山子怕自己砍玉米秆,会伤到这个小女孩。
山子走到前边,抡起战刀,继续他的“讨伐”。偌大的院子里,就一个十岁的男孩,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嚓!”一棵;“嚓!”又一棵。哈,一个男孩子在这样的“战斗”中体会到一种难言的快意。
前边,玉米秆已经不多了。
山子再次抡开了战刀,“嚓——”又砍下了一棵。就在他把刀从右抡到左,向左边扭转身子的一刹那,发现大事不好了。小女孩就站在他身后不到一米的地方,收刀已经来不及了。刀尖从小女孩的额头前划了过去。女孩的身子往后闪了一下,额头的右侧立刻出现了一个大口子,鲜红的血顿时涌了出来,顺着额头、眉毛、眼睛流了下来。而小女孩什么时候来到他身后的,山子一点儿也没察觉。
小女孩哇哇大哭起来,用胖胖的小手去抹额头,抹了一手鲜血。女孩更惊恐了,放声大哭。哭声在宁静的公社大院上空声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