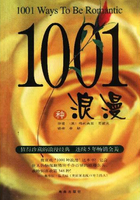我们离婚了。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我只想一个人到海边或是没有人的什么地方走走,但是梅梅太小,我又不想把她托付给别人。妈妈那儿我也不想去,虽然那是我最可以放松的地方,但我怕那样我会成为彻底的弱者。早晨,我把梅梅送到幼儿园,自己便坐在床上看书。以前为了幸福而忙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现在沉浸在书海中,为那些各色各样的人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感动,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原来一个人的日子也不错。
一星期以后,我已经相当平静。真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坚强。我决定回海滨小城,回到那个我生活了20年的地方,尽管我知道这很难很费精力,但我无法再呆在这座不属于我的城市了。我动用了自己所能想到的人际关系,半年以后,带着女儿回到了妈妈身边。
我在小城的电视台做编导,这是我曾经很向往的职业,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算命的说我有才华有潜力,直到此时有了应验。我做的节目先后上了市台、省台,并连连获奖。
我不太和旧时的同学联系,只有两三个好友偶尔通通电话。她们无一例外地为我惋惜:“你们俩可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啊……”我笑笑,没有说话。他已不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吗?
小雨是我在那座陌生城市里最知心的朋友,她一直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他的信息:他并没有和叶桐结婚,不知为什么;他不太写稿了,报纸上很少有他的名字;最近在同学聚会时看见他,瘦得不行,而且咳嗽得厉害,脸色蜡黄。
这是我们离婚的第三个年头。梅梅经常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我哄她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像电影上演的那样。以前听到这句话我总要笑,想想也真是那样,他离我们的确很远了。
在我过完30岁生日的第二天,小雨打来了电话:“宏明得了癌症。”我的脑袋“嗡”了一下,声音不由地抖了起来:“什么时候?”“他好像早就知道了,我们去医院看他……他挺想你的。”我的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所有的伤心、怨恨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去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天晚上,我就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见到他,从相识到相恋的一幕幕在脑海中一点点浮现,那我曾经以为忘却了的情感不断汹涌而至。我这才发现,我爱他已经到了无法忘却的地步,即使伤心失望,也只是把他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一旦这种情感被唤起,它所产生的震撼力我几乎无法承受。
我找到了他所在的那家医院。推开病房门,屋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在睡觉。还是那副睡相,全身蜷成一团,紧紧抱着被,神情安详得像个孩子。我把被拽过来替他掖好,他一个激灵坐起来,惊恐的眼神一如从前。看到我,他愣了愣,眼圈一红,把头深深地埋在我手间。好久,我们谁也没说话。
我想起了从前我们如胶似漆的时候,两个人都隐隐担忧而谁也没说出口的那句话:“我们这么好,会遭天妒的!”我想起了开玩笑时他说的“将来我死了,不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死在你的怀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吻着我的头发,“珊儿,珊儿,你肯来陪我了,你不生我气了吗?”我泪眼婆娑地望着那双修长的手,心中悲痛欲绝:假如有来生,假如有来生多好啊,我一定要再做他的妻子!
我陪宏明呆了10天,我们一起回忆从前,一起唱歌,讲梅梅小时候的趣事,我们更多的是依偎在一起——然后宏明就去了,他说:“抱紧我……”
我欲哭无泪。他把无尽的思念和悲伤留给了我,然而这次我却无法坚强。
回到小城,我虚脱似地躺了一个月。叶桐寄来一个大包裹,并附了一封信:“珊姐,对不起,我让你伤心了那么久。我早就想告诉你真相,可又怕违背了宏明的一片苦心。就在我们那次见面前,宏明找到了我,他说他得了癌症,没有告诉你,怕你担心。他说想和你离婚,这样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太苦。我说那样你会伤心的,他说伤心就伤心吧,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就演了那场戏,你走之后他也哭了。以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说你,我让他去找你他却不肯。珊姐,我从来没见到过这种感情,我太羡慕你了。叶桐。”
包内是宏明几年来写给我的没有发出的信。我流着泪一封封地读着,几乎两三天就有一封,有时一天有好几封。宏明向我讲着他的孤独、痛苦和思念……“珊儿,你还恨我吗?你知道我多不愿看到你流泪,可是我没办法。我不愿死,我还想在春天的时候和你带着梅梅去放风筝,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有了。我只希望你带着梅梅好好地过下去。”宏明的话一直响在我耳边。
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谁取代宏明了。
Δ我西双版纳的爱断情伤
【兰湄】
这里展示的是一位女主人公口述的一个家庭的悲惨故事……
曾经相亲相爱过知青岁月
我和郭俊达是七十年代初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认识的,那是1972年,我从上海初到西双版纳时,还是一个17岁小姑娘。郭俊达是比我早一年来的上海知青,那时和我分在同一组,他见我的手被锄头磨起了血泡,就常帮我。我心里很感激他,把他当大哥哥看待。
郭俊达是大学教授的儿子,说话文绉绉的。一有空他就捧着一本书读,蚊子旱蚂蟥叮在身上他也不顾,有人就叫他书痴。
而正是这个书痴却救过我一次命。那天,我们在用大砍刀砍一片很密的杂草。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条毒蛇,在我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郭俊达从不远处急忙跑过来,从衬衣上撕下一片布条迅速缠住我的手臂,他顾不得有感染中毒的危险,又用嘴对着我的伤口将毒液吸吮出来。然后,他又抱着我飞快地向寨子里的医疗点跑去……
在第二年四月傣族的泼水节,在狂欢的人群中,我也戏耍着把一盆水泼到了郭俊达的头上,用傣族青年泼水传情的方式表达了我对他的爱情。
1978年,我们双双从西双版纳直接考上了南方一所名牌大学,郭俊达学的是法律,我学的是中文。毕业后,他分在了检察院,我留在学校里教书。我们很快结了婚,一年后我剖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美满的三口之家。
1986年,丈夫又考取了法律系研究生。在重返母校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拿到了律师执业证。硕士毕业后,他就与朋友一起在本市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因为他谙熟法律,又敢于仗义执言,他的律师事务所很快声名大震,许多单位和个人争相找他帮忙打官司。
随着他事业上的成功,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两年后我们有了四室二厅的住房,还有了一辆桑塔纳车。我在大学里也很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常驾着车去郊游,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
移情别恋后的婚姻蒙上了阴影
我一直以为郭俊达是一位对家庭十分负责任的忠诚的丈夫。尽管有时他的一些行踪也引起过我的怀疑。像有时我给他洗衬衣时常嗅到香水的味道。有一次我在他的西服上还发现了几根长头发。我想他在外面的应酬很多,难免会有陪酒的小姐与他逢场作戏一番,这在他处的那种环境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然而,1995年3月的一天,我发现了丈夫隐藏了很久的婚外恋情。那天下午,我讲完课后骑自行车去市青少年宫,去接在那儿学踢足球的12岁的儿子。经过一座公园时,我突然看见丈夫的汽车停在门口。我想正好可以叫他和我一起去接儿子。我停稳车,就向公园内走去,刚绕过花坛时,我就看见了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我的丈夫正和一个女人在油棕林间的石椅上亲热地拥抱着说话……
我的头脑里像马蜂炸了窝似地嗡嗡直响,血一下子涌上了脸颊。我转身跑出了公园。在打开自行车锁时,我觉得应该冷静一点,也许我看花眼了。正在我疑惑时,我却看见郭俊达和那个年轻女人肩并肩地出来了。
丈夫看见了我,他有些尴尬地替我们作了介绍,他掩饰着说:“这是我的当事人曼妮,一个从西双版纳走出来的傣族作家,她找我帮她打一本书的官司。她嫌办公室里太吵,所以就约我在公园里谈。”那个留着黑缎似的长发的女人就站在他的汽车旁,用一种含笑的目光友好地看着我。她的身材很好。在她说了一句“你好”之后,我迟疑地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纤细的手。
我觉得不能让郭俊达在这个女人面前失了体面,就轻描淡写地对他说:“我去接儿子,你下班后早点回家吧。”他带着那女人开着车子一溜烟走了。我心事重重地踩着车,在过十字路口时差点撞上了一辆运石料的大卡车。
傍晚,我和儿子回到家里时,丈夫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我们了。
吃晚饭后回到卧室里,他急切地向我解释说:“曼妮很可怜,她一开口就眼泪汪汪的,我没有办法稳定她的情绪,她把我当成她惟一信赖的人,所以……”“所以你们就抱在一起。”“不,是她扑在我的怀里的,我没有办法拒绝她!”他一脸无奈地说。我知道丈夫是个挺会怜香惜玉的男人,我决定原谅他这一次,只是,我说:“我希望你不要跟那个女人太亲近了!”他含混地说了一句:“你放心吧,官司一打完,我就不再与她来往。”
身染恶疾,幸福随风而逝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它背后潜伏的阴影却在扩大。我没有发现丈夫继续与那个叫曼妮的女人来往。然而,我却发现丈夫越来越消瘦,并且时常莫名其妙地头晕、发烧。他也借口工作忙,常在律师事务所里睡觉,即使回家也通常是在深夜。
今年五月的一个周末,下着瓢泼大雨。那天儿子去同学家参加生日聚会去了。丈夫很晚才回来,而且他显然喝了很多酒。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抱着头一言不发,他的身体却在不住地颤抖。我走过去扶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怎么啦,你病了?”他抬起头,我看见他深陷的眼窝里积满了泪水,我心里一惊,问:“你这是怎么啦?”他低下头,喃喃地说:“对不起,我得了,得了不治之症。”我摇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可能只是工作太累了!”可是我的眼泪却涌了出来。
他从公文包里慢慢拿出了一张纸。我接过来,一看,那是一张血清抗HIV抗体的血液检查单,它清楚地表明了丈夫是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我只觉得眼前发黑,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绝望抓住了我的心。他慢慢地向我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的正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曼妮。她找我的丈夫打官司之前,曾和她的摄影师丈夫在澳大利亚居留过半年,在那里她丈夫与一个美国的女记者发生了一段恋情,而那个女记者实际上是一个艾滋病人。曼妮的丈夫后来抛弃了曼妮。
曼妮只身回国后,又碰到了一件令她痛苦万分的事情:一家出版社未经她的同意,趁她出国时,在她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随意添加了许多淫秽不堪的内容,而且以裸女做的封面也极其庸俗。她觉得她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所以她请郭俊达作她的律师起诉那家出版社的非法侵权行为。
在与这位女作家多次接触的过程中,她自由浪漫的生活风格和艺术气质吸引住了郭俊达,她也喜欢上了郭俊达。他们曾多次同居。在他帮她打赢了官司的那一天,她还要他带着她去海滨度假……回来不久,她就开始发烧、消瘦,开始以为是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直到去查血时才知道是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她通知了郭俊达……
丈夫流着泪用拳头狠狠地捶着头,追悔莫及,我的心也像刀剜一样难受。我所爱的丈夫不仅背叛了我和家庭,而且还染上了致命的病毒。
当他嗫嚅着劝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从他的身边逃开,将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发疯般向他身上扔去,愤怒地尖叫着说:“你给我滚!”他坐在沙发上一点也不避让。当那只青瓷茶杯在丈夫头上砰的一下,在地上摔得粉碎时,我看见一股殷红的血从他的额头上渗出来。
我吓呆了,心痛万分地跑过去想揩掉他头上的血。他躲开了,说:“我没事的,你别碰我!”我一下子倒在他的怀里痛哭起来:“我不能没有你呀!”
我现在才觉得我多么深爱着我的丈夫。我仿佛绝望地看见像吸血鬼一样的艾滋病毒在丈夫的血液里怎样疯狂地吞噬健康的细胞,侵入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然后把一切的免疫系统捣毁殆尽,让更多的病魔长驱直入……
第二天,丈夫开车送我到了另一座城市的医院,那里没有人认识我们。在血液检验室里抽了血之后,我们又驾着车回去了。
我的生命在黑暗中飘飞
在等待取结果的一天下午,我问丈夫那个女人的情况怎么样了,他说她的病已经发作了,可能就要死了。我突然生出想去看看那个女人的念头,丈夫默默地开车带我来到了人民医院。
在传染区病房的隔离室里,我看到了那个叫曼妮的女人。她已完全丧失了我第一次看见她时的美丽面容,像一片夏天的树叶在秋天里枯萎,她脸上布满了可怕的紫斑,骨瘦如柴,浑身皮肤溃烂,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她因为高烧已经神志不清,极度痛苦地呻吟着……我逃了出来,直想呕吐。丈夫扶着我回到了车里,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一点也恨不起来那个将病毒传给我丈夫的曼妮了,我只觉得她是那样的可怜,生不如死,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啊。我的丈夫也会变成她那个样子吗?假若我染上了病毒呢?我在温暖的阳光下觉得不寒而栗,欲哭无泪,我的生命开始在黑暗中飘飞,再也找不到可栖息的家了。
在取结果的前天晚上,丈夫彻夜未归。我等他到快天亮时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我发现桌上压了一封信和那张化验单。原来他昨天下午开车跑了三百多公里去取化验单,并连夜送了回来。我颤抖着手拿起那张化验单,我的血清抗体呈阴性,也就是说我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有些悬着的心刚放下来,可是我马上又被丈夫留给我的那封字迹潦草的信给吓住了。他在信里写道:最亲爱的兰湄:
我不能想象你面对一张化验单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好像等待死亡的判决书一样。所以,我去给你取回来了。所幸你没有染上我身上的那种瘟疫。我真的爱你,可我不敢再介入你和儿子的生活。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你和我们的儿子却还拥有这个美丽的世界。我希望你们要好好活着,也是替我活着。
我不希望你们看到我发病时的恐怖景象,我也不能再害你们了,所以我选择了逃避,我想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逃到惩罚和死亡再也找不着我的地方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我只希望下辈子,如果我们还做夫妻的话,我们一生一世纯洁地相守相伴。我总回想起你在西双版纳时留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模样,那时我们多么幸福啊!多想想我们过去的幸福吧,好好活着,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求你别对他提我染病的事情,永远都不要提,好吗?
活着多好哇!有阳光、雨水和各种活跃的生命。你忘掉我吧,好好把握和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永远爱你的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