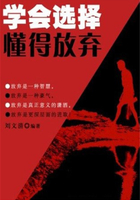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已经创造了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这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不仅使楚国在东亚领先打开了铁器时代的大门,而且使中国冶炼可锻铸铁的技术领先于西方约1700年。当时西方冶炼的是锻铁,用途不如可锻铸铁广泛。楚国制作了大量铁器,但主要是农器和匠器。至于兵器,通常仍用青铜制作,但钢剑也已出现。
这时的青铜兵器有以下三个发展趋向:其一是戈、矛、戟越来越精了。戟原由一戈一矛合成,这时楚国已有双戈戟和三戈戟,可能是向吴人学来的。其二是剑越来越多了。楚墓如墓主为男性,多随葬兵器。江陵发掘的一些小型楚墓。各随葬铜剑一件,而其他兵器无所见。其三是出现了弩机。当时在平原上作战,仍为车兵与徒兵混合编队。随着剑和弩的逐渐推广,徒兵的作用逐渐增大了。
中国的铜镜出现得很早,可是直到春秋晚期还很少。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楚国的铸镜业逐渐兴旺起来。铜镜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以及款式的更新,都相当迅速。迄今已有的先秦铜镜的发现地,绝大多数是楚镜。贵族之家固然必有铜镜,一些平民之家也有了铜镜。铜镜是梳妆用具,它的普及也反映了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和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楚人的文字是先后向殷人和周人学来的,但有楚式的风格气派。
这时,笔画扭曲的“虫书”和附饰鸟形的“鸟书”已近乎绝迹,但铭文仍有字体较修长和笔画多波折的传统特色。墨书因毛笔的推广而增加,多见于竹简,字体较方正,笔画较简省,包含着隶书的萌芽。据文献记载,秦代蒙恬始造毛笔。但从战国楚墓中,已有多支毛笔出土,可见旧说不确。迄今已有的先秦毛笔,无一非楚笔。从考古资料来看,毛笔应是楚人发明的。
这时,楚言已经成为夏言(雅言)的一种方言。但与楚字相比,楚言的特色尤为鲜明。楚言夏化是楚人夏化的重要因素,它使楚人的族属变换了。吴人跑到郢都去大闹了一场,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夏和楚认同了。从此,楚人不再是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的“蝙蝠”,而已厕身于“诸夏”和“上国”之列了。
(第六节老子与道家
昭惠时代是楚国思想界的早春二月。大约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同时,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孔子名丘,字仲尼,是鲁籍宋裔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号老聃,是楚籍陈裔人。儒家代表了北方的学术主流,道家代表了南方的学术主流。当时所谓南方,是含淮北在内的。
说老子就是号为老聃的李耳,这还不是全无疑点的定论。春秋战国之际,被称为“老子”的学者不止一位,可能有两位甚至三位:
其一为周守藏室之史李耳,其二为老莱子,其三为周太史儋。司马迁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苦于不易分辨,三者并存之。后人通常以为,著有《老子》其书的老子其人即李耳。
李耳与老莱子,至少有五点相同或相似之处:第一点,他们都生活在春秋晚期,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而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第二点,他们都是楚人。老子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第三点,他们都号为“老子”。第四点,孔子对他们都尊之为师。“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第五点,他们都著有道家之书。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李耳与儋,相同或相似之处不下四点:第一点,生存年代都在战国早期。苦县原属陈国,公元前478年才并入楚国,事在孔子去世后一年。李耳若为楚人,则必生存于战国早期,不得见孔子。儋曾谒见秦献公,事在公元前374年———即孔子去世后105年,生前更不得见孔子。第二点,显然同名。李耳字聃,“聃”与“儋”音义俱同。第三点,可能同官。李耳为周守藏室之史,儋为周太史,两职似为一职。第四点,都曾西行入秦,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周本纪》和《秦本纪》以及《庄子·寓言》等。
虽说老子有三位,其实大概只有两位:第一位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全称应即老莱子,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第二位是战国早期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或作“儋”,曾仕于周为太史,其专职为守藏室,发展了老莱子的学说,把老莱子的遗著改写为分作“道”、“德”两篇的《老子》。
老莱子乡贯不明,相传晚年隐居蒙山,其地在今湖北荆门。归隐之前,曾在楚国的北境居住,从而孔子有幸向他请益。战国中期的道家对此尚有近真的传闻,以为老子是南方人。《庄子·庚桑楚》
记庚桑子对南荣趎说:“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趎从其言,带着干粮上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这个老子既然在南方,那就一定是老莱子了。《庄子·外物》记孔子见老莱子,说是事出偶然:老莱子的一位弟子出门打柴,遇见孔子,回去向老莱子报告,老莱子派这位弟子去把孔子叫来的。《战国策·楚策》记:“或谓黄齐曰:
‘……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太平御览》卷915引《庄子》佚文,记老子赞孔子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以凤喻圣贤,是南方的楚俗。孔子也曾赞老子,喻之为真龙,事见《礼记·天运》。以龙喻圣贤,是北方的夏俗。闻一多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智哉斯言!
儒学和道学,大致说来,前者盛于北方,后者盛于南方。说得更加准确一些则是,前者盛于黄河中下游,后者盛于淮水流域和长江中游。战国中期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及其弟子,认为道家集中在南方的楚国。《庄子》一书所记有道家思想的人物,除了子虚、乌有之辈而外,几乎全是楚人。据说,楚国的一些农夫也有道家思想,如《庄子·天地》所记子贡在汉阴遇到一位种菜园子的老农,“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建议这位老农改用桔槔以提高工效,不料被这位老农劈头盖脸地指责和嘲笑了一通。这位老农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位老农所讲的,全是道家的理论。当然,这是战国中期的道家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它用夸张的艺术形式显示了道家学说流行于楚国的史实。
楚国本来盛行巫学而兼用杂学,巫学是楚人的传统学术,杂学是指楚人所能搜集和研习的外来学术———即“《书》、《志》、《记》”
等以及南方的周人如随人季梁的学说。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的科学如天文、历算、地理和医药等等,有原始的哲学如道学的萌芽,有原始的艺术如诗歌、乐舞和美术,有神话、传说和信史,当然也有巫术、巫技和巫法。除了楚国,还有陈国和宋国也盛行巫学。就宇宙观来说,道学其实导源于巫学。巫学朝着理性化、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便是道学。促使道学成长的,是楚国变弱为强的历史经验和以寡驭众的社会状况。
《庄子·天下》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个太一就是从楚人崇奉的星神太一脱胎换骨而来的,被道家抽象化、理念化,成为宇宙的本体了。
从社会背景来看,《老子》一书痛切地反映了楚国县民的认识和愿望。县民本来不是楚人,他们是在故国沦亡之后才隶于楚籍的,老子也是这样的县民。县民之中,贵族和平民都有。他们深怀黍离之悲,对祸福的倚伏有真切的体验,对鬼神的笃信则容易幻灭。他们希望楚国的君臣少去触动他们原有的社会结构,少去打乱他们原有的生存方式,最好是因其故俗听其自然。《老子》主张管一个大国,要像煎一条小鱼那么细心。人们常说道家出世,这对道家本身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若不遁于野,则必隐于朝,对功名、利禄、珠玉、声色之类无所萦心,对贵贱、进退、得失、荣辱之类无所介怀,只求保全自己的赤子之心。可是,道家的出世并非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对时务和世态并非无所臧否。道家冷眼看世界,但怀着一颗深埋潜藏的热心。他们对弊政的针砭远过于儒家,有时如长歌当哭。《老子》(本书引其原文概用王弼本)第42章说:“强梁者不得其死。”第75章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4章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为民和小国请命,但也为君和大国着想。怎么统一起来呢?理想境界是第80章所描述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就要像第19章所讲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老子》的作者当然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们由理想到现实,要求为人君者在上与下、动与静、雄与雌、刚与柔的关系上,甘于处下、尚静、守雌、贵柔。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为”。道家的无为,不是无所可为,而是达到无不可为的最佳方案,如第37章所讲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前提是第49章所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的作者认为,只要实行他们的主张,就会有第19章所讲的“孝慈”,第38章所讲的“忠信”,以及第19章所讲的“民利百倍”。
如果以为道家所讲的全是迂阔、虚幻之谈,那是没有真正认识道家。如果以为道家要历史开倒车,那是铸就了大错。其实,道家所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尽管历朝历代的君臣没有一个完全照道家的学说去做,但还是有一些明君贤臣为政务清静,以无为求有为,而且成效卓著,这就是有限度地实践了道家的学说。
从哲学上说,《老子》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例如第11章说: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58章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第63章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36章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第40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1章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第45章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78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诸如此类,无不蕴涵着妙理玄机,在《老子》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
《老子》的理论出自所谓“玄览”,即静观、细察、默想、顿悟。
除了类比推理之外,不加论证。这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思维方式,大而言之,也是东方世界的典型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道家独有的,其实儒家也有,只是道家更为玄妙罢了。这样的思维方式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然而富有启发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战国中期以后的状况,大致就是这样。不过,孔子其人和老子其人却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而且在理论上有相互渗透之处。老子也讲过要“孝慈”和“忠信”,孔子也讲过要“无为而治”,都是为了救世,道虽不同而可相为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就重儒轻道了,这是古代中国的不幸。
道学站在楚文化鼎盛期的起点上,它是正在迅速发展的楚国社会的批判因素,也是这个社会的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