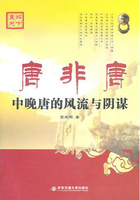护卫庄王的战车有三十乘,名为“乘广”,左广和右广各十五乘。是日清晨,庄王乘左广追逐刚离去的赵旃,右广紧随而行。赵旃情急,跳下战车,逃进树林中去。庄王的车右屈荡也跳下战车,追进树林,与赵旃格斗,拉下了赵旃的战袍,赵旃落荒而去。晋师唯恐魏锜和赵旃激怒楚人,以致楚人紧随他们而来,派出一队战车去接应他们。潘党在阵前望见晋国的战车扬起的尘埃,当即派人驾车传告全军:晋人打来了!这时,楚师已列而出,孙叔敖传令进兵。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
《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他所要求的是先声夺人,直捣晋阵。
在庄王的引导和令尹的督催下,楚师全速前进,战车疾驰,徒卒飞奔,很快就冲破了晋阵。荀林父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竟击鼓传令全军速退,宣布先渡过黄河回去的有赏。上军将士会善治军,能应变,预先在敖山前面设伏达七处之多。庄王命唐惠侯击晋上军,派骁将潘党率机动战车40乘协助唐惠侯。晋上军且战且退,士会亲自殿后指挥,得以保全。晋中军和下军在溃退中乱作一团,死伤枕藉,残部狂奔不可止。中军大夫赵婴齐先已在黄河岸边为自己预备了渡船,战败后抢先渡河逃命。
赵旃因所乘的战车受阻,再次逃向树林。逢大夫及其两子所乘的战车来到附近,逢大夫看到了赵旃,只当没有看到,加速驱车而过,嘱咐两个儿子不要回头。两个儿子不明缘由,偏回过头去,叫道:赵老头子在后面!逢大夫不得已,停下车来,叫儿子们下车,让赵旃上车。逢大夫指着路边的一棵大树对儿子们说:我会到这里来为你们收尸的。次日逢大夫赶到那棵大树附近,果然找到了两个战死的儿子的尸体。
晋将知庄子的儿子知(荀)被楚师俘获,知庄子救子心切,率其私卒反击。此人善射,射杀了连尹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把一个死的、一个活的都带回晋国去了。
晋国的一些战车在慌乱中陷进洼地,搅成一团,动弹不得,士卒束手待毙。追上前来的楚人动了恻隐之心,教晋人抽去车前的横木,拔下车上的大旗,才一乘一乘爬出了洼地。楚人放晋人走,晋人喜出望外,临走时扭头说:我们可不像贵国那样多次逃跑啊!这是解嘲的话,表面意思是晋人没有逃跑的经历,因而也就没有处理因逃跑而搅成一团的战车的经验。虽则语含讥刺,楚人并不介意,还是放他们逃跑了。
晋中军和下军为渡河而争船,都拉着船帮不放,船开不了,两军都操起戈来斩对方的手,据说掉在船舱里面的断指可以一把一把地捞起来。
《新序·杂事》说,庄王得知晋人因争渡而相杀,便下令停止追击。楚人教晋人逃出洼地,或许是在庄王下达停止追击令后发生的事。当天黄昏,楚师在邲水旁宿营。晋师残部仍在渡黄河,黄河边终夜人声嘈杂。
次日,楚国的辎重赶上了野战部队。于是,楚师东进,在衡雍(今河南中牟西北)暂驻。
潘党主张筑几个“京观”,让子孙知道祖先的战功。所谓“京观”,是把敌军的尸体堆成小山模样,封上土,插上表,用以炫耀战绩。《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庄王对潘党说,这,你可不懂了。从字的结构来看,“止戈”才是“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上列七德,而寡人一德也没有,寡人拿什么去告诉子孙呢?古代的明王杀死了首恶元凶,才做成京观以儆效尤。晋人无罪,他们是因尽忠于君命而死的,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尸体做成京观呢?作为佐证,庄王征引了《诗·周颂》的《时迈》、《武》、《赉》、《桓》诸篇,即“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和“绥万邦,屡丰年”等句,用得恰到好处。
庄王在衡雍祭了河神,筑了先君之庙,行了告庙之礼,然后班师。城濮之战的结局是晋胜楚败,邲之战却以楚胜晋败告终,其中的是非和得失,值得军事家和政治家详探细讨,也值得史学家深思长想。历来的评论,无不就国力是否雄厚、武备是否充足、朝政是否修明、士气是否高昂和指挥是否正确等立论,其是者胜而其否者败。由此而得出的意见,即使有些出入,也无关宏旨。国力、武备、朝政、士气、指挥诸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任何单项因素都未必能起决定作用,而且有些因素很难笼统地用“是”、“非”或“优”、“劣”来表述。在上列诸因素中,只有国力此强彼弱是清楚的,无论在城濮之战和在邲之战前,都是楚较强而晋较弱。但和平时期的国力并不等于战争时期投入的兵力和财力,更不等于在战斗过程中真正起了作用的兵力和财力。在交战双方实力相近的场合下,较强或较弱不是致胜或致败的主要因素。城濮之战的结局,是国力较弱的战胜了国力较强的。在邲之战中,晋国投入的兵力和财力并不少,倒战败了。政治是否修明,在邲之战前不难判别,即晋不如楚;但在城濮之战前很难论定,楚未必不如晋。交战双方的士气,尽管有或高或低的差别,可是并不明显,很难说高多少就必胜无疑,低多少就必败无疑。至于指挥是否正确,后人的认识大抵为结局所左右,以为胜者指挥必正确,败者指挥必错误,这是把后验的当成先验的,把已然且偶然的当成未然而必然的。一言以蔽之,还是以成败论英雄。这样,通常是愈省力则愈失真。
城濮之战和邲之战都是大决战,假如以方程式为喻,它们都是难解的多元多次方程式。必然性不仅是由偶然性展现的,而且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偶然性的无序导致失败,偶然性的有序导致胜利。
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序与否。有序的标志是君臣同心、将佐同德、虑事切实、审势中肯等等,无序则适得其反。
邲之战前,晋国的三军将佐发生过几次争论。上军将士会和下军佐栾书深悉楚国的政情,都认为不宜与楚国为敌,《左传·宣公十二年》记其言甚详。
士会说,德、刑、政、事、典、礼六者都走上了正轨的国家,是不可敌的。楚国就是这样,它做到了“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谓“德立”即郑国服则舍之;所谓“刑行”,即郑国叛则伐之;所谓“政成”,即连岁出征而“民不罢劳,君无怨”;所谓“事时”,即用兵不违农时;所谓“典从”,即有令行禁止的良法;所谓“礼顺”,即贵贱有别、赏罚得当等等。士会指出这六点来,虽言之不虚,但未免过誉。如士会说: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这,就言过其实了。当时的楚历,官方行周正,民间行夏正而月名与夏历有异。“荆尸”为民间楚历正月,相当于周历三月。“荆尸而举”即在夏历正月用兵,方值农闲,不违农时。可是,楚国出兵并不总在夏历正月。这次在郑都和邲水连打两仗,由春经夏入秋,历时四月有余,不可能不耽误春耕春种。劳师远出,旷日持久,虽打胜了第一仗,却很难保证把第二仗也打胜。
就“事时”这一点来说,楚国不如晋国,晋国这次出兵倒恰在农闲时节。郑卿皇戌说楚师又“骄”又“老”而且“不设备”。栾书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自从攻灭庸国以来,庄王几乎没有一天不提醒国人要认识民生的艰难,要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祸患。出征时,庄王几乎没有一天不提醒将士要认识常胜不败是很难做到的,殷纣王百战百胜而终于断子绝孙了。庄王还教育国人要发扬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要懂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由此,栾书认为不能说楚师“骄”了。栾书引晋国名臣狐偃的话说:“师,直为壮,曲为老。”“直”为有理,“曲”为无理;“壮”为体力强、士气高,“老”为体力弱、士气低。栾书认为这次是楚直晋曲,由此,不能说楚师“老”了。栾书提出,庄王白天有左广和右广轮番侍从,夜间有内民轮番守卫。由此,不能说楚师“不设备”。皇戌为了怂恿晋师攻击楚师,故意把楚师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一经栾书揭穿,便讨了个没趣。
在邲之战中,晋楚双方兵力的强弱和士气的高低相去无几,但楚国君臣心志齐一,非晋国君臣所能企及。君臣心志齐一,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不同意见。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让不同意见充分展开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择善而从。心志齐一体现在决策既定之后态度的坚定和行动的协调上,从国君到主帅,从主帅到将佐,从将佐到士卒,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城濮之战前的晋师和邲之战前的楚师,内部都有不同意见,但在决策既定之后,曾有不同意见的将佐都能和衷共济。如令尹孙叔敖,出于恤民和求稳的愿望,曾主张退兵,与庄王不谋而合。但在庄王被伍参说服,决定向晋师开战之后,孙叔敖态度很坚定,指挥很果断。战时,庄王先行,孙叔敖继进,中、左、右三军就车驰而卒奔了。在晋楚双方兵力大致相等的条件下,楚师竟有如此一往无前的气势,晋师当然非败不可。战胜之后,庄王拒绝筑京观,为此而发表了一席内容精深的谈话。与战胜了就趾高气扬的晋文公相比,优劣立判。
(第四节霸业的顶峰和霸主的本色
邲之战后不足半年,即公元前597年冬,楚伐萧。萧是宋的附庸,公族为子姓,其故址在今安徽萧县。宋、蔡发兵救萧,萧乃固守待援。楚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临阵不慎,被萧人俘获。庄王派使者告诉萧人,只要不杀两位楚将,楚师就可以撤走。萧人不明利害,偏偏处死了两位楚将。庄王大怒,传令攻城。申公屈巫(巫臣、子灵)报告庄王,天冷,士卒挨冻了。庄王巡视三军,慰勉有加。三人军将士顶风冒寒,迅即包围萧都,发动了连续的强攻。次日,城破,萧被彻底地灭亡了。
人的性格通常都不是单纯的,往往有两种似乎并不协调的性格交缠在一起,此显则彼隐,此隐则彼显,但总有主从之分。庄王也这样,冷静时能做到的,冲动时就做不到。对公理和正义更是这样,言论和行动,认识和实践,有时合拍,有时脱节,可以几经反复,只是合拍的多些,脱节的少些罢了。伐萧正是脱节的一个实例,因而不是值得称道的业绩。尽管这样,当时舆论所贬斥的不是庄王的暴烈,而是萧人的狂妄。庄王心安理得,只是苦了那些挨冻的士卒。
公元前595年———庄王十九年,申舟奉命出使齐国,庄王吩咐他不可向宋国假道;同时,公子冯奉命出使晋国,庄王吩咐他不可向郑国假道。使齐者必经宋,使晋者必经郑,按当时的惯例,越他国之境非假道不可。庄王的意图无疑是要试探宋、郑两国对楚国的恭顺程度,可是难为了使者。申舟说,郑国耳聪目明,宋国耳聋目盲,使晋者可保无恙,使齐者必死无疑。当时郑从楚,宋背楚,郑襄公刚朝见过庄王,宋人则因其先君曾在孟诸受辱而衔恨于申舟,所以申舟预言自己非死不可。庄王对申舟说,如果宋人杀了你,我就去讨伐宋国。申舟无奈,把儿子申犀带进宫让庄王见过,就出发了。果然,宋卿得到报告说申舟过境不假道,为申舟无视宋国主权的蛮横行为所激怒,杀死了申舟。消息传到了郢都,正安坐在宫中的庄王勃然变色,奋袂而起,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到天井里,随从才给他穿上鞋。走到宫门外,随从才给他佩上剑。走到一处名为蒲胥的市区,随从才让他登上车。相传庄王当夜住在城郊,部署兴师伐宋。
是年九月,楚师包围了宋都。这是一场空前持久的恶战,宋人矢志坚守,楚师虽动用了首创的攻城利器“楼车”,仍不能得志。宋向晋告急,晋爱莫能助。拖到翌年五月,农事大忙,楚师准备回国种田。庄王已登车,申犀拉着庄王的乘马,稽首对庄王说,家父明知必死而不敢违命,大王却食言了。庄王默然,无言以对。申叔时为庄王驾车,见状,献“筑室、反耕”之计。“筑室”,即在阵地上建房,宋人一看到就会明白楚师还要围攻下去;“反耕”,即派一部分士卒回国去种田,以应农事之急。庄王从其计。不出申叔时所料,宋人不胜忧惧。当时城中缺粮,民众已在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再也守不下去了。于是,由当初主谋杀死申舟的宋卿华元出面,向楚乞和。庄王见宋人有诚意,退兵一舍。楚宋和议既定,双方举行盟誓,据《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其辞有云:“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华元到楚国做人质,以示守信。
灭萧之役和围宋之役,都是恃强凌弱,小题大做。庄王不惜用暴力来强化自己的霸主地位,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诸侯很难指责庄王,因为正是萧国和宋国先采取了促使冲突激化的行动,尽管它们遭到十倍、百倍、千倍的报复,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也是咎由自取。而且,庄王言必信,行必果,其品格令人畏服。
春秋五霸,性情最暴烈的是楚庄王,但度量最宽宏的也是楚庄王,无论对国外对国内,都是这样。对国外,逆者讨而威之,足见其暴烈;顺者抚而怀之,又足见其宽宏。对国内,若敖家族的乱臣贼子几乎被斩尽杀绝,足见其暴烈;平时爱护臣僚,珍惜人才,重大节而轻小过,又足见其宽宏。
有一则故事,说庄王不究臣僚的小过,见于《说苑·复恩》,大意是:庄王与群臣夜宴,忽而风吹烛灭,有个人暗中拉扯庄王身旁一位美人的衣裳,美人拔下了那个人的冠缨,向庄王告发。不料庄王竟向群臣宣告,你们与寡人饮酒,都要尽欢才好,谁不拔掉自己的冠缨,谁就不算尽欢。于是,群臣都把冠缨拔掉。然后重新燃烛,尽欢方罢。在邲之战中,有一位将领总是走在庄王的前面,奋力作战,五次击退来犯的敌人。庄王问此人何以毫不畏死,此人答道,我早就想肝脑涂地报答大王了,今天才遇到这个机会,我就是那个暗中拉扯美人衣裳的人啊!后人说庄王有这个故事,无疑是因为他确实有容人的雅量,至于这个故事的真伪,却是无须查究的。
对臣僚的爱护和对人才的珍惜,绝不等于纵容。《淮南子·缪称训》记共雍向庄王请赏,庄王对他说:“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汝)无一焉,吾无以与女(汝)。”庄王力求做到赏罚得当,这在讲究贵贱亲疏的社会里是政治清明的一个重大因素。四年之内,楚人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重足而立,屏息而听。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则唯楚人马首是瞻,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
连年征战,师疲民劳,楚人的生计不免受到损害。对此,不但孙叔敖怀着深沉的忧虑,庄王也不是不明白。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取决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以一位国君的意志为转移。在列国竞逐的时代里,霸主是由惨烈的战争造就的,他们是战神的骄子。
伐宋得胜后,楚国息兵养民,三年没有出征。息兵养民与用兵劳民又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前者为弛,后者为张。真正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必须善于掌握张和弛的节奏。《说苑·正谏》说到庄王伐阳夏,久战而不罢,群臣欲谏而不敢。庄王忙中偷闲,到云梦去打猎,伍举相机进谏说,大王能猎获很多野兽,靠的是马。要是大王的国家灭亡了,大王还能有马吗?庄王答道,你说得好!寡人知道打败了强国可以称雄天下,扩大了国土可以增添财富,却忘掉了民众可能不为我所用。于是,罢阳夏之役。这也只是一个故事,但说明了庄王在贤臣辅佐下能注意掌握用兵与息兵以及劳民与养民的适当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