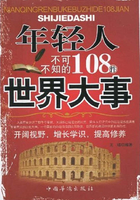熊通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慑于楚国的兵威,照办不误,派使者去向周天子进言了。这事尽管没有办成,但终究表明随国是顺从楚国的,楚国可以扬威于汉东了。所谓“观中国之政”,意即介入中原的政局。固然可以说这是大言,但它绝非虚张声势的空言,其中包含着熊通的真情实意。熊通“观中国之政”的雄图,不久就由他的子孙化为实践了。季梁是一位贤臣,对他,楚人可能比随人更加尊重。他的影响,在楚国或许比在随国更加深广。据《左传·桓公六年》所记,季梁的学说以民为神之主作中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按照寻常的认识,神为民之主,逻辑上当然可以引申到民须忠于君而信于神。按照季梁的理论,民为神之主,逻辑上自然应该引申到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这个思想出现在春秋早期,虽誉之以石破天惊亦不为过。后来真正因季梁的理论而受益的,倒不是他的本国———随国,而恰是他的敌国———楚国。
季氏自称“周王孙”,有铜器铭文可证。随州季氏梁1979年出土铜戈两件,都有铭文。其一铭曰:“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之用戈。”
其二铭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如上所述,曾即随。季怡,可能是季梁的后人。季氏梁,可能是后人为纪念季梁而取的地名。
楚国扬威于汉东,使靠近楚国的几位诸侯寝不安席。谷伯和邓侯跑到泰山下面去,朝见鲁公。他们想靠鲁国来牵制楚国,用心可谓良苦。但他们对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却不甚了了,那就是远水难救近火。
公元前704年———熊通三十七年,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史记·楚世家》记熊通闻讯大怒,说: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果然,他当即自立为楚武王了。显然,“武王”是熊通生前就有的尊号,死后则沿用为庙号。和先君熊渠一样,熊通也说过:“我蛮夷也!”当然,这也是为独行其是辩护所用的遁词。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中原诸侯在国内虽偶尔称王,在国外则仍称本爵,而且没有生前就自选庙号的。熊通称王之后,周天子莫如之何,诸夏和群蛮也都莫如之何。
斗伯比认为这时的随有隙可乘,主张再次伐随,武王从其议。
这年夏天,武王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在今湖北钟祥东)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黄国离沈鹿很远,尚属情有可原;随国离沈鹿不远,随侯拒不到会分明是藐视武王,而这正中武王下怀。武王一面派章去责备黄君,一面兴师伐随。那位受宠用事的少师主张速战速决,随侯以为可行,不顾季梁谏阻,引兵迎击楚师。楚师迂回到随都的东面,随师在速杞(在今湖北随州)与楚师遭遇。将战,季梁对随侯说,楚人尚左,楚王一定在主力左军,大王最好也随左军行动,去进攻楚师的右军,可不要同楚王碰上。季梁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少师说要王对王才相称。随侯又听从少师,坚持尚右的传统,仍随右军行动,命少师为戎右,下令进攻楚国的左军。冲锋之后,胜负立决。随师大败,随侯落荒而逃,他的戎车和车右少师一起被楚师俘获。武王接受斗伯比的意见,不灭掉随国,而让随侯在表示愿意悔改之后与武王会盟。从此,随国不敢再开罪于楚国了。三年以后,楚国在汉东又打了一场胜仗。那是在公元前701年———武王四十年,莫敖屈瑕奉命领兵东行,以期与贰、轸两国会盟。郧是贰、轸的邻国,以为楚与贰、轸会盟将不利于郧,便策动随、绞、州、蓼诸国联兵截击楚师。蓼()在今河南唐河南,随、绞、州的地望已见上文。随国没有响应,绞、州、蓼三国虽表示响应而尚按兵不动。郧师则急不可耐,已集结在郧郊的蒲骚了。对楚师来说,这样的局面是不难对付的,敌军又散又弱,可以逐个击破。
然而屈瑕缺乏主帅应有的素质,稍遇疑难便优柔寡断,将东渡汉水时收到上述情报,竟不知所措。副帅斗廉建议屈瑕顿兵郊郢(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或宜城东南),以观随、绞、州、蓼的动静;斗廉自己则请求带领一支精兵奇袭郧师。屈瑕还是游移不定,打算卜问吉凶。斗廉认为没有卜问的必要,《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斗廉说: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斗廉异乎寻常的坚定,促使屈瑕打消了忧虑。斗廉统率的精兵兼程东行,夜袭蒲骚,一举击溃了郧师。郧人自食其狂妄的恶果,楚与贰、轸则得以在胜利的喜悦气氛中会盟不误。
速杞之役和蒲骚之役确立了楚国在汉东的霸主地位,此后汉东尽管还有一些反复,但大局已定了。
(第四节兼顾侧背
武王没有把侧背的安全置诸脑后,东征的胜利使他受到鼓舞,于是有胜利的西征和北征。
还在自立为武王的公元前704年,打败了随国之后,武王就曾移师西进,击败濮人,拓宽和加固了后方。
其明年,汉水上游的巴国派使者韩服到楚国来,请求楚国协助巴国与邓国通使修好。于是,楚使道朔陪同巴使韩服访问邓国。不料,刚走到邓国南部的鄾邑,还没有渡过汉水,就遭受暴徒袭击,两人都被杀死,礼币则被抢走。章奉武王命向邓国提出抗议,邓侯竟拒不接受。由此,楚、巴合兵伐邓,包围了鄾邑。这一仗,楚又是主谋,又是主力。邓侯命大夫养甥、聃甥率援军救鄾邑,迅速渡过汉水攻击楚巴联军。楚巴联军的主帅是那位后来因奇袭郧师而立下卓著战功的斗廉,这次伐邓围鄾只是小试身手。邓师中了斗廉的佯败诱敌之计,陷入楚巴联军重围,兵败如山倒。鄾邑的守军和居民见状,连夜逃散。
大约在鄾之役以后不久,楚师北渡汉水,击败鄀师。战俘中有一位名叫观丁父的,颇有韬略,武王任命他做“军率”。“军率”是高级将领,可以指挥一军。
公元前700年———武王四十一年,楚伐绞,问其与郧合谋袭楚之罪,主帅仍为屈瑕。此役情况明了,任务单纯,而且是以石击卵,屈瑕指挥自若,绞被迫为城下之盟。当时为城下之盟等于战败者向战胜者认罪,是战败者的奇耻和战胜者的殊荣。绞人为此而忍辱含垢,屈瑕则由此而趾高气扬了。
楚伐绞,是从东南往西北走。更在楚都东南的罗人企图乘机偷袭楚都,其大夫伯嘉受命到彭水(今南河)去侦察。伯嘉一而再、再而三地点算楚师渡彭水的人数,不禁忘形,被楚人发现了。伯嘉带回罗国的情报,大概是楚师主力没有全部出动,所以罗国按兵不动,以为就此无事了。可是,屈瑕没有忘记要惩罚如此胆大妄为的罗人。
其明年,楚伐罗,主帅还是屈瑕。年事已高的斗伯比为屈瑕送行,见屈瑕有骄矜之色,深为担忧,回丹阳后,请求武王增援屈瑕。
其实,这次楚伐罗是全军以出,无援兵可派了。武王听了斗伯比的话,不以为然,斗伯比也没有详说力争。武王回宫后还在想斗伯比那个近乎荒唐的建议,不知所为何来,于是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明达事理,善解人意,她对武王说,大夫斗伯比所担心的,怕不是士卒寡不敌众吧?我想,他所担心的是莫敖轻敌致败哩!武王恍然大悟,派人去追告屈瑕。可是为时已晚,悲剧正等待着屈瑕。
屈瑕只能指挥单打一的战役,对涉及多方的战役和变化多端的战局则束手无策。这正像做代数题,他只能做一元一次方程式。而且,他有一个致命的性格弱点,即在逆境和貌似逆境的顺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多疑难断,在顺境和貌似顺境的逆境中则会同样不由自主地一意孤行。伐罗不像伐绞那么单纯,它是貌似顺境的逆境。
邓、卢、罗这条常山之蛇已伤而未僵,在楚国发兵后,它动弹起来了。屈瑕为了尽早攻克罗都,督催全军尽快渡过鄢水(今蛮河),队列错乱也在所不惜,以致渡过鄢水之后不成队列了。行近罗都时,正面有罗师迎击,这是谁也不以为怪的;背面突然出现卢师偷袭,这却使屈瑕和他的将士都大惊失色了。楚师腹背受敌,迅即溃败。
屈瑕因退路被罗卢联军截断,不得已,率残部南逃。由于罗卢联军的追击,屈瑕一行狂奔不止,竟逃到了荒谷一带。屈瑕无面目见君王、父老,乃自缢;其他将领则自囚,以听罪。武王宣告臣民,这是寡人的过错。他宽宥了全体将士,但楚人的耻辱不是君王的宽宥所能洗刷的。
屈瑕的自缢开创了楚国统帅以死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其人其事,于当时虽有过,于后世则不为无功。
伐罗之败给了楚国不止一个惨痛的教训:传统的用兵方针———近交远攻已经过时,要改弦更张了;传统的选官原则———任人唯亲有利亦有弊,要先贤而后亲才最好。
从文献资料来看,此后八年之中楚国没有兴师动众,表明其似乎很难补偿伐罗之役的损失。其实不然,伐罗之役,楚师虽则溃不成军,但其死伤未必惨重。此后八年之中,武王改变了只图远略、不恤近患的一贯作风,稳步推进,在巩固腹地的基础上开拓边疆,楚师攻灭了近在肘腋之间的罗国、卢国、鄢国以及较远的州国和蓼国,而且在灭州之役和灭蓼之役中任用的统帅是做过战俘的鄀人观丁父。
(第五节武王暮年的壮举
武王在位五十一年时,至少有七十岁了,自觉老境已到,而且病势渐重,然而壮心不减。这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以楚子为楚王而事之。由此,随国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武王以此为借口,又一次大举伐随。像往常打大仗那样,这次他仍然躬临战阵。楚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车兵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工兵的装备和技术也改进了。即将为出征而斋戒、祭祀之时,武王觉得心律不齐,便告诉夫人邓曼。据《左传·庄公四年》所记,邓曼为之叹息,她坦然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与世长辞,国家还算是有福的。③武王就这样出征了,为社稷而视死如归。到汉水东岸后不久,心疾猝发,他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当即去世。今钟祥东有木山,应即武王病故之处。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决定严密封锁武王去世的消息,率领全军继续前进,修整了道路,在溠水上架设了浮桥,在靠近随都的地方扎下了营垒。随人见状,以为楚师有久战之意和必胜之志,不胜惶恐,于是请求议和。屈重代表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人才收兵回国。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武王发丧。
对英雄迟暮的武王来说,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所。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有道伐无道是可以与“汤、武”媲美的正义事业。因此,穷兵黩武一类的贬词对武王是全然不适用的,这,只要看武王的政治遗产就可以明白了。
武王所留下的,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文明的灿烂阳光,从江汉平原的西部照到了东部,从汉水的西边照到了东边。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近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的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正走向更为文明昌盛的未来。可见,武王的征服事业与所谓蛮夷的“乱华”和“猾夏”殊少相似之处。
武王所留下的,有一套粗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当然还有其他官职,只是文献没有一一记录下来。楚国真正的封邑或称赏邑,始于武王封公子瑕于屈。先前的楚国贵族只是以祖居之地为氏,不曾以封赏之地为氏。在这个国家里,徒兵和车兵各有所用,都是国家的爪牙。
武王所留下的,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左翼是鄀,右翼是蓼,相向窥伺着南襄夹道。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和占领南阳盆地了。
在武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标新立异的勇气。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发愤图强,只是一味地攻城夺地,杀人越货,那就错了。楚人的发愤图强,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先人筚路蓝缕的精神,创业兴国。武王和他的臣僚懂得恤民方能役民的道理,以及足食方能足兵的道理。先前出师不大顾及农忙、农闲,武王末年特意在农闲时出师,这是一大进步。在农闲时出师,即《左传·宣公十二年》
所谓“荆尸而举”。“荆尸”为楚历月名,相当于夏历正月,恰在农闲时,“荆尸而举”有“事时”即适时的优点,后世奉之为良规。这就做到了《国语·周语》所讲的“民之大事在农”,“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外,假如以为武王时楚人的标新立异只是追求与众不同,那也是错的。楚人还像先前那样,歆慕中原的文明,能采用的就采用,能仿效的就仿效。但到武王时,他们开始边模仿、边创造了。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史记》裴骃《集解》引《皇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鲖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按,其地在今河南新蔡,春秋早期非楚境,不得有楚王冢,《皇览》虽言之凿凿而必误无疑。
《史记》张守节《正义》引《世本》曰:“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
按,此说也断不可信,其地在楚武王时非楚所有,也不可能有楚武王冢。楚武王葬地应在汉水之阴,墓上无封土,不得谓之冢。它究竟在何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考古发现了。
当楚人在南国崛起之时,那些留居北国的祝融残部都在沦落之中。
秃姓的舟人原在淮北,早已为西周所灭。妘姓的郐和鄢靠近郑国,西周末东周初为郑国所灭。己姓的苏和温已经合二为一,在周、郑、晋之间,春秋时代为狄人所灭。妘姓的路和偪阳靠近晋国,春秋时代都成了晋国的领地。曹姓的邹即邾靠近鲁国,相传为曹姓而实则为己姓的莒靠近齐国,只有他们两家活过了春秋时代,但也乏善可陈。楚人同他们像一群任意游走的鱼儿,已在历史的风涛中相忘于江湖了。
(第六节越汉水,出方城,入中原
武王死,子熊赀立,是为文王。
熊赀早年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傅是从申国请来的,史称“葆(保)申”。因武王在位长达五十一年,文王继位时已人到中年了。
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也许这是武王的遗命而由文王付诸实施的。郢作地名,古义不详,今义为岗地或台地。
何以称“郢”,至今不可索解。当时的郢都故址在今宜城南部,东不过汉水,南不过蛮河。早在武王中期,楚国就占领了在它东南的郊郢,用做渡汉东征的基地。武王后期,击灭了罗、卢、鄢诸国,原为鄢地的郢就成为比丹阳更好的奠都之地了。文王迁都于郢,可谓水到渠成。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处在南来北往、东来西往的枢纽上,南瞰江汉平原,北望南襄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荆雎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汉水中游的重镇。
楚国以郢为首都,无论制驭蛮、越、巴、濮,还是抚绥汉阳诸国,乃至窥伺中原诸夏,都便于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