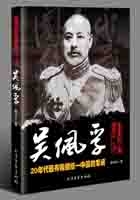遂州有三宝,稚儿跳绳踢毽时最爱唱:“蓬莱盐巴蓬溪糕,遂州南街打菜刀。”
蓬莱制盐历史十分悠久,可溯上到西汉文景之时。史载蓬莱所产井盐,盐粒洁白如雪,远销国中各大商埠口岸。蓬溪所制姜糕甜而不腻,入口化渣,当年慈禧太后品尝之后,赞不绝口,赐封为“玉糕”,供宫廷专用。这遂州南街的曾记菜刀,更是了得,刀锋寒光逼人,削铁如泥,声望直逼杭州张小泉剪刀。
南街是遂州城一等一的热闹去处,早些年,曾记铁匠铺的生意火红得不得了。每天清晨天不见亮,小伙计们就起床生火打铁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比雄鸡的啼鸣还要早。
住在南街上的人们,听到铁匠铺的风箱声,就像贪杯的人闻到了美酒的香味一般,浑身上下通泰无比。设若哪天铁匠铺因为有事不营业,人们便一天都提不起精神来。
南街上闲散的人离不开铁匠铺,每日里不论寒暑阴晴,九点钟准会围过来,一边闲摆些天南海北的龙门阵,一边看曾文正打铁。
曾文正是曾记铁匠铺的第五代传人,技艺炉火纯青。邻人们说看他打铁,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每日里,曾文正总是不慌不忙地先抽一袋旱烟,过足烟瘾后,炉里的火正好发出青光,他知道炉温已达到了最高点。于是,他左手拿着一把铁钳,夹一块红红的毛铁,右手拿一小锤,一锤一锤地指点着两个徒弟,用大锤将那块毛铁打成刀形。
刀形铁变冷后,两个徒弟一人拉风箱,一人将冷铁夹入炉间,埋进炭里加温。
这时,曾文正就会乘隙小憩一会儿,喝一口瓷缸里的凉茶或温开水,顺便和围观的人开开玩笑,偶尔摆些荤龙门阵,常常逗得人们哄堂大笑。
等到炉火红了,曾文正又将炭里的“刀”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反复指点徒儿锻打。
这样的过程往往需要反复五六次,有时甚至七八次。当曾文正右手里的小锤极快地敲打那把“刀”时,徒弟就停了手,用黑乎乎的毛巾擦一擦额上的汗。
曾文正虚起眼睛看了看货,认为满意了,顺手将打好的菜刀,夹起来放进旁边的水桶里淬火。“嗞”的一声响,水桶里立即冒出一股浓浓的水蒸气。
菜刀就这样打成了,围观的人少不了啧啧称赞。
这些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的曾文正老了,变成了曾大爷,自然没有力气再从业打铁了。想想曾经有过的辉煌,他时常抿着嘴巴偷着乐。
南街上的人们却记得他,也记得铁匠铺带给他们的快乐。邻居们每每从铺子前经过,都要和曾大爷打打招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曾大爷总是躺在竹椅上晒太阳,手里把玩着一把紫砂壶,慢慢地品着茶,露出极满足的神色。
南街上最有学问的张秀才说,曾大爷已经从铁匠蜕变成了雅玩的大家了,无欲以达禅境矣。
邻人们听不懂张秀才所云,都说他的话像六月里隔夜的稀饭,有一股酸臭味。
今年开春,遂州城外的涪江通了汽船。汽笛声里,很多颧骨高耸的粤人来到了遂州城。人们传言南方人很有钱,他们到遂州来,是专门来寻找和购买宝物的。
遂州本地人私下里笑粤人痴,遂州哪来的什么宝物?见到粤人就戏谑他们要不要城外头河滩上遍地的石“元宝”。
粤人笑笑,并不生气。路过铁匠铺时,看见曾大爷手上的紫砂壶古朴雅致,眼中便放出绿光来,恳求一观。
曾大爷抱壶在怀,听不懂粤人的“鸟语”,只顾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啜着茶。
粤人连比带画,大冷的天,额上急出了汗。
曾大爷终于明白了,龟儿子原来口渴了讨茶吃,便嘎嘎地笑着,将紫砂壶颤巍巍地递了过去。
粤人接壶在手,并没有喝茶之意。他反反复复地把玩,壶嘴内现一图案,一鹤振翅欲飞,似明朝宣德年间制壶名家“松鹤叟”的印章。续观壶底,果然有大明宣德款识,以壶内茶垢和手抚痕迹之润泽论,当属宣德老品无疑。
粤人心头狂喜,松鹤叟制壶,素有捏泥成金之美誉,世传真品可遇而不可求。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曾大爷拉着家常,说欲用壶内壁茶垢治哮喘,愿出十金求购。
曾大爷两眼微微地闭着,好像没明白粤人所言何事,古井一般的心里,连一丝涟漪也没有泛起。这把壶是曾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曾氏子孙喝着它长大,也喝着它制出一把又一把名扬天下的菜刀。
唉,壶虽无意,人却有情。
粤人见曾大爷闭目不语,只道老人家嫌价低不肯出售,又加十金购之。
曾大爷依旧不言不语,闭目躺在竹椅上,双手将壶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看他心满意足的样子,很像一位坐禅的老僧。
粤人不解,悻悻而去。
四邻耳闻此事,知道曾大爷手中的茶壶价值二十金。乖乖,一把破茶壶居然是个宝贝疙瘩!街坊邻居们便接踵而至,铁匠铺又开始热闹起来。
曾大爷不知缘由,心里自然高兴。他用紫砂壶沏了好茶,热情地招待众人。但是,他渐渐地发现,街坊邻居到铁匠铺来,眼中已没有了往昔的淳朴,而多了攫取之色。更让他烦恼不已的是,往日自己可以躺在竹椅上,自由自在地品茶,现在却要坐起来应酬,实在让他非常不舒服。
曾大爷开始烦躁不安,吃饭不香,喝茶也不香。他知道这一切不顺心,全都因为他有一把值钱的紫砂壶。
端午节,遂州城外涪江赛龙舟。粤人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遂州城。
他匆匆赶到铁匠铺,不再遮遮藏藏,明确地告诉曾大爷,自己为了紫砂壶专程从广东而来,并加价到一千金求购。
观者哄然叫好。
曾大爷恨粤人扰乱了自己的清静生活,今见他又来胡言乱语,心里越发恼怒,任由他巧舌如簧,就是不为所动。他把那把壶在手中玩了又玩,放在嘴边亲了又亲,猛然掼于石阶上,碎声砰然。
一街邻坊无不惊愕。
粤人见了,顿时捶胸跺脚。他捧起地上的碎片,如丧考妣,惨嚎之声不绝。
从此以后,邻人见曾大爷面容恢复了往日的安详,闭目躺在竹椅上。
旁边置一陶壶,偶尔品上一口茶,那神情,连张秀才见了,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据老辈人讲,那一年,曾大爷一百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