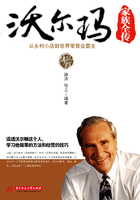大清自开国以来,历来推崇武备,在全国各地广置银库,以备战时之需。四川乃天府之国,素为朝廷倚重,辖内九府三十八州一律设置甲等银库,贮银规模一时为全国之冠。遂州地处涪江中游,平畴沃野,两川税银五占其一,州衙库存充盈,有金遂州银潼川之说。
乾隆十二年(1747)春,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叛乱,兵燹波及松茂二州,两川震动,朝廷召集十万重兵讨伐。四月,王师入川,急令调拨遂州库银以资军饷。四川巡抚冯永昌亲往遂州银库解押,谁知启库验银,偌大的银库里,官银已被盗走十之五六!冯永昌大惊失色,着令现场人等严密封锁消息,外泄者军法从事。并于当晚连夜赶回成都,禀报总督胡昌盛得知。军备官银被盗,事关平叛大局,胡昌盛哪敢怠慢?只得据实呈报朝廷,翌日天明,八百里加急文书飞驰京师。五日后,兵刑二部文牒火速传到蓉城,责令胡昌盛、冯永昌二人限期侦破此案。
二人得令后,急得像热锅上乱爬的蚂蚁,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此事案发天字一号,到期不能结案,项上吃饭的家伙肯定不保。胡昌盛本欲亲自前往遂州,但十万王师过境,应酬接待事务繁多,加之又要征调他州库银以筹军饷,一时脱不了身。二人商量后,总督胡昌盛留守省垣,巡抚冯永昌再莅遂州。临行前,胡昌盛拉着冯永昌的手握了又握,拍了又拍,像生离死别一般反反复复地叮嘱了又叮嘱。
冯永昌受此重托,一日飞奔两百余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遂州城,当天夜里进驻银库。
银库设在涪江中的圣莲岛上,四面环水,只有一座小小的吊桥与岸上相连。桥长三十余丈,两端皆有重兵把守,仅就其地理位置来判断,外盗没有任何可能进入到银库中作案。
冯永昌在银库里悄悄地观察了三天,没有发现丝毫有价值的线索。思来想去,认定是内贼作案,便在遂州衙门的安排下,乔装成新来的库工,混迹其间暗中察访。
每日的辰时,库工们按例在库房一侧的桥头,准时集体裸身交接工作。守夜的库工还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地走过小桥,上岸后到衣帽间穿戴完毕,方可各自回家。冯永昌也不例外,一切都严格按照皇家规定程序执行,但即使是这样,库中的官银仍时有丢失。
冯永昌心里十分纳闷,真是大白天见鬼,奇怪得很。
遂州捕头陈豫川,是个有着二十多年侦探经验的人,自从奉命协查此案以来,一个人便有事无事地在遂州城的大街小巷里闲逛。他认为如果真是内贼所为,遂州城中肯定会有蛛丝马迹出现。陈豫川的思路常常与众不同,尤其在侦查疑难案件时,一般人多认为案发现场才会有线索,其实不然,真正的作案高手,现场怎么可能留下犯案痕迹呢?仅凭银库所处的位置和严格的工作程序,那里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此,陈豫川认为真正容易得到信息的地方,应该是那些龙蛇混杂的茶肆酒楼、花街柳巷。
陈豫川始终像一个闲散之人,呱嗒呱嗒地趿拉着一双脏兮兮的木屐,整日里城东城西地到处吃茶喝酒,听茶客酒徒们摆些三教九流或江湖豪客的龙门阵。
谷雨节前一日,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郎酩酊大醉后,在天上宫戏园子里放声痛哭,任由旁边的人百般劝慰,依然哭闹不止,好像有什么伤心事一样。
好事者说少年郎在“百花楼”有一位叫香荷的相好,交往已有年余,二人感情甚笃。不想日前被一神秘客看中,出重金包下香荷,少年前去与之理论,那人一边搂着香荷饮酒,一边抛出十锭马蹄银,羞辱道:“此银为大爷在此一夜的过夜费,小子可有银子?”少年不堪羞辱,到玉春堂酒楼借酒泄愤,因而哭闹不已。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豫川心想这遂州城内,怎么会有出十锭银子上百花楼嫖一宿的富豪?莫不是哪里来的江洋大盗不成?
陈豫川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天上宫,悄悄来到位于柳荫街的百花楼。他乘人不备,一个鹞子翻身越过高高的院墙,隐身潜入到楼里窥视。香荷的房间内,果然有一客正与之亲热。定眼一看,陈豫川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人竟然是省垣来的巡抚大人冯永昌!让陈豫川更加吃惊的是,放在案桌上的马蹄银,居然是遂州银库中所存的军备银子无疑!陈豫川不敢声张,连忙从百花楼中悄然退出,急匆匆地赶回州衙中报与上司周昌明知晓。
周昌明虽为遂州州牧,官位却远不及巡抚冯永昌。当他听了陈豫川的报告后,也是惊骇不已。他不敢造次,反复叮嘱陈豫川,在没有获得真凭实据之前,只可暗中严密监控,不可鲁莽缉拿,免得打虎不成反被虎伤。
周昌明表面上要陈豫川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以陈豫川之能,焉能判断有误?因此,他一边给陈豫川交代着注意事项,一边急急忙忙草拟呈报公文,画押签章后,立即遣人连夜快马飞报兵刑二部。他之所以绕开总督胡昌盛直接呈报朝廷,是想独贪破案之功,借以减轻遂州库银失盗的渎职罪。
周昌明自作聪明耍心眼,怎瞒得了陈豫川?陈捕头觉得十分地可笑,但闷在心里并不说出来。回到家中,依旧满脑子都是冯永昌那胖乎乎的嘴脸。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身为捕头就应该心无旁骛地时时想着案子,怎可心存杂念而念及其他?
陈豫川独自坐在书房里抠脑壳,却始终不得其解。冯永昌整日在省垣成都为官,哪有时间前来遂州作案?难道他会分身术不成?可是刚才在百花楼看到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白花花的库银怎么可能假得了?
陈豫川虽然认为冯永昌没有时间作案,但他依然确信遂州库银失盗一事,肯定与冯永昌有关。当天,陈豫川命令手下的兄弟们,在冯永昌临时下榻的寒阳宫四周,暗中布控,定要拿到他犯罪的真凭实据。
夜里,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的陈豫川,一时心乱如麻,他决定亲自到寒阳宫走一趟。来到寒阳宫后,天色已经黑尽,隐于竹木间的兄弟们,见陈捕头亲自前来夜查,便用暗号和他打招呼,示意冯永昌已经返回了住处。
陈豫川笑了笑,也用暗号一一作答,自己选择了一株离冯永昌卧室最近的黄葛树,纵身隐藏其上。
巡夜的王老头梆梆梆地敲响了二更的鼓声,一路从南门拖拖沓沓而来,嘴里有气无力地叫唤着:“小心火烛,谨防盗贼。”
隐藏在黄葛树上的陈豫川,猛然看见一位黑衣人飞奔而至,那人来到寒阳宫门前,守卫的兵弁无不对他点头哈腰,神情十分恭敬。黑衣人径直来到冯永昌所住的房间前,伸手敲了敲门。
冯永昌掌灯相迎,灯光下,陈豫川见黑衣人竟然是银库的库工杜亮,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在陈豫川的记忆里,存着各种各样人物的档案,这个来历不明不白的杜亮,当然是他记忆中的重头档案。
杜亮人称蛮牛,年龄二十七岁,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三年前经人推荐,从潼川府振远镖局到遂州银库当了一名库工。其人平时里表情阴冷,从不与他人过多往来,在遂州城内无亲无戚也无房产,租了小南街上一间小民房,独自一人居住。
陈豫川忙用暗号遍示众位兄弟,令他们务必将杜亮截获。吩咐完毕后,陈豫川自己先行一步,匆匆赶到杜亮在小南街的临时住处,反复搜索之下,竟然一无所获。
陈豫川并不失望,又连忙赶到州衙的巡捕房内,兄弟们早已将杜亮捆绑在此等候。陈豫川端坐堂上,面对神情倨傲的杜亮,毫不转弯抹角地单刀直入,大声询诘库银失盗之事。
杜亮听了陈豫川的问话,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摇了摇头,神色如常地反诘陈豫川所问何事。
陈豫川知道他有冯永昌撑腰,并不把自己一个小小的捕头放在眼里,加之此人性情阴冷,心理素质绝佳,如若与他简单地问问话,无异于对牛弹琴。为了打消杜亮心存侥幸的念头,陈豫川示意兄弟们乱棍猛杖,下手绝不留情。
众位兄弟长期跟随陈豫川走州闯县,吃香的喝辣的,当然也办过无数的大案要案,对老大点头扬眉间的暗示,早已烂熟于心。当下发一声喊,乱棍齐齐打在了杜亮结实的身上,下手狠辣,哪里还管得了他的死活?
杜亮果然是一条“蛮牛”,虽然乱棍加身,始终低着头不哼不号。
陈豫川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曾听师傅阳明生说过前朝库工的逸闻轶事,因此知道杜亮不哼不哈并非他很坚强,而是他的身上藏有秘密,怕开口呼号露了馅儿!兄弟们当然不知道这个秘密,见老大的眉头皱成了一堆,那是下死手的暗号。于是众捕快下手愈发地凶狠,一时棍落如雨,打断了好几根青冈木做的棍杖。
杜亮终于熬不住拷打,大声惨叫起来。陈豫川看见从他的肛中,接二连三地屙出五锭库银来。
杜亮见实在无法再隐瞒下去了,遂尽招其秘。
杜亮者,实乃巡抚冯永昌之外侄也,祖籍京师丰台人,偶然得知了库工之秘,偷偷地藏在家中练习。初时,将鹌鹑蛋塞进肛内,逐渐适应后,改用卵石涂抹麻油塞之。稍后,又以铜锭塞肛中贮藏,如此循序渐进,五年其技乃成。杜亮挟此绝技悄悄入川,先到潼川府振远镖局当了个趟子手,后又找舅父冯永昌将自己荐入遂州银库当了库工。三年间,杜亮以此技盗银数以百万计。
交代至此,任由捕快们百般拷问,杜亮再不多说一言。他只承认冯永昌是自己的舅父,既不肯说赃银藏于何处,也不肯承认所犯之事与冯永昌有关。
陈豫川知道杜亮说的话有真有假,却再也撬不开他的嘴巴。无奈之下,陈捕头只得将实情迅速报告周昌明知晓。二人秘密将杜亮囚于州牢中,并严禁消息外传。州里的大小官员像往常一样,陪着冯永昌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十日后,兵刑二部的公文到了遂州。
陈豫川持文牒赶往省垣成都,率众包围了冯永昌的私人府邸,从其家中起获库银一百六十万两之巨,其中大半已熔解成了银块。
陈豫川大喜,交代兄弟们务必将赃银押解回遂州,自己则乘了快马先回遂州上报州牧大人。
周昌明得报,大喜过望,连夜发兵将冯永昌抓获。
大清乾隆十二年秋九月十六日,刑部百人会审,轰动全国的遂州库银失盗案画押结案。圣谕:斩冯永昌及杜亮于京师菜市口,悬首于西门示众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