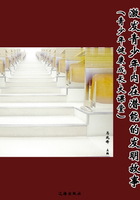碰了这个钉子之后,特文科里顿小姐大声地问道,那么钱应该付给“哪位先生”?这样的先生一共有两位(特文科里顿小姐是雇了两辆马车前来的),两人接了钱,都把两先令六便士放在摊开的巴掌上,一言不发地瞪着她,张着嘴巴,似乎要让天地都看到,他们受到了怎样不公正的待遇。特文科里顿小姐被这幅骇人的景象吓坏了,又在每只手里放了一个先令,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诉说着天理人情,一边开始重新数行李,但这次把“两位先生”也都算了进去,结果总数更乱了。那“两位先生”呢,都只是瞅着那最后一个先令,仿佛这么一瞧,它就可以变成十八便士似的,但是最后只得嘟嘟哝哝地走下了台阶,上了各自的马车,扬长而去,撇下特文科里顿小姐坐在帽盒上直淌眼泪。
比利金看到她哭丧着脸,无能为力,一点也不表示同情,只是吩咐“叫一个年轻人进来”,让他跟行李去搏斗。等那位大力士退场之后,一切才恢复平静,新房客也开始吃饭了。
但是比利金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知道特文科里顿小姐主持着一所学校。从这一消息引申出去,她马上得出了结论:特文科里顿小姐是想在她面前摆老师的架子。“但是你休想,”比利金自言自语道,“我可不是你的学生,不是她,”这是指罗莎,“不是那个可怜的姑娘!”
另一方面,特文科里顿小姐已经换好了衣服,恢复了精神,又燃起了慈祥的愿望,想要利用一切机会广施教化,尽量摆出心平气和的神态,以便为人师表。这时的她心情舒畅,介于两种生存状态之间,她把针线筐放在面前,既像是一位与人为善、和蔼可亲的伴侣,又像是一位明白事理、循循善诱的师长。正在这时,比利金进来了。
“我不想向你们隐瞒,女士们,”比利金说道,身上裹着庄严的围巾,“因为不论是隐瞒我的动机或者我的行为,都不符合我的性格,因此我冒昧地特地前来拜望,表示我希望你们可以对晚餐感到满意。我的厨娘虽然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的工钱已经足以促使她勤奋学习,不只是懂得烧烧家常便饭而已。”
“我们确实觉得味道不错,”罗莎说道,“谢谢你。”
“我们的饮食一向丰盛而且富有营养,简单而且有益健康,”特文科里顿小姐说道,口气中有一种优越感,这些话飘进比利金嫉妒的耳中,无异于是在称呼她“我的好人”,“加上我们一直住在那个古城,在有条不紊的家庭里过着安静舒适的日常生活,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来到这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满。”
“关于你们的饮食,我已经关照过我的厨娘,”比利金忍不住坦率地回答道,“我想,特文科里顿小姐,你也会同意,这种未雨绸缪是必要的。我对她说,这位小姐由于已经习惯了我们这儿所认为的贫乏的饮食,最好逐步地提高食品的质量。因为从简陋的饮食一下子改成丰盛的饮食,从所谓的大锅菜一下子变成所谓的小锅菜,这需要体质上能够适应,可是年轻人往往缺乏这种能力,尤其是那些住惯寄宿学校的女学生们。”
很清楚,比利金现在是要公开跟特文科里顿小姐作对,仿佛她已经充分地肯定,后者是她天然的敌人。
“我相信,你的话并无恶意,”特文科里顿小姐回答道,隐隐地感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但是请允许我提醒你,它们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这只能是由于你完全缺乏准确的知识才造成的。”
“我的知识,”比利金反驳道,为了加重语气,显得既彬彬有礼,又强硬有力,于是把音节拖得很长,“特文科里顿小姐,我的知识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我相信,大家公认经验的指导是正确的。但是不论是否如此,我年轻的时候进过一所非常体面的寄宿学校,校长的文雅高贵不亚于你,年纪也同你差不多,或者再年轻几岁也说不定,可是它的伙食却使我得了贫血症,一辈子都没有医好。”
“这是很有可能的,”特文科里顿小姐说道,仍保持着模糊的优越感,“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罗莎,我的孩子,你的针线做得怎么样了?”
“特文科里顿小姐,”比利金又说道,仍然彬彬有礼的,“在你暗示要我退出之前,我作为一个上等人,想请教你,希望你也作为一个上等人来回答我,你是不是怀疑我说的话?”
“我不明白,你根据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特文科里顿小姐刚开口说到这里,比利金就制止了她。
“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当做假设,我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假设。你很有口才,特文科里顿小姐,毫无疑问,这是你的学生所期望的,同样毫无疑问,学生付了学费也是值得的。我相信,这些都毫无疑问。但是我不会为你的口才而付钱,也不指望在这里从你的口才中得到教益,因此我还是要重申我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你的血液循环不良——”特文科里顿小姐又开口道,但是比利金又立即制止了她。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措辞。”
“那么,如果你认为,你的血液贫乏——”
“我是说寄宿学校给我造成的贫血。”比利金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特文科里顿小姐继续说道,“我所能说的只是,根据你的说明,我不得不相信,你确实患了贫血症。我还必须说明,如果这种不幸的状况影响到了你的谈吐,那真是太令人遗憾了,因此,改变你的贫血状态是非常有必要的。罗莎,我的孩子,你的针线做得怎么样了?”
“哼!在离开之前,小姐,”比利金高傲地把特文科里顿小姐从视线中删除了,向罗莎说道,“我希望你我之间可以取得谅解,从今以后我只与你一个人打交道。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小姐,我只知道像你这样年纪的一个。”
“这办法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亲爱的罗莎。”特文科里顿小姐表示道。
“小姐,”比利金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我听说有一种磨臼,只要把老处女放在里面一磨,就可以使她们恢复青春(这对我们中间有些人来说,实在太好了)。我现在不是在说,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磨臼,可以使那些老处女变成少女,我只是说,我只知道你这么一个少女。”
“今后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向这儿的人提出,”特文科里顿小姐说道,露出了高贵而愉快的脸色,“亲爱的罗莎,我只要通知你就行了,我相信,你会把它传达到应该传达的地方。”
“晚安,小姐,”比利金既热诚又冷淡地说道,“我的眼里只看到你一个人,我怀着最真诚的祝愿祝你晚安。我十分愉快地说,我不必向另一个人表达我的鄙视,不幸的是,这个人是与你有着密切关系的。”
比利金讲完这一篇告别辞,便仪态万方地走了。从此,罗莎便成了一只羽毛球,不停地在两只球拍之间飞来飞去。不经过一场大战,什么也做不成。例如,在每天都要碰到的正餐问题上,特文科里顿小姐在三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下,会这么说:“亲爱的罗莎,请你跟这屋里的人商量一下,能否给我们炸一盘羔羊肉,要是没有,烤鸡也成。”
于是比利金会驳斥道(罗莎并没有说一句话):“罗莎小姐,如果你了解一点鲜肉市场的情形,你就不会想吃炸羔羊肉了。因为第一,羔羊早已长成绵羊了;第二,市场里有的日子杀羊,有的日子不杀。至于烤鸡,小姐,老吃它非吃倒胃口不可,再说,你不妨到市场去看看,能买到的鸡都又老又瘦,腿细细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贪图便宜,专门挑瘦的买呢。小姐,你还是想点新鲜花样吧。应用一点家政知识,来吧,想些别的菜肴吧。”
这位聪明慷慨的家政专家作了这番宽宏大量的分析之后,特文科里顿小姐受到了刺激,红着脸回答道:“哦,亲爱的罗莎,你不妨向这屋里的人提一下,鸭子也可以。”
“啊,罗莎小姐!”比利金喊了起来(罗莎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你竟然提到了鸭子,让我吃了一惊!别说现在不是吃鸭子的季节,价钱非常贵,老实说,我看到你吃鸭子,心里就很难过,因为鸭子可供食用的只有胸脯肉,可现在的鸭子简直找不到胸脯肉,装在盘子里就只有薄薄的几片,只有皮和骨头!再想一下,小姐。多考虑考虑你自己,不要管别人。来一盘胰脏,或者一点儿羊肉吧。这类的食品可以任你挑选。”
确实,有时这游戏会变得非常激烈,甚至剑拔弩张,使得上面那种小接触显得相形见绌。但是比利金几乎万无一失,得分总是比较高,有时明明已经走投无路,她仍然能够出奇制胜,打败对方。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罗莎在伦敦郁郁寡欢的处境,这儿的气氛只能使她觉得,仿佛她在等待着永远等不到的东西。跟特文科里顿小姐做针线和谈天,她感到非常厌倦,因此提议一边做针线一边读书,特文科里顿小姐欣然地同意了,因为她的朗读是有口皆碑,久经考验的。可惜罗莎不久就发现,特文科里顿小姐对原作不太忠实。她会跳过爱情场面,插进些赞美女子过独身生活的段落,还会篡改原文,塞进不少道德说教的私货。为了举例说明,不妨看看这热情的一段:“爱德华说道,我最亲爱而仰慕的人儿啊,于是把那个亲爱的头搂在胸口,把温存的手指插入她柔软的头发,让它像金色的雨一般从手指间落下。我最亲爱而仰慕的人儿呀,让我们飞出这冷漠的世界,这铁石心肠的寒冷的荒原,飞向温暖繁荣的、信任和爱的天堂吧。”但是在特文科里顿小姐伪造的版本中,它就变得平淡无味:“爱德华说道,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以及白发苍苍的教区牧师的允准,我们终于订婚了。于是他怀着敬意,把纤细的手指举向唇边,这些手指擅长刺绣、针线、编织,以及其他真正的女性技艺。他说,让我在明天日落之前,去拜访令尊,告诉他,我们将住在郊区的一栋房子里,它也许不够高贵,但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在那里的晚会上,他将会永远受到欢迎。那儿的一切安排都要符合节约的原则,为了家庭的幸福,丰富的学识和主持家政的天使的美德一定要同时具备。”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邻居们开始谈论,说比利金家那个漂亮的姑娘仿佛总是在惦念着什么,老是从客厅那灰乎乎的窗口向外眺望,情绪有些消沉。确实,要不是碰巧找到了些描写航海和海上冒险活动的书籍,给她带来了一些光明,她真的会落入完全的消沉。为了补偿删去的描写爱情的段落,特文科里顿小姐总是会大声地朗读经纬度、方位、风向、水流、船体尺码以及其他的一些统计数字(尽管这些东西使她完全摸不着头脑,她还是觉得它们对她的学生是很有教益的),罗莎一边仔细地听,一边拼命地吸收她最感兴趣的内容。就这样,她们两个人各得其所,比之前愉快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