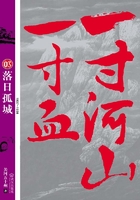整整半年过去了。克里斯帕克先生坐在伦敦慈善之家总部的会客室里,等待着哈尼山得先生接见他。
在大学时代的体育活动中,克里斯帕克先生认识了一些拳击大师,观看过他们的两三次比赛。现在他有机会看到,根据骨相学对于后脑勺结构的分析,职业慈善家和拳击家是非常相似的。在慈善家身上,那些构成或者助长“斗殴”习性的器官特别发达,以至于他们动不动就要对他们的同胞兄弟发起进攻。现在便有几位慈善大师进进出出,忙个不停,脸上杀气腾腾,仿佛随时准备与他们碰到的后生小子一决雌雄,这与克里斯帕克先生当年目睹的拳击场上的盛况简直如出一辙。他们正在筹建一个小小的精神磨坊,要对农村地区发起进攻,另一些慈善大师则在支持这个或者那个重量级拳击手,要他们参加这一场或那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那副神气就跟拳击场老板差不多,因此他们要达成的协议也许只是一场场厮杀的结果。这些战斗的一个组织者,曾经以慷慨激昂的演说而闻名,身穿一套黑色衣服,这使得克里斯帕克先生想起了一位与他相仿的拳击界已故的大师。那位社会名流曾经一度以“冷若冰霜”闻名于世,当年在绳子和木桩圈起的拳击场上,真是显赫一时。这类大师和那类大师只有三点不尽相同。第一,慈善家一向缺乏锻炼,因此大都太胖,无论脸和身体都显得脂肪过多,形成了拳击家们称之为羊油布丁的状态。第二,慈善家不如拳击家脾气好,常常要用粗话骂人。第三,他们的战斗规则大大地需要修正,因为它不仅使他们可以把别人逼得背靠在绳子上,还可以把人逼得发疯,而且对方即使倒下了,仍可以拳打脚踢,不受限制,可以踹上一只脚,还可以挖对方的眼睛,还可以从背后打断对方的骨头,不必手软。在最后的这些细节上,拳击大师是比慈善大师光明磊落得多的。
克里斯帕克先生思考着这些相似和不同,同时观察着进进出出的慈善家们,发现这些人似乎都背负着一种特殊的使命,即要穷凶极恶地从别人手中攫取一些东西,却绝对不给别人任何东西。他这么全神贯注地思考着,观察着,以至于人家把他的名字叫了两遍,他才听到。最后,他才应了一声,于是一位衣衫褴褛、工资低微的雇员慈善家(即使他为人类的公敌办事,他的境况恐怕也不至于这么悲惨),把他带进了哈尼山得先生的办公室。
“先生,请坐。”哈尼山得先生说道,嗓音十分洪亮,口气像是学校老师在向一个不讨他喜欢的学生下命令。
克里斯帕克先生坐下了。
哈尼山得先生在几千份通知的最后几十份上签了字。这些通知要求相应数目的穷苦家庭响应号召,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付款,参加慈善之家,否则便会被上帝抛弃。另一位衣衫褴褛的雇员慈善家(虽然办事认真,但是毫不起劲)把这些通知放进一只篮子带走了。
“现在,克里斯帕克先生,”哈尼山得先生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之后说道,一边把椅子向他转过一半,胳臂弯成直角,两只手搭在膝上,紧皱着眉头,仿佛表示,我得赶紧把你打发走,“听着,克里斯帕克先生,你和我,先生,对人的生命的神圣意义怀有不同的观点。”
“是吗?”初级教士问道。
“是的,先生。”
“请允许我问一下,”初级教士说道,“你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件神圣的事物,先生。”
“请允许我问一下,”初级教士继续问道,“你认为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什么?”
“算了,先生!”慈善家回答道,胳臂仍弯成直角,紧皱着眉头望着克里斯帕克先生,“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你刚才一开口就声称,我们怀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否则你不可能这么说)你必然认为我持有某些观点。请问,你认为我持有哪些观点?”
“现在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轻人,”哈尼山得先生说道,仿佛后面这一点使情况变得特别严重,如果换作一个老年人,他还可以不予计较,“被人用暴力从地面上消灭了。你认为这叫什么?”
“谋杀。”初级教士回答道。
“先生,你把做这种事的人叫什么?”
“杀人犯。”初级教士回答道。
“我很高兴,你至少承认这一点,先生,”哈尼山得先生以他那咄咄逼人的态度回答道,“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说到这里,他又皱了皱眉头,盯着克里斯帕克先生。
“请你说明一下,你这些毫无根据的话是什么意思?”
“先生,我坐在这里,是不怕别人威胁的。”慈善家回答道,提高了声音,像是呐喊似的。
“作为现在唯一在场的人,我对这一点比任何人都清楚,”初级教士镇静自若地回答道,“但是我打断了你的解释。”
“谋杀!”哈尼山得先生继续说道,口气像是在跟人吵架,已经忘乎所以,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合抱着双臂,每讲一句短短的话便会感慨万千,点着头露出厌恶的神色,“杀人!亚伯!该隐!我不能跟该隐打交道。我不能握沾满鲜血的手,它只能使我发抖。”
但是克里斯帕克先生并没有马上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拉开嗓子欢呼,像是慈善之家开会的时候,那些同人一听到这些话,必然会做的那样。他很冷静,只是把交叉的双腿中原来搁在上面的一条换到了下面,温和地说道:“我不想打断你的解释,因为你已经开始了。”
“《十诫》中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先生!”哈尼山得先生继续说道,像是演讲似的停顿了一下,表示在责问克里斯帕克先生,似乎后者认为,《十诫》说过杀人可以偶尔为之,然后洗手不干一样。
“《十诫》还说,不可作假见证。”克里斯帕克先生指出。
“够了!”哈尼山得先生咆哮道,显得声色俱厉,盛气凌人,如果在开会时,怕是会把整个屋子都震塌了,“够了!以前由我监护的人现在已经成年了,我的委托也结束了,它使我一想起来便不寒而栗。这是你代他们领取各项费用的账单,这是收支清单,这些钱你都收到了,及时地收到了。现在让我告诉你,先生,我希望你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初级教士,今后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他点了点头,“更好的作用。”他又点了点头,“更——好——的——作——用!”他又点了点头,最后还连续点了三次。
克里斯帕克先生站了起来,脸上有些发热,但是仍然可以完全控制住自己。
“哈尼山得先生,”他说着,拿起了那些单据,“关于我比现在发挥更好的还是更坏的作用这个问题,是一件涉及判断力的事情。也许在你看来,我只有参加了你们的慈善之家,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说得对,先生!”哈尼山得先生回答道,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摇了摇头,“你早参加这个团体就好了!”
“可惜我并不这么以为。”
“换句话说,”哈尼山得先生说着,又摇了摇头,“如果你致力于揭露和惩办罪行,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俗人,那么,我也可以认为你已经更好地发挥了你的职业的一种作用。”
“我对我的职业可以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它的首要责任是帮助那些处在穷困和苦难中的人,帮助他们摆脱绝望和烦恼,”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但是我完全清楚,我的职业不是要为各种职业规定它们的任务,所以我不想多谈了。然而我必须为内维尔先生,也为内维尔先生的姐姐(在极小的程度上也是为我自己),对你说,我知道我完全明白和了解内维尔先生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思想和感情,我丝毫不必害臊,也不必隐瞒,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没有什么需要悔恨或者改正的地方,我相信他的话都是真的。由于我相信这一点,我才关心他帮助他。而且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我就要关心他帮助他。如果任何考虑能够动摇我的决心,我将为我自己的卑鄙感到可耻,以至于任何人,包括任何女人的赞许,都不能补偿我对我自己的鄙视。”
善良的人!勇敢的人!而且又是这么的谦逊。初级教士的自负,并不比一个在微风习习的操场上守住球门的小学生多。他单纯而坚定地忠于自己的责任,不论大事小事都一样。一切忠诚的人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忠诚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真正伟大的心灵看来,没有什么是渺小的。
“那么你认为这件事是谁做的?”哈尼山得先生突然向他转过身来问道。
“我绝对不愿,”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为了洗清一个人的嫌疑,轻易地把罪责加在另一个人的头上!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告发。”
“啐!”哈尼山得先生大不以为然地喊了一声,因为这绝对不是慈善之家一向奉行的原则,“先生,你不是一个毫无私心的证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
“我怎么会有私心?”克里斯帕克先生问道,天真地笑了笑,一时想不明白。
“先生,你教学生是会拿到一笔酬金的,它难免会对你的判断发生一定的影响。”哈尼山得先生粗鲁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也许还想保留这笔收入?”克里斯帕克先生回答道,终于恍然大悟了。
“好啦,先生,”这位职业慈善家回答道,站起身来,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我不想给人们量尺寸做帽子,如果他们觉得我手头有的帽子对他们合适,只要愿意,不妨拿去戴上。这是该由他们去考虑的事,与我无关。”
克里斯帕克先生看着他,心中升起了一股正义的怒火,于是向他发出了指责。
“哈尼山得先生,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本来指望,我们可以像私人之间商谈问题一样,心平气和,不必使用讲坛上那种夸夸其谈的态度和耸人听闻的手段,我也不必为此提出指责。但是你在我面前正是表现出了这两种能耐,如果我对此保持缄默,那就无异于成了这两者的合适目标。这使我不能容忍。”
“我知道,它们不合你的口味,先生。”
“这使我不能容忍,”克里斯帕克先生又说了一遍,没有觉察到对方的插话,“它们违反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正义观念,同样也违反了一个高尚的人应有的克制精神。有一个人,你认为他犯了大罪,可是我了解有关的一切细节,我拥有许多理由,真诚地相信他是无辜的。就因为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我与你的意见不合,你便使出讲坛上惯用的手段,立即把矛头针对着我,指责我否认这桩罪行本身的严重性,而且是它的帮凶和教唆者!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在另一些问题上把我当做你的对立面,你也会拿起讲坛上花言巧语的法宝,利用人们的轻信,经过动议、附议、一致通过等等手续,把可笑的谬误或者无稽之谈标榜为真理。如果我拒绝相信它,你便会使出讲坛上蛊惑人心的手段,宣称我怀疑一切。总之,由于我现在不愿膜拜你制造的假上帝,你便说我否认真的上帝!如果有一天,你声称你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战争是灾难。于是你说,只要把一系列混乱的决议堆在一起,抛上天空,就可以消灭战争,其实你抛上去的只是一只纸鸢的尾巴。我根本不承认这发现是你的功劳,我也根本不相信你的办法可以奏效。于是你又使出讲坛上蛊惑人心的手段,说我喜欢战场上的恐怖,是魔鬼的化身!如果有一天,你又头脑发热,利用讲坛胡言乱语,你会不分青红皂白,把清醒的人当做醉汉来惩办。我仗义执言,要求为清醒者着想,考虑他们的舒适、方便和饮食起居,你便会使出讲坛上蛊惑人心的手段,宣称我别有用心,把上帝的选民看做牲畜和野兽!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你们这些动议者、附议者和支持者,你们各级大大小小的慈善家们,都像疯狂的人一样杀气腾腾。你们一向不顾一切,不负责任,把最卑鄙、最无耻的动机栽在别人身上(让我来提醒你,你刚才还在这么做,你应该为此感到可耻),你们任意引用数字,你们明明知道是片面的,不能说明复杂的情况,就好比一本账上只有借方没有贷方,或者只有贷方没有借方。因此,哈尼山得先生,我认为这种夸夸其谈、蛊惑人心的态度,即使在社会生活中也是有害无益,如果把它应用到私人生活中,那就更加不堪设想,无法容忍了。”
“你说得太过分了,先生!”慈善家喊道。
“但愿如此,”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再见。”
他飞也似的冲出了慈善之家,但是不久便恢复了正常的轻快步子,一边走一边露出了笑容,心想,要是那位陶瓷牧羊女看到了他在刚才这场小小的热烈争执中,怎样对哈尼山得先生迎头痛击,不知会怎么说呢。因为克里斯帕克先生也有一点无伤大雅的虚荣心,但愿自己打中了要害,并且自以为已经把那位慈善家打得落花流水,因此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他朝斯坦普尔法学会馆走去,但不是去P.J.T.找格鲁吉斯先生。他顺着吱吱出声的楼梯,一级级地往上走,最后来到屋角的几间顶楼那儿,打开没有上闩的门,在内维尔·兰德勒斯的桌子旁边站住了。
一种隐匿与寂寞的气氛笼罩在屋子里,也笼罩在居住者的身上。他憔悴不堪,跟这些屋子一样。它们那倾斜的天花板,那粗糙生锈的锁和炉栅,那笨重的木箱和屋梁,似乎都在逐渐腐烂,散发出监狱的气息,而他呢,具备着一副犯人的憔悴外表。然而阳光仍然从丑陋的老虎窗中射进屋子,这窗户伸出屋顶,耸起在瓦片中间。对面那裂缝的、被熏黑的护墙上,几只受骗的麻雀在跳来跳去,似乎得了风湿病,像是一些披着羽毛的小瘸子,把拐棍忘在巢里了。尚未凋谢的树叶在附近拂动着,改变了一点气氛,发出了一些不太悦耳的声音,要是在乡下,这就可以称为美妙的旋律了。
屋子里陈设简陋,但是书籍不少。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一个穷学生的住处。克里斯帕克先生是这些书的挑选者,或者出借者,或者赠与者,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这从他一进屋看到这些书时,眼中流露的亲切目光便可一目了然。
“内维尔,怎么样?”
“我的心情很好,克里斯帕克先生,正在用功读书。”
“我希望你的眼睛不要睁得这么大,也不要这么亮。”初级教士说着,慢慢地放开了他握住的手。
“它们这么亮是因为看到了你,”内维尔回答道,“等到你离开了我,它们马上又会变得暗淡了。”
“要振作精神,振作精神!”对方用鼓励的口气敦促道,“这是战斗,内维尔!”
“即使我快要死去,你的一句话也能使我振作起来,即使我的脉搏停了,我认为只要你一碰我,它又会重新跳动起来,”内维尔说道,“但是我已经振作了精神,我正在好好学习。”
克里斯帕克先生把他的脸转动了一下,让它对着亮光。
“我希望看到你这儿更红润一些,内维尔,”他说着,指了指自己健康的脸颊作为样板,“我希望有更多的阳光照在你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