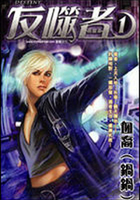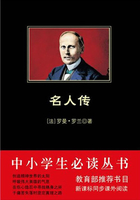出发前,他只吃过一片面包,现在想吃早饭了,便走进路边的第一家饭店。
在大篷车饭店,只有马和牛这类的旅客才能随到随吃,因为水槽和干草总是现成的,至于人,到这儿来用早餐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这辆大篷车花了不少时间,才准备好茶、吐司和熏猪肉。内维尔坐在铺细沙的店堂内消磨着这段时间,看着那些咝咝出声的湿木柴,心想不知要等他走了多久,它们才会给别人带来温暖。
确实,大篷车饭店位于山顶,冷冷清清,门前的泥地上尽是潮湿的马蹄印和踩烂的麦秸。老板娘在柜台里打骂着泪流满面的婴孩(孩子的一只脚上穿着红袜子,另一只脚板光着),干牛酪打翻在架子上,旁边是一块发霉的台布和一把绿柄餐刀,放在一只铁制的独木舟里,脸色苍白的面包躺在另一只独木舟里,旁边撒满了面包屑,好像船触了礁,它正在淌眼泪一样,半干半湿的替换衣服晾在那里,供大众参观。这儿所有的饮料都是用带柄大杯子喝的,其他餐具也跟大杯子是一路的货色。从这一切看来,大篷车饭店尽管在招牌上写着“服务周到,人畜无欺”,事实上恐怕难以办到。然而目前这个人对饮食并无苛求,可以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在超过需要的过长的休息之后,重新踏上旅途。
出了店门,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他停下脚步,琢磨着是继续走大路,还是走一条小路,这小路两旁有高高的树篱,从一片斜坡穿过微风习习的荒原之后,显然终究又会折回大路。于是他决定走小路,因为它坡度很陡,路面上又印满了深深的车辙,内维尔·兰德勒斯一早就出发了。他健步如飞,走时需要花点力气。
他费力地走着,听到后面似乎传来了脚步声。由于这些人走得比他快,他便站在一边,紧靠着高高的树篱,好让他们通过。但是他们的态度十分奇怪。只有四个人走到前面去了,另四个人却放慢了步子,逗留在后面,仿佛打定主意要等他走时跟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大约有六七个)却马上转过身子,以飞快的速度循原路往回走了。
他瞧瞧后面的那四个人,再瞧瞧前面的那四个人。他们也都瞧着他。他继续赶路了。前面的四人一边走,一边不时地回头看他,后面的四人则逐渐地向他逼近。
当他们走出狭窄的小路,来到荒原中宽广的斜坡上之后,不论他向哪一边移动,这队形始终保持着原状,这样,已经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这些人的包围。为了最后证实这点,他站住了,结果他们也都站住了。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盯住我?”他问所有的人,“你们是一帮土匪吗?”
“不要答话,”其中一人说道,并不朝谁看一眼,“还是保持沉默的好。”
“还是保持沉默的好?”内维尔反问道,“这话是谁说的?”
没有人回答。
“对,你们这帮胆小鬼,还是别出声,让我过去的好。”他怒气冲冲地继续说道,“你们前面四个,后面四个,想包围我,我不会屈服的。前面四个听着,把路让开,我一定要过去。召唤人们去做早祷时,他已经离城有八英里了。”
大家全都站着不动,包括他自己在内。
“如果八个人,或者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向一个人进攻,”他继续说道,火气更大了,“那么这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其中一部分人动手了。上帝作证,如果你们再不让开,我只能这样做啦!”
他扛着笨重的手杖,加快了脚步,向前面四个人猛冲过去。其中最高大、最强壮的一个立即跳到他这一边,敏捷地迎上前来,但直等那根大手杖用力打过去,他才扑上前来,两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
他们一起在草地上厮打着,这个人压低了嗓音说道:“别管他!一对一,公平交易!他和我的身材相比,不过像个小女孩儿,等到教堂的钟声在修道城响起,何况他的背上还背着东西。别插手。我能制伏他。”
他们紧紧地互相揪住,在地上滚了一会,弄得两人脸上都血迹斑斑,最后,那人把膝盖从内维尔的胸口移开,挺直了身子说道:“就这样!现在来两个人,一人拉住他一条胳膊!”他们立即照办了。“至于你说我们是一帮土匪,兰德勒斯先生,”那人说道,吐出了一口血,从脸上抹掉了更多的血,“你到了中午就会明白一切的。不是你逼我们动手,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反正现在我们要带着你,绕到大路上去,如果我们是土匪,你不愁找不到人帮助的。谁给他脸上擦一下,瞧,血还在往下淌呐!”
脸擦干净以后,内维尔认出了那个说话的人,原来就是修道城赶公共马车的乔,他只见过他一次,就是在他到达的那天。
“现在我劝你还是别讲话,兰德勒斯先生。你会看到,有个朋友在大路上等你,他是在我们分成两组时,从另一条路往前走的。在你遇到他以前,还是不开口的好。谁把那根手杖拿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内维尔完全给搞糊涂了,他向周围看了看,没有说一句话。两个押送者揪住了他的胳膊,他走在他们中间,好像在梦境里似的。最后,他们回到了大路上,走进一小群人中间。刚才回来的那几个人也在其中,但是站在中央的是贾思伯先生和克里斯帕克先生。两个押送者把内维尔带到了初级教士的面前,放开了他,这是出于对那位先生的敬意。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我简直被搞糊涂了!”内维尔喊道,人们紧紧地围住了他。
“我的外甥在哪里?”贾思伯先生问道,态度很凶。
“你的外甥在哪里?”内维尔反问道,“为什么你要问我?”
“我要问你,”贾思伯回答道,“因为与他最后在一起的是你,他现在失踪了。”
“失踪了?”内维尔吃了一惊,喊道。
“别忙,别忙,”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让我来说,贾思伯。内维尔先生,你不必惊慌失措,好好地想一想。现在你必须头脑冷静,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注意听我的话。”
“我尽量这么做,先生,沿着大路前行,但是我好像疯了。”
“昨天夜里,你是与埃德温·德鲁德一起离开贾思伯先生的家的?”
“是的。”
“什么时间?”
“大概是12点吧?”内维尔伸手摸了摸混乱的脑袋,向贾思伯问道。
“一点也不错,”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这正是贾思伯先生向我讲的时间。你们是一起到河边去的?”
“毫无疑问。我们是到那儿去看风的动向。”
“后来呢?你们在那儿待了多久?”
“大约十分钟,我想不会更多。后来我们一起走回你的家,他在门口跟我分手的。”
“他有没有说还要到河边去?”
“没有。他说他马上就回家。”
旁边的人互相看了看,又望了望克里斯帕克先生。贾思伯先生一直密切注视着内维尔,这时对克里斯帕克先生用怀疑的口气说道——他的声音轻轻的,但很清楚:“他的衣服上怎么有那些血迹?”
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内维尔衣服上的血迹。
“这根手杖上同样也有血迹!”贾思伯从一个人手中拿过手杖说道,“我知道这是他的手杖,昨天夜里他就拿着它。这是怎么回事?”
“请你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内维尔?”克里斯帕克先生敦促道。
“刚才为这手杖,那个人跟我厮打过,”内维尔指着刚才的对手说,“你可以看到,他身上也有同样的血迹,先生。我发现我被这八个人围困时,我还顾得了别的吗?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我怎么猜得到真正的原因呢?”
他们承认,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保持着沉默,还引起了殴斗。然而那些目睹这一切的人,看到已经在晴朗寒冷的空气中干掉的血迹,还是皱起了眉头。
“内维尔,我们得回去了,”克里斯帕克先生说道,“当然,你愿意回去弄清事实,辩明你无罪吧?”
“当然,先生。”
“兰德勒斯先生可以跟我并肩走,”初级教士继续说道,同时向众人望了一眼,“走吧,内维尔。”
他们开始往回走了,其余的人都跟随着他们,保持着不同的距离,只有贾思伯走在内维尔的另一边,始终没有离开那个位置。他一声不吭,听着克里斯帕克先生一再重复他的问题,而内维尔一再重复他刚才的回答,以及双方如何提出一些解释性的猜测。他坚决保持着沉默,尽管克里斯帕克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一直在请求他参加讨论,但是任何请求都无法改变他脸上那冷若冰霜的神色。他们进城以前,初级教士提议,不妨马上去找市长,贾思伯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在进入撒帕西先生的客厅以前,他始终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