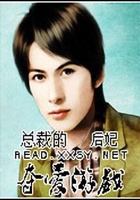We went slipping silently along, between the green and fragrant banks, with a sense of pleasure and contentment that grew, and grew, all the time. Sometimes the banks were overhung with thick masses of willows that wholly hid the ground behind; sometimes we had noble hills on one hand, clothed densely with foliage to their tops, and on the other hand open levels blazing with poppies, or clothed in the rich blue of the corn-flower; sometimes we drifted in the shadow of forests, and sometimes along the margin of long stretches of velvety grass, fresh and green and bright, a tireless charm to the eye. And the birds! —they were everywhere; they swept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river constantly, and their jubilant music was never stilled.
It was a deep and satisfying pleasure to see the sun create the new morning, and gradually, patiently, lovingly, clothe it on with splendor after splendor, and glory after glory, till the miracle was complete. How different is this marvel observed from a raft, from what it is when one observes it through the dingy windows of a railway-station in some wretched village while he munches a petrified sandwich and waits for the train.
参考译文
当旅店老板得知我和我的代理人是艺术家时,我们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提升了一大截,得知我们正在欧洲徒步旅行后,我们的地位就更高了。
他向我们介绍了海德堡的路线情况,告诉我们最好绕过哪些地方,最好在哪些地方多逗留些时日;对那晚我所使用的物品,他只收取了低于成本的费用;还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并送了很多德国人最喜爱的绿李子。因为我们赏光,他坚决不答应我们步行离开海尔布隆,于是,叫了葛兹·封·贝利欣根的马车来载我们离开。
我用素描的形式把马车画了下来。它算不上是件作品,只是画家所谓的“习作”——能够完整作画的素材。这幅素描有几处败笔,如:马车的速度与马的步伐不一致,这是不对的。而且,给马车让路的人实在太小了,就是我所说的不符合透视画法。最上边的两条线不是马背的曲线,而是缰绳;似乎还丢了一只车轮——当然在完成的画中,这些败笔都会被纠正。马车后面飞舞的不是旗帜,而是车上的篷帘。画中还有太阳,不过,我没有空出足够的空间。现在,我记不清奔跑的那个人前面是什么了,不过我想那可能是堆干草,或者是个女人。1879年的巴黎画廊上,这幅习作被展览出来,但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因为展览不为习作设奖。
车到桥头的时候,我们付了钱打发马车回去了。河面上漂满了圆木——细长的、没有树皮的松树圆木——我们倚靠在桥栏上,看着人们把这些木头捆成木筏。这些木筏的形状和结构都适用于内卡河道弯曲和极狭窄的地方。木筏长50码至100码不等,尾部有九根圆木那么宽,前部的宽度相当于三根圆木。舵的主要部分是一根撑篙,安装在木筏的前部。三根圆木的宽度只能容纳一个舵手,因为这些小木材的粗细也不过相当于一名普通妇女的腰围大小。木筏几部分的连接是松散的,灵活性也较强,以便随时变向来适应河流任何水流形式的需要。
内卡河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狭窄,你足可以把一只小狗扔到对面。当一些地方水流陡变时,撑筏者就不得不使出几招绝技,引航变向。河流并不总是淹没整个河床——河床的宽度达到30码,有时甚至达到40码——但是石堤把注入其中的水流分隔成三等份,并把主要的水量汇集到中心水道中去。在浅水期,这些整齐的、狭窄的石堤会露出水面四五英寸,就像被淹没的房屋的屋顶。但在深水期,它们就都会被河水淹没。在内卡河,一帽子的雨水就能使水位上涨,一满筐的雨水就会使河决堤!
舒劳斯旅馆与几条堤坝走向相同,与它并排的那一段,水流湍急。我时常坐在自己的房间,透过玻璃看那长而狭窄的木筏沿着中心水道顺流而下,擦过堤岸的右侧边缘,小心地对准下游石桥的中孔滑下。我就这样望着它们,在对什么时候能看到它们撞在桥墩,成为残骸的憧憬中迷失了自我。然而,我总是失望。一天早晨,有一条木筏粉碎在那里,不过是在我刚刚踏进房间去点烟时撞击的,因此我还是错过了。
在海尔布隆的那个早晨,当我俯瞰着木筏时,蛮勇的冒险精神突然产生,我对我的同伴们说:“我准备乘木筏去海德堡。你们和我一起去冒险吗?”
他们的脸色吓得苍白,不过还是尽可能优雅地表示赞同。哈里斯想给他的母亲发封电报——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因此,他去发电报了。与此同时,我跑上那条最长、最好的木筏,热情地向舵手打招呼道:“嗨,你们好啊!”这一问候立刻使气氛活跃起来,接着我们便进入了正题。我说我们原本是要徒步到海德堡去的,但现在打算乘坐他的木筏去那里。我的这些话一部分是通过Z先生翻译的,他的德语说得很好;一部分则是通过X先生翻译的,他的德语说得尤其好。我能像发明德语的狂人一样听明白它,不过我要通过翻译才能把它说好。
木筏上的老大提提裤子,若有所思地动动嘴里嚼着的烟草块,说出了我预料中的话——他没有运送旅客的执照,担心万一这件事宣扬出去或者万一出了事故,法律会追究到他头上。于是,我租下了这条木筏,雇了他的舵手,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伴着一阵激昂的号子声,右舷的舵手们弯腰开始了自己的活计,收起缆索,升起筏锚,我们的木筏便飞速地向前移去。很快,它的时速就达到了两海里。
我们一行人聚集在木筏的中央。起初,大家的交谈有些低沉,主要是围绕着生命短暂,难测,危机重重,时刻作好最坏的准备是必需和明智的。这种交谈渐渐变成低语,内容都是些海洋的危险之类的东西。然而,当灰色的东方出现红霞,黎明那神秘的庄严和静寂响起小鸟欢快的歌声时,大家的音调也欢快了许多,我们的情绪逐渐高昂起来。
夏日的德国是至善至美的。但是,如果不乘木筏从内卡河漂流而下,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感知、享受这种至高的温柔、平和的美妙的。木筏的漂流是不可或缺的运动,它柔美、顺滑、流畅、无声;它平息一切狂躁的行为;缓和所有不安的仓促和急躁情绪。在其宁静的影响下,一切影响情绪的烦恼、悲伤都销声匿迹,变成一个梦,一种魅力,一种深深的、宁静的喜悦。这与炎热、辛劳的徒步行走,与尘土飞扬、隆隆行驶的火车,还有在炫目的大道上单调颠簸的疲惫马车,形成了怎样的对比啊!
带着不断高涨的愉悦和满足感,我们在郁葱芳香的河岸间静静地滑行。有的地方,岸边倒垂下的浓密柳枝,覆盖了后面所有的土地;有的地方,河岸一侧是壮丽的山脉,上面植被丰盈,另一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开放着鲜艳的罂粟花,或是靛蓝怡人的矢车菊。我们时而漂流在森林的阴影之下,时而沿着天鹅绒般柔软的草地边缘滑行。那映入眼帘的草地是那么碧绿清新,灼灼明亮,蕴藏着无限的魅力。还有那鸟儿——随处可见。它们频繁地穿梭于两岸之间,鸣起的欢歌不绝于耳。
看日出能让人百般回味且愉悦人心。太阳冉冉升起,耐心地、温柔地铺上一层又一层光彩,披上一片又一片壮丽,直到一个新的早晨完整地筑就起来。在木筏上观赏日出,与等候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嚼着干巴巴的三明治,透过窗户眺望破落的小村庄的感觉,有着天壤之别。
月亮升起来
Spell of the Rising Moon
皮特·斯坦哈特 / Peter Steinhart
有一座小山就坐落在我家附近,我常常会在夜间去爬山。到了山上,城市里的嘈杂就会变成远方的低语。在安静的黑夜里,我能够感觉到蟋蟀的欢乐和猫头鹰的自信。不过,看月出才是我爬山的目的,重新找回在城市中轻易就迷失的那种宁静与纯真。
在小山上,我看过很多次月出。每次月出都是各有风情,不尽相同。秋日里,圆圆的月亮露出丰收的自信;春风中,月亮灰蒙蒙地表达着羞涩;冬日里,冰轮般的月亮孤独地悬在漆黑的空中;夏日中,橘黄色的月亮朦朦胧胧地俯瞰着干燥的田野。每一种月亮都似精美的音乐,感动我的心灵,抚慰我的灵魂。
赏月是一种古老的艺术。远古时代的猎人,对空中月亮的了解如同知晓自己的心跳一样,丝毫不差。他们熟悉29天中的每个月亮,月亮会由明亮饱满变得萎缩,直至消失,然后再次复活;他们知道,月盈期间,每当日落,头顶的月亮就会显得更高更大;他们还知道,月亏期间,月出一日更比一日迟,直到有一天,太阳升起时仍不见月亮的踪迹。古人能根据经验知道到月亮的行踪变化,真是造诣颇深的事情。
但生活在室内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和月亮的联系。城市耀眼的街灯、玷污的烟尘遮蔽了原本晴朗的夜空。人类虽已在月亮上迈出了第一步,反而对月亮变得更加陌生。没有几人能说得出今晚月亮何时升起。
无论如何,月亮仍然牵挂着我们的心。如果不经意间看到刚刚升起的、大大的、黄澄澄的满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一睹她高贵的姿容。而月亮也会赐予观看她的人礼物。
在七月山间的一个夜晚,我得到了她的礼物。车子莫名其妙地熄了火,我一个人束手无策地困在山中。太阳已经落山了,我看到东边山头闪出一团橘红色的光线,好像森林着火一样。刹那间,山头也被火焰吞噬。过了一会儿,月亮突然从密林中探出涨红的大大的脸,夏日空气中弥漫的尘雾与汗气,使月亮显得有些荒谬的变形。
大地灼热的呼吸扭曲了它,月亮变得格外暴躁,不再完美。不远处,农舍里的狗紧张地乱叫起来,好像这奇怪的光亮唤醒了野草中的魔鬼。
然而,随着月亮慢慢爬上山头,它聚合了全身的坚定与威严;它的面孔也从红变成了橘黄,又变成金色,最后成为淡淡的黄。月亮不断地上升,下面的丘陵山谷逐渐暗淡朦胧,好像大地的光亮让月亮渐渐吸走了似的。待到皓月当空,圆圆的月亮洒下象牙般乳白的清辉,下面的山谷在这样的风景里,形成了一片片幽深的阴影。这时,那些乱叫的狗才打消了疑虑——原来那团光是它们熟悉的月亮——停止了吠叫。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信心十足,心情欢畅,禁不住笑了起来。
整整一个小时,我都沉浸在这奇美的景观里。月出是缓缓而又充满微妙的。要想欣赏月出,我们得退回到过去的时代,带着一种对时间有耐心的心态去欣赏。看着月亮毫无顾忌地不断攀升,我们能找到内心少有的宁静。我们的想象力能让我们感到宇宙的广阔和大地的无限,忘却自己的存在,感觉自我的渺小,却又深感自己的独特。
月光从不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艰辛。山坡好像在银色月光下披上了柔和的轻纱。在月光的照耀下,海水显得碧蓝而静谧。沉浸在月光中,我们不再像白天那般精于算计,而是沉浸在自我内心的情感之中。
正当我陶醉于月色之美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七月的那个夜晚,我看了一两个小时的月景后,回到车里,再次转动钥匙发动汽车时,发动机出人意料地响了起来,和几个小时前熄火时一样蹊跷而神秘。我开着车沿着山路回家,月光洒在肩上,心中满是平静。
从那以后,我常常会到山上看月出。当成堆的事务渐渐平息,生活逐渐明朗,这时常发生在秋季,我就会爬上那座小山。我等着猎人之月的出现,等着金色丰盈的月亮俯照大地,给黑夜带来光明。